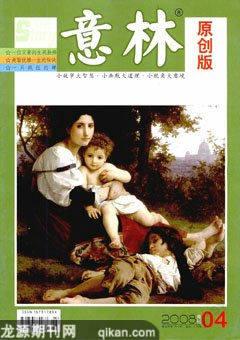超越时空的母爱
刘康声
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改嫁了。说不清母亲为什么要改嫁。因为那时候我只有6岁。
年幼、年轻时。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在了玩上,母亲的生活根本没有在我的视野里做过长久或短暂的停留,也就不知道她是苦是甜。大学毕业后重又回到故乡,接触母亲的机会便多了些。逐渐发现,她表面上很满足、很幸福,而内心里一定有说不出来的滋味。那个我从未叫过“爸爸”的继父初看时像个阅历丰富的老干部。脸上露出的微笑很慈祥,一接触。我就发觉自己上了眼睛的当,大概母亲当初也是上了眼睛的当。他脾气暴躁。言语粗俗,而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的自私,只顾自己的需要,而从不考虑母亲的需要。
一个春天,有一回我去看母亲,母亲正坐在楼下阳光照耀的花园里,把一台微型收录机贴在耳边,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我已经站在她眼前了,她才注意到我,于是放下收录机,关掉。我问:“是不是又听‘二人转呢?”我知道母亲喜欢听这种东北地方戏。母亲也不回答我,只是说一句“来啦”,然后聊一聊天气,聊一聊孩子。有时母亲会主动找个话题。说:“周二下午你哥来了。”或者是:“昨晚你二姐一家三口来过。”接着就说起他们的事。
我之所以做出母亲喜欢听“二人转”的判断。是因为我多次发现母亲独自一人时手捧着小收录机,而且还看到过收录机的盒带仓里装着一盘“二人转”磁带。老人和年轻人不大一样,我曾琢磨过,母亲总是捧着一盒旧磁带翻来覆去地听,怎么就听不够呢?我也问过母亲,母亲很平静地说:“闲着也是闲着。”
母亲60岁的时候查出患有心脏病,我们做儿女的心情都很沉重。一年后,母亲的病情稳定了下来,和正常的老人一样了,我也就渐渐放松了警惕。再去看母亲时,她依然捧着那台小收录机。那台小收录机里像装着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母亲的耳朵。
妻子的父母家住在180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我们很少回去看望。1998年除夕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母亲那里。告诉她明天一早就要走了。去孩子姥姥家过年。母亲叮嘱我说:“别空手,多买点儿东西带过去。去了以后帮着多干点儿活。”我一一答应。
傍晚,母亲下厨房炒菜,妻子照例抢着去做,可这一回母亲没有让步。
很快,母亲就炒好了两个菜,还煮了一盘大虾,鲜红鲜红,闪着晶莹的亮光。
继父不在家,我们四个人坐下来吃饭。母亲给我打开一瓶啤酒,知道我酒量有限。说:“喝点儿吧,剩下的浇花。”母亲给我和女儿的碗里各夹了一只虾,然后在盘子里挑了半天。挑出一只最大的夹到妻子碗里。说:“吃吧,新鲜的,你姐上午刚送来。”
离开母亲,在回家的路上。妻子惊喜地说:“阿康,你注意没有。今天晚上妈特意给我夹了几次菜。”我打趣道:“妈喜欢你呗。”妻子并不赞同我的说法,反驳道:“不,以前妈可都是给你俩夹菜,从来未管过我。”妻子说的是实话。我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我总不能告诉母亲该如何如何去做吧。所以遇上妻子抱怨时,我就诡辩道:“咱俩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妈给我夹菜不就等于给你夹了吗!”妻子不服。但以后的日子里,她依然像我一样对母亲百般孝敬。
正月初五上午十时左右,母亲去世的消息通过电话传到了岳父家里。一时间全家人都静默了。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火速赶回吉林,这时的母亲已经闭着双眼不能再看我一眼了,她躺在床上像睡着了一样……
跪在母亲床前,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唯有无限的悔恨。在内心里流淌不止。我后悔没能陪伴母亲度过她人生中最后一个春节,如果我不走,她可能也不会永远地走了……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又一次注意到了那台几乎时时陪伴母亲身边的小型收录机。我信手按下“PLAY”键,等了许久,却未听到任何声响。电池没有电了。我取出磁带,回到家里塞入我的录音机,立刻,扬声器里传出嘈杂的对话声,那居然是我和母亲的对话,不知母亲是什么时候给我俩的谈话录了音,那是一段十分随意又没有任何主题的母子之间的对话。我的鼻翼克制不住地颤动着,泪水涌出眼窝。母亲在阳光照耀下的花园里手捧收录机侧耳倾听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她分明是心中时刻装着我,而我却浑然不知啊!
母亲的晚年是孤独的,每天没有自己的儿女相守身边,没有知心的老伴相陪身边。她只好将儿子的声音装进一盒小小的磁带。并永久地珍藏在她孤独的心里。
可能母亲不会时时装在儿子心中,但儿子却永远装在母亲心中。母爱因此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