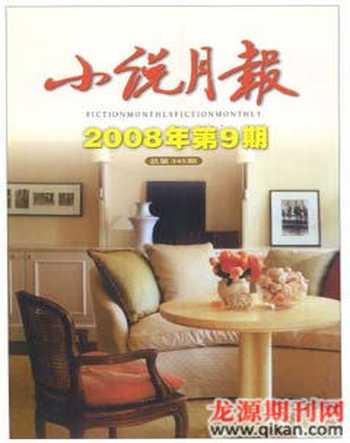小说二题
阿 来
秤砣
还在故事起始处,秤和主人就已经苍老了。
秤的主人有好几个子女,一大堆亲戚,身上却带着孤人才有的冷飕飕的萧索味道。让人觉得,除那杆孑然的秤,他就没有别的亲人与伙伴。在人们印象中,这个人从来没有年轻过。大家想想,这个人真是从来就是这样吗?所有人皱起眉头,做出打开了脑子里专管记忆的机关的样子,静默好一阵子,才有人开口,说,是,一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要是他是一个修行的人,就可以宣称自己已经一百,甚至是更大的岁数了。但他不需要这样的神秘感,他对每一个对他年龄感兴趣的人都说,五十六,我今年五十六岁零二十七天了。他喜欢准确的数字。其实,他也是个马马虎虎的家伙,但是,自从那杆秤来到他身边,他就喜欢准确的数字了。
秤本来是头人家的。大概有两百年的时间吧,整个机村就只有两把秤。一把大秤,一把小秤。大秤称的是粮食啦药材啦这些大宗的东西。大秤把老百姓家里的这些大路货秤过去,小秤把头人家从远处运来的值钱的东西称出来:茶、盐、糖和一些香料,有时甚至是银子与宝石。但宝石总是难得一见的,更多的还是茶与盐。糖和香料出现的次数比茶、盐少得多,又比宝石多得多了。过去,机村的日子是很缓慢的。就是远处的一个什么消息,在这个人口里沤上几天,又随另一个捎话人在什么地方盘桓一阵,真比天上缓缓飘动的云彩还要缓慢。
但一解放就不一样了。
被打倒的头人叹气说,共产党里都是些急性子的人哪!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头天晚上得到通知,剥削阶级的财产要被没收。但他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工作组就带领着翻身的积极分子把他们一家子从高大轩昂的屋子里驱赶出来了。那时候,自己家里连一点细软都还没有来得及收拾。不是头人不爱财,而是按照机村的老节奏,越是重大的事情越要来得缓慢。这天早上,头人还准备和家里人讨论一下怎么样能够尽量不失体面地搬出这座大房子,去住一幢下人的小房子,工作组和翻了身的下人就已经拥进来,把连早饭都没有吃完的一家子赶出去了。很多年过去,头人对此还耿耿于怀,他说:“妈的,最后一顿当老爷的饭也不让人吃好。”头人顾念的不是他的财产,而是他的面子,他做老爷,做人上人的最后一顿饭。一座大房子里是有不少财产,但架不住给那么多户人家一分,分到每一家就没有两样了。就说头人家的两杆秤吧。大的一杆,归了生产队。曾经称金分银的小的这一杆,就到了现在这主人的手上。他主动要的这杆秤。为什么呢?他说了一句古老的谚语,这句谚语给秤另外一个名字,叫公平。
他说,所以要这杆秤,就是让它当得起公平这个称呼。
而有人引用了另一则谚语,这个谚语里把秤叫权力,说想要秤的人就是想掌握权柄。那时,他的脸上就是很沧桑的表情了——私下里,大家都在议论,说,这家伙以前就是这种表情吗?奇怪的是,没有人想得起他以前是种什么样的表情了。倒是他有话说,权柄,那杆大秤才是权柄。是啊,交了多少公粮,是那杆大秤说了算,每人每户交了多少麦子与洋芋,也是那杆大秤说了算。而他那杆小秤呢?用时兴的话说,不过就是秤量一些小农经济的尾巴。这家人有远客来了,从那家人借一斤油,那家人有件喜庆的事,请客,需要集中每户人家那几两配给的酒,都是从这杆秤上过的。这秤过去在头人家里称过金银、宝石与鹿茸。到了他的手里,也就是这么些村民之间互相倒换救急的茶叶盐巴之类的东西了。秤有没有因此抱怨,人并不知道。但这杆秤的新主人确实没有因此抱怨过什么,他只是说:“越是这样,就越是要公平啊。”
村子里传说,他认为自己得到这杆秤也是不公平的,所以,要用加倍的公平来对待它。
在以斤以两论进出的交易中,秤的公平就体现在秤杆的平旺上。这一点,他对自己都没有太大的把握。终于,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杆秤固定在一个地方悬挂起来,就在他家东南向的窗户跟前,每天,一个固定的时候,太阳光会透过窗户照射到屋子里。当最初的太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就把秤——更重要的是秤杆投影在墙上,他把秤杆在水平的状态上固定住,然后,把投影的位置刻在了墙上。以后,有人再要淘换东西找他过秤的时候,就一定得是晴天,一定得是最早的阳光投射进他们家窗户的那个时候。他这么孜孜以求一杆秤的公平,人们虽然不以为然,但还是不想冒犯他。但凡一个人过于认真地对待一样事情的时候,别人都会小心一点,不要冒犯于他。但久而久之,面对这样一种仪式,前来称量东西的人也会生出非常虔敬的心情。
称东西的人总是提早到来。
他就把东西放上秤盘,然后,一起坐下来,静等着阳光透进窗户的那一个瞬间。
这个时候,有人会赔着小心说:“经常这样,真是太麻烦你了。”
他那张紧巴巴的脸松弛了,露出了笑意,嘴里说出很诗意的话来:“来吧,太阳出来了,看我们眼前是多么敞亮。”
但他这样的话并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么斤斤计较怎么可能让人心里温暖又敞亮呢?
太阳光照耀进来,他抿紧嘴唇,细眯起眼睛,一点点拨动那枚油浸浸的秤砣,直到秤杆的投影和墙上的刻痕重合在一起。
那个时候,每个工作组进村来都是分散了驻到村民的家里,叫做“同吃,同住,同劳动”。记不得是第几个工作组进村的了,秤砣家里也驻进了一个。这是个在会上热情坚定,而私下里却有些腼腆的年轻人。年轻人在会上大讲秤砣如此这般地使用一杆秤,对于破除小农经济思想,对于建立一大二公的社会具有多么多么重要的作用。他讲出来的意义太多,弄得秤砣自己都睡着了。
回到家里,他那张严肃的脸显得更严肃了,他说:“工作同志,以后,你不要再讲我这杆秤了,弄得人家都来笑话我。”
“你不是很坚持原则的人吗?为了坚持原则不是从来不怕人说三道四吗?”
“我做的我受。不要因为别人说我的好话,来让别人笑话我。”
弄得这个年轻人当时就无话可说了。接着,秤砣有些艰难地开口了:“工作同志,你是不是还欠我粮票?”
“我欠你粮票?”小伙子惊得差点就从地上蹦起来了。
按秤砣的算法,小伙子真的是差他粮票。差多少?三两。那个年代,工作组是不会受人招待的。他们住在农民家里,每天都按标准向主人交一定的钱和粮票。这次工作组的标准是每天五毛钱,一斤二两粮票。十天半月,就跟主人家算一次账,按标准如数交上钱粮。其实不是小伙子少交了粮票,而是秤砣算错了账。算错账的根子还在那杆宝贝秤上。
那杆秤是十六两一斤。
砣子当然也就认为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十六两一斤。工作组的年轻人给的是十两一斤,依他的年纪,也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十六两一斤这回事情。第一次算账,秤砣就发现他少交了二两,但他没有说话。他不好意思把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说出来,当然,他更怕说出来这样的事实会让犯错的对方感到尴尬。第二次,又少了三两。他继续隐忍不发。第三次,对上了。他想,年轻人已知错了。但是,这回,这个平常沉静羞怯的小伙子却在会上夸夸其谈,太多的好话让他成了别人眼中的一个笑柄。他并不想从任何一个地方得到表扬。他只是觉得,这么一杆秤落在自己手里,而不是随便哪个阿猫阿狗的手上,那他就要像一杆秤的主人。他甚至觉得,既然树有树神,山有山神,一杆秤这么重要的东西也应该有一个神。他甚至想让庙里的画师画一幅秤神的像供在家里。这样离奇的想法让画师吃惊不小。他关于各种神像的度量经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说法。秤砣走了,画师又是上香又是诵经,因为这样荒谬的想法把他只听清净之音的耳朵污染了。一杆秤让他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要失去这份敬意。但是,这个年轻人那些让人半懂不懂的话,让他成为了笑柄。他很生气,但他又找不到一个表示自己不高兴的有力的方式。于是,他终于忍无可忍把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甚至关涉到人性中贪欲的事情说了出来:“你差我三两粮票。”
粮票的数量很少,但是关乎一个人的品格,特别是当一个人具有把很小的东西赋予很多很多崇高意义的时候,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了。
“我怎么会差你粮票?”
看到年轻人涨红了脸,急急地反问,他慢慢伸出了三根指头。像他这种个性,说出人家欠自己东西,而且是区区三两粮票也很伤自己面子。俗话说,再重的鼻子也压不住舌头。但他常常就是鼻子压住了舌头。但要不动舌头,把话压在心上,自己多少还是感到有些委屈。他有些不好意思,又很高兴终于能够向别人指明使自己吃亏在什么地方。于是,他总是一片死灰的脸上涌起了通红的血色,并且坚定地伸出了三根手指。
年轻人掏出自己的笔记本,把记在某一页上的账目细算了一遍,笑了:“我没有欠你的粮票。”
“你欠了。”
年轻人又算了一遍,更加肯定自己是正确的。但他还是坚持说对方错了。他脸上一点犹疑的神色都没有,只是坚定地说:“你才算了两遍,告诉你吧,我在心里都算了一百遍了。”
“那把你的算法让我听听看。”
他就算了一遍。然后,是那个年轻人惊叫起来:“什么,你说一斤是十六两?”
“难道一斤不是十六两?”
秤砣把年轻人拉到那杆秤的前面,指着已经显出木纹的秤杆上一枚枚的金花,一一数来。年轻人长了知识,过去是有一种秤,一斤就是一十六两。年轻人明白过来,也不想解释现在的秤早已经是十两一斤了,就大笑,说:“对,对,我错了,我马上补给你三两粮票。”
秤砣眼里露出了满意的神情:“你这个孩子,谁要你还几两粮票。我只是要你不要算错了账。”他那张潮红的脸更加潮红了。这么一算,他在心理上就对这个人取得了某种优势。年轻人则意识到趁着他这股得意劲,正好做些启发性的工作:“秤砣大叔,这秤到了你的手里真是公平,可过去在头人手里就未必公平吧?”
秤砣陷入了沉思,脸上的潮红也慢慢褪去了:“已经倒霉的人,就不要再提了吧。”接着,秤砣改换了话题:“好了,我要到镇上去一趟,我用豆子去换些大米,给你——咦,你们是怎么说的,‘改善改善伙食。”
临出发的时候,年轻人把一斤粮票交给他。秤砣找不开。年轻人心里忽然涌上一个想法:“零头不用找了,你就到馆子里吃顿饭,粮票算我请的。”
他没有想要接受年轻人的馈赠,他只说:“那我反欠你一十三两了。”
年轻人洒脱地挥挥手:“我说过不用找了。”
秤砣就带着些豆子,还有他那杆秤上路了。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想,这也不是个不学好的年轻人。而今天,自己已经给这个年轻人很好的教训了。秋天的太阳把地上的一切都晒得暖洋洋的。他一步步走过那些干净的温暖的石头,草丛,木桥,穿过落尽了叶子的桦树投在地上的稀疏的影子,那些豆子在袋子里互相轻轻碰触着发出愉快的声响。好像没走多久,就走出了几十里地,就看到了镇子在太阳下闪耀着的白灰的墙与青瓦的顶。真的,秋天里,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显得那么干净,那样的从里至外,闪闪发光。
镇上吃国家配给粮的人喜欢机村的豆子,这些豆子干炒过后,膨松酥碎,是很好的零食。最适合看露天电影时揣上一把。当然,如果和肉炖在一起,又是另一种风味。镇上的人喜欢从配给的口粮中匀出一点大米,换几斤机村的豆子。有露天电影时,是孩子们的零嘴,下大雪的日子,旺旺的火炉上翻腾着一锅肉与豆子,也是日子过得平和的象征。
秤砣来到镇上,敲响了一家人的房门。主人打开门时,他已经称好了三斤豆子,手里稳稳地提着秤站在人家面前。主人也不说话,拿个瓷盆出来就倒豆子,倒是他提醒人家:“看秤。三斤。”
主人头也不回:“不看,不看,你的秤,放心!”返身又端了米出来,倒在秤盘里。砣子称了,倒回去一些,再一称,平了,这回,还不得他开口,主人就说:“谁不知道你的秤,不用看,不用看,放心!”
秤砣的脸上又泛起一片潮红,细细的眼缝里透出锥子般锐利的光。遇到热心的主人,还会搬出椅子,端出热茶,和他坐在太阳底下,闲话一阵乡下的收成。这一天也是这样,因为他去的都是相熟的人家。开照相馆的一家。裁缝铺的一家。卫生所的医生一家。手工合作社的铁匠家。铁匠老婆说:“你来,就跟走亲戚一样。”
他也差不多就怀着这么一种心情,走在从这一家到那一家的路上。
之后,他走到了镇子最西头的一个院落里。那是他每年用豆子换大米的最后一家。那家的主人是邮局的投递员。门口停着那辆驮着绿色邮包的自行车。
最后,他来到了镇上的人民食堂。他坐下来,掏出了一斤粮票。点了肉菜,还点了三两米饭。这是年轻人欠他的三两。算账的时候,麻烦出现了。在他一斤十六两的盘算里,人家该找他十三两的票。但他点了三遍,心里就有些急了,人家居然只找了他七两。他当然不知道粮票都是按新秤的计量,都是十两一斤。按十六两一斤算,人家确实少找了他。于是,在结账的柜台那里,就起了争吵。看热闹的人们围拢过来,听清了事情的原委,相继大笑。
秤砣拿出了他的宝贝秤,冲到柜台跟前,一声一声数那老秤杆上的金色星星。数到十六的时候,他头上汗水都出来了。但好奇的人们爆发出了更大的笑声。血轰轰地冲上了头顶,他狂吼一声掀翻了齐胸高的柜台。然后,举起秤就往那个收款员身上砸去。没抽到几下,细细的秤杆就折断了。于是,他举起了那个光滑油腻的秤砣,连续几下,砸在了那家伙挂满自以为是表情的脸上。直到警察出现,叫人把那个满脸血污的家伙送到医生那里。他才慢慢清醒过来。
他对警察说的第一句话是:“他少找我粮票。”
人们才齐声说:“老乡,你错了!”
“我错了?”
“一斤早就不是十六两,而是十两了!”
因为自己不骗人,主持公道,所以知道不骗人的表情是什么样子。他环顾四周,所有人的表情都不是骗人的表情。
“一斤东西怎么可能不是十六两呢?”
有人把一杆新秤拿到他面前,给他细数上面的金色星星。是十颗,而不是十六颗。他把乞求的目光转向警察。警察忍住了笑说:“跟我们走,秤早就是十两一斤了。”
秤砣就举着自己的秤给警察押着往派出所去了。他突然说:“那是我多要了他三两粮票。”
“你说什么?”
“那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不告诉我?”然后,他举起了那个秤砣,对准自己的额头重重地拍了下去,然后,就晃晃悠悠地倒下了。他觉得自己就要死了,不能当面再问那个整天宣扬新思想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告诉他普天下都换成了十两一斤的秤了。当然,他没有死成。只是从此再也不给人称秤,也不觉得能给什么人主持公道了。而那个年轻人,也因为这个错误,不等他出卫生院,就调离机村了。
从此,他就是机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了。又是十多年过去,伐木场礼堂里上演过一部彩色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是,一个反革命,用一个秤砣干掉了一个人。人们给这部电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难忘的秤砣》。说起这个名字时,人们突然想起多年前机村自己的秤的故事,再看见他时,就有嘴巴尖刻的人说一句:“难忘的秤砣。”
但秤砣自己并没有什么反应。一脸平静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后来,当新的流行语出现,人们也就将秤砣这个称呼给慢慢淡忘了。
蕃茄江村
查考字典,蕃茄不是中国的本土植物。
这种也叫西红柿的漂亮东西更不是机村的本土植物。
看机村那些蔬菜种植户,当省城来的大卡车拉走了地里的收成,在农业银行储蓄所走了一遭,腰上缠着的钱袋还很饱满,自然就会来到小酒馆里,叫菜的声音也很有底气:“酒!大份的蕃茄汁烧牛排!”好像他们跟这东西已经打过几十辈子的交道了。其实,这种植物在机村落脚生根,开花结果还不到三年时间。
当然,机村人知道这个东西还要早那么十几二十年。到底是十几年,还是二十年,经历其事的人已经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不是他们的脑子记不住东西,而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某种东西消失了,某种东西出现了,谁也不是历史学家,也分不清这出现与消失是偶然还是必然。
只有书呆子达瑟琢磨过这个问题。“蕃茄”,他皱着眉头说,“你们看,这个蕃茄的‘蕃,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嘛。”
“呆子又在说胡话了。”
达瑟可不管这个,自顾按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问问老年人,过去汉人可不叫我们藏族,而是叫‘西番。就是这个蕃茄的‘蕃。”
如今,机村的年轻人都上过学,也识得字,却没人有兴趣去深究这两个字的异同,一个有草头,一个没有那个表示是植物的草头。但的确有人回去问了。也得到了确实答案。过去,也就是解放前,人家是把这一方的人叫做“西蕃”。一解放,实行了新的民族政策,这种称呼就消失了,西蕃就改唤做藏族了。人们的这番考据功夫已经偏离了达瑟的思路。他想的是,既然有这个蕃字,说明这个东西出处,就该是在这个地方。本来,他曾经拥有的百科全书上说得一清二楚,这东西如何是从印第安人的美洲传布到整个世界。但是,一个农民,如何能够长久拥有一套百科全书呢?艰辛的生活早把他的树上的书屋和那些书都摧毁殆尽了。这些年,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偶尔,他的书瘾会发作一下,那也是青年时代激越情怀的遥远回声了。算了,就不说那些曾经如何被宝贝的书是如何零落与毁损了。只说,达瑟靠着这个名称推断蕃茄这个东西本该是出自西番之地,也就是机村这样的地方了。
且不说这个考据大有谬误,但说人们见了他努力思考的怔忡模样,不禁叹息,说:“眼看日子舒心消停一点,他的老毛病又要犯了。”
达瑟和大家一起大口喝酒,却用怜悯的眼光看发出同情之声的伙伴。
酒酣耳热之时,江村一个人不声不响,想着什么事突然自己就笑起来。
那些酒喝得头大的人都说:“嚯,又想起你的蕃茄罐头了。”
江村真的是想起蕃茄罐头的故事了。他笑道:“真是奇怪得很,那阵觉得味道那么奇怪的东西,怎么就这么顺口了呢?”
那是江村自己十二三岁时的事情。那时,和他同龄的孩子都在准备考县里的中学,他却已经离开了学校,一个人四处游荡。经常两三天不回家,他老爹也不着急。这家伙说:“反正读了中学回来也要这么浪荡,不如现在就去。早浪荡早收心,还来得及做一个好农民。”
江村每次回家,不但自己没有饿饭,还总能从怀里掏出点什么东西带回家来。有些人家,孩子根本不敢拿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回家。但江村老爹不管这个,他说:“好,这孩子顾家。”
这些浪荡的孩子去什么地方呢?其实也就一个地方。从机村顺着支线公路出去一段,在河口交汇之处,公路支线与干线交汇了。从这里往东是乡政府所在的镇子,往西四十公里,公路翻越一座雪山,盘山公路狭窄陡峭。那时,不但路不好,路上的卡车性能也不怎样。刚一上坡道,汽车引擎就哭泣般呜呜嘶叫。那速度就不用提了。机村的野孩子们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个地方,无事可干时,喜欢走了长路到这里来与汽车赛跑。在好几个路段,他们甚至能够跑到汽车前面。这个游戏竟然一批传一批,伴随了机村好几拨喜欢好勇斗狠的半大小子。他们来到路上,倾听着远方隐隐传来的马达声,然后,一声喇叭,汽车驾驶窗的玻璃上闪烁着阳光,从弯道处拱了出来。上坡了,在平路上飞驰时拖着的烟尘尾巴在蓝空下慢慢消散。
半大小子们就站在路边,等汽车开过,然后,一阵猛跑,终于跑到了汽车前面。在一个弯道上,汽车爬行得更慢了,他们就站在公路中央,对着挡风玻璃后面司机模糊不清的脸绽开得意的笑容。司机可不管这个,死死地踏着油门,让卡车呜呜嘶叫着往山上爬。他们要等到卡车都到眼前了,才一下子跳到路边。如是几个回合,又走长路回到村子里边。回家路上那份无聊与厌烦就不用提了。直到有一天,一个胆大的家伙爬到了卡车上面,并从上面掀下来一只木箱。木箱砰然砸在路上,那么大的声音把小子们吓得够呛,他们四散奔逃进路边幽深的树林,紧伏在地上。咚咚的心跳声震得耳朵生疼。卡车并没有停下。他们来到路上,看到箱子已经裂开。里面一些玻璃瓶子也裂开了。里面流出乌黑的浆汁。首先伸手蘸来尝试的大叫:“止咳糖浆!”
果然是止咳糖浆。大家一哄而上,吃得满嘴满脸。然后,躺在山坡上慢慢回忆刚刚结束的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细节。于是,一个生动的故事出现了,生动的故事成了这群小子骄傲的资本。
江村不属于这伙人。他年纪尚小。又过了几年,他才站到那段盘山公路上。他也遵守着过去那些半大小子们流传下来的规矩:只弄吃的东西。所以,他就遇到了蕃茄。第一辆车来了,他爬上去,掀开篷布,是一车厢整整齐齐的麻袋。他用刀挑开袋子,是盐。他跳下车,把舌尖上的咸盐吐在地上。舌尖上的苦咸味还没有过去。第二辆车就来了。他又上去了。这回,是一车留着很大缝隙的板条箱。他掀不动箱子,就用刀子起开箱盖,里面是白铁的小圆罐头。他揣了几罐在怀里,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还特意跑到路边,向着后视镜里的司机挥手。他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这路上,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故事里听得烂熟的细节了。这一切司机都是知道的,但还是不管不顾地踩着油门把车轰轰地往山口开。
江村从车上弄下来的是几个蕃茄浆罐头。
罐头上的彩色包装真是漂亮:画中的红色果子红彤彤水汪汪。江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样完美无瑕的果子:樱桃的质感,草莓的颜色,苹果的形状,自然应该把这个世界上所有果子的美味集于一身了。光想想这个,江村已经迫不及待了。手上的铁皮罐子密封得无懈可击,让他无从下手。他自然想到了刀子,这才发现,刀子落在了车上。而车已经翻越过山口了。要是他能忍耐,那就可以揣着罐头回到村子里。但他怎么等得及呢。于是,他用石头砸那罐头。只是轻轻一下,罐头就瘪下去了。再砸,这里瘪下去,那边却又鼓胀起来。他手里的力道加大了,狠劲地砸了三四下之后,铁皮的某一处裂开了。从裂缝中间,紫红色的浆汁冒了出来。他不知道罐头里不是完整的果子,而是怨恨自己大意丢了刀子,只能得到果子的汁液。他把嘴凑到裂缝边猛吸了一口,轻轻的一团黏稠就滑到了胃里,什么味道呢?他没有尝到,只是鼻子好像闻到了一种奇怪的气味。怎么样的奇怪呢?他也说不上来。反正很陌生,也很新鲜。是那些新事物——塑料啦、油漆啦、尼龙袜子啦,诸如此类的事物的气味。当然更是那些机村人从来不吃或没有吃过的东西——豆腐皮蛋的气味。
这回,他慢慢地吮吸,让嘴巴里充满了从未品尝的味道。
他有些失望,画上的果子那么漂亮,但是,味道却并不如想象的那样,而是……很……闪烁不定,很……像梦境虚幻的微光。
带着那种味道的奇异感觉,他揣上罐头走在回村的路上了。
他没有把罐头带回家,而是埋在了村外一棵树下。晚上睡觉前,他走到门外,看见了稀薄月光下那株大树的朦胧影子。睡觉前,他把两个字描在了手心里,明天好去问达瑟。
当写着这两个字的手掌摊开来时,达瑟很奇怪:“你在哪里看到这字的?不认识怎么会写?”
“我不告诉你。”
达瑟说:“蕃茄。”
“蕃——?”
“蕃茄。”
“蕃——茄?”
“对,蕃茄。”
“蕃茄!”
“对。”
江村嘴里一直念着那水果的名字,从苔藓底下把罐头起出来。他嘿嘿一笑,说:“伙计,我认识你了。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边说,他用刀子起开了罐头盖子,并叫了一声:“蕃茄!”
呈现在眼前的不是画片上完美无瑕的果子,仍然是一团黏稠的紫红色浆汁。这使他失望至极。
十几年了,每一次江村讲起这蕃茄的故事时,大家都像是第一次听见一样,大笑着用手拍打着桌子。什么东西一旦现身过,以后就会频繁出现了。很快,江村就在镇上的饭馆里见到了那东西。和他一道的人至今还想得起来,隔着橱窗,他像遇见老熟人一样大叫道:“蕃茄!”
他们尝试这东西和鸡蛋烩炒在一起的味道,和白菜煮在汤里的味道,最后,还习惯了把这东西当苹果一样生吃的味道。
农技员常常说这东西的营养是如何丰富,但机村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考究。但那农技员最初要在机村找一户人家试种蕃茄时,的确费了不少工夫。农技员说机村土壤的酸碱度,气温与日照,昼夜的温差,种植蕃茄都再合适不过。大家都对农技员说,你还是去找江村吧,他跟蕃茄有缘。但是江村不干。他说:“我知道,那是一个难对付的东西。而且,我也不喜欢它那怪怪的,说不出名字的味道。”
农技员说:“不要你喜欢,要城里人喜欢。”
终于,他好像给了农技员多大一个恩典,划出一块地试种一下。因为公路主线正在改道。改道后的公路主线不再翻越那个山头,而是从机村经过,并通过一条几公里长的隧道,穿过觉尔郎峡谷旅游区。夏天,蕃茄撑开了宽大的叶片,并不漂亮的花开过以后,青绿的果子一天天长大。硕大的果子,压得植株都要折断了。农技员指点他下种,松土,间苗,施肥。农技员还强迫他疏掉了植株上太密集的果子。就在隧道通车那天,他那些蕃茄也变红了。好像这些果子也跟机村人一样为这件事情兴奋不已。不久,真的有省城里来的蔬菜公司出很好的价钱买走了他全部的蕃茄。
第二年,他就是机村人种植蕃茄的师傅了。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去县里农技员那里咨询一番。当机村好几户人家地里的蕃茄都长出累累果实的时候,他睡不着觉了。要是省城那个蔬菜公司不来怎么办。农技员让他放心,但他的确放心不下。于是,农技员就让他去了一趟省城。看见了公司的大房子和四处去拉菜的卡车队。他放心了,回来,在县城和农技员一起在饭馆里小酌。江村说:“我给你讲讲我第一次遇到蕃茄的故事吧。”
“好啊。”
他就讲了起来。故事还没有讲完,讲到他在手心里写上那两个不认识的字,让达瑟辨认时,他自己笑了起来。他用手掌拍打着桌子,笑道:“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说我跟这个东西有缘分,这就是为什么你让我成了机村的蕃茄师傅!”
农技员只是又给他满上了一杯酒,说:“干!”
江村却很奇怪:“你为什么不笑?”
“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然后,农技员自己也大笑起来。
原刊责编 朱燕玲
【作者简介】阿来,男,藏族,1959年生于川西北藏区的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做过乡村教师、文化局干部、杂志编辑、主编。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后转写小说。著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及《阿来文集》(四卷)等。小说集《旧年的血迹》获中国作协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现为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