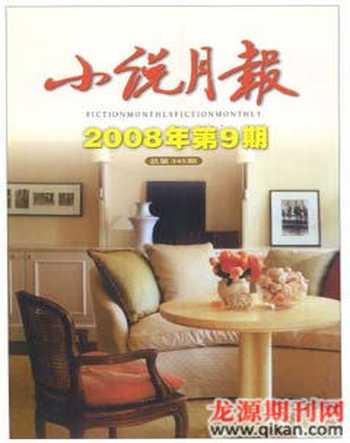夜行客车
再没有比深更半夜坐上一部来历不明的车更让人不安了。可现在我就坐在这样一部车上。车里空空荡荡,除了司机、售票员和后座那位一直低着头的男人,就剩下我了。那盏昏黄的小灯在我刚踏上车时短暂地亮过,但后来,它就熄灭了,车中一片昏暗。
窗外,是诡异的夜色,说它诡异,是因为这夜色中并非漆黑无物,而是充满暧昧、骚动、晦暗不明的东西。它们在这寂静的街道上游荡,影影绰绰,空气都被搅得波动了。唯有惨白的路灯一动不动,无言地靠近我们,又沉默着离去,如同一个个手举灯炬的幽灵。
我乘坐的这辆车从外形上看是一辆公交车,走的也是公交车常走的路线,而且每站必停,但我奇怪地发现,那些等候在站台上的人们没有一个登上这辆车。他们在寒风中竖着衣领,焦急地东张西望,却并不理会我们正停靠在他们面前。
售票员一声不响,似乎比站台上那些无动于衷的人们更加无动于衷。于是车门便叹息一声关闭,车轮重新启动。
我思忖着,为什么人们对这辆车的到达熟视无睹。是这车有什么异样吗?我回想起,自己是怎么登上这辆车的。半小时前,我刚刚结束了一个乏味冗长的学术会议,从人声嘈杂烟雾弥漫的会场里出来,太阳穴隐隐作痛,看看手表,已经差五分十点了。经验告诉我,要赶上那趟前往远郊家中的末班车,几乎是不可能了。但我还是决定试试。我冲出大楼,跑过楼前的草坪和大门前的守卫,跑过一个个正准备打烊的小店,像一只灵巧的羚羊那样奔跑着穿过马路(一声声刺耳的刹车声和咒骂声从我身后响起),穿过黑暗中一个个匆匆行走的行人,远远地,就看到车站上停靠着这辆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一辆平常的公交客车。黑暗中,车门上方那盏灯孤寂地亮着。是去灵山的吗?我问。之后,我登上了车。
车门在我登上第二级踏板之后就关闭了。汽车启动,仿佛它是专为我一人等候在那里的。我一边暗自庆幸一边挪到后面给自己找了个座位坐下。我坐在靠后倒数第三排,靠近车窗的地方。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整个车厢空空荡荡,除了那位一直背对着我们的司机,坐在前门一动不动的售票员,仅有的乘客除了我,就是后座的那位男人。
那男人一直低着头,像打盹。当两旁的路灯偶尔划过车厢时,我发现他头戴一顶暗色的,在黑暗中介于红、褐甚至是黑色之间的鸭舌帽。这是一种奇怪的装束。我知道鸭舌帽曾经很流行,但那是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当时正上演着一部电视剧《上海滩》,剧中那位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男主角许文强就戴一顶风流倜傥的鸭舌帽,于是一时间,这座城市里大大小小的男人都戴起了鸭舌帽而且像许文强那样压低着帽檐。不过时尚瞬息万变,现在,你很难在这个城市看到一顶鸭舌帽了。我再次回头打量,发现他不仅头戴这诡异的鸭舌帽,连身上那双排扣长呢子大衣,格子呢长裤子,尖头白底花皮鞋,都显然与时下流行的不同……而且,他胳膊上竟然戴着一只红袖章!猛然,我意识到这人简直就是从几十年前上海滩的老照片上走下来的,这个发现让我心头一恍惚。
这人也许是从某个电影或电视剧的拍摄现场回来的吧,我努力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了让自己安心也为了转移注意力,便开始回想刚才会议上的形形色色。我参加的是一个学术会议,但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谈学术,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学术之外的事情,例如自我吹嘘(和某某大师同台演讲,和某某高官共进晚餐,自己的某某作品被列入某某著名系列,自己的名字被某某词典收录等等)。这年头,你若是想在学术会议上去听学术,那真是犯傻,就像一位作家对我说的,你想听作家谈文学也是犯傻。那作家们在一起说什么呢?有一次我问。升官发财,狗男狗女,吃喝嫖赌,坑蒙拐骗,什么都行,除了文学,他说。
我一定是无意间打了一会儿盹,睁开眼发现客车正驶过一座水泥大桥,进入了郊区。一轮支离破碎的月亮在桥下闪烁着粼粼波光,一排排白杨树在路灯的映照下如满树繁花。人烟变得稀少,道路开始颠簸。站与站之间的距离已然变长。当客车在郊区某片落满尘土的草丛前停下时,我看到几个年轻女子站在那里等候着,她们是附近一家大商场打烊后回家的营业员,和大多数外地打工者一样,租住着附近郊区那些价格便宜的农舍,这趟开往灵山郊区的公交车是她们上下班的必需工具。但让我意外的是,当车门在她们面前喘着气豁然打开的时候,她们竟然谁也没有朝这里望一眼,更别说朝车门跨近一步,她们的眼睛仍然望着别处。
车门叹息了一声关上了。我目瞪口呆。
当汽车再次开动时,我忍不住了。为什么人们都不上这趟车?我说。没人回答。司机一动不动,眼睛望着正前方,这可以理解;但无论是我前面不远的售票员,还是我后面的那位男乘客,都没理会我,这让我觉得不可忍受。为什么人们都不上这趟车?我再次问。提高了嗓音——这趟车不是去灵山的吗?
这趟车是去灵山的,那女售票员终于说话了,她的面目在黑暗中朦胧不清,声音也含糊不清,但我还是听清楚了。
那人们为什么不上这趟车?我追问。
我感觉有人拉扯了一下我的袖口,回头,那男人已经凑到了我身后。别说话,他低声对我说,暖暖的带着烟草味道的呼吸吹到我耳朵上,你难道什么都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我诧异地问。
奇怪,你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看见吗?
看见什么?我看见这趟车停靠在站台上,就上了这趟车。我看见了这趟车,就上来了。就这么简单。
啊,啊,那人笑了,我明白了。来,抽口烟。他从衣兜掏出一包烟。看见我摆手拒绝,他从里面抽出一支,给自己点燃。当打火机的火苗猛然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眉毛黑而浓密,低垂的睫毛上方的眼皮边,有一道小小的伤疤。这伤疤让我的心猛然一动。
请问——我迟疑着说。
嘘——他将手指放在嘴唇上。打火机灭了,他的脸又湮没在黑暗中。只是随着烟头火光的一明一亮,他的脸再次伴随着浓浓的香气隐约可见。现在你想起什么没有?他问。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我老老实实回答。
刚上车的人都会这么说,他简洁地说。
那你呢?难道你上车很久了吗?可据我所知,这车的起点距我上车的地方也不过三四站。所以,你顶多比我多坐了三四站……
这趟车比你想象的,走的远得多。
是吗?我迷惑了,这不是去灵山的车吗?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他的声音带着笑意,你现在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像我,闭上眼睛打打盹,时间就过去了。
谢谢,我不困。我马上就到家了。
你不会很快到的,他说。
到没到家我比你清楚,真是岂有此理,我有些生气了。
不信你看看表。他并不生气。
我看看手表,表盘在黑暗中影影绰绰。我看不清楚,我说。
我给你借点光,他凑近我,打着了打火机。
表上的指针指在夜里十点差五分。
前面我说过,我从会场出来的时候看过手表,当时的时间正是差五分十点。也就是说,从我冲出会场跑过街道上了汽车到现在,行驶了这么久,竟然没有花费一分钟的时间!
这不可能!我诧异,明明过了这么久——这表难道停了?我将表凑近耳朵听——它仍然十分正常地、滴答滴答地走着。
有时候不正常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他不慌不忙地说。
我在篮球场上奔跑着。裁判员尖锐的哨子声在我身后响起,我知道,我只有短短的十秒了,而我必须在这十秒之内把手中那只篮球投进篮筐里。那只球此刻正在我手里,它沉重、巨大,上面沾满汗水和沙砾,而我此刻也并不是在奔跑,而是坐在球场沙砾遍布的土地上艰难地挪动着——确切说这球场其实已经不是球场,而是一片粗糙的沙滩——而我的两条腿已经断了,它们被打上了沉重的石膏,如两只冬眠的被冻硬的动物般并排躺在地上,因此我只能抱着那只沉重的球,一边徒劳地挣扎着想朝前挪动,一边无奈地看着人们呼喊着在我身边跑来跑去。他们推推搡搡,他们带着汗臭的腿脚不时撞到我,他们像盲目的潮水那样一忽儿朝前又一忽儿朝后涌去,他们眼睛充血头发竖立汗水淋漓气急败坏,他们不是在打球而是在蜂拥着寻找、扑向什么,我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他们在找篮球,就是我此刻抱在怀里的这只篮球,可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球在我这里!我声嘶力竭地喊,但我的声音就像被巨石堵在深深的井底,被这无边的喧嚣吞噬了……一个人终于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他朝我俯下了身子,我立即明白此人是我的一名队友,一名中锋,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是我看到了什么?他的额头上,一缕鲜红的血缓缓流下来……
在醒来的刹那,我恍然觉得这人有些眼熟,肯定是我的一个旧交或早年的朋友、同乡,可他是谁呢?
汽车仍然在黑暗中运行,望着窗外朦胧的田野,我模糊地想,幸好,这是一个梦。但某种焦虑和紧迫感还是留在了我的身上,如一条黏糊糊地贴在我脊椎深处的蚂蝗,让我无法挣脱。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汽车照例一无所获地关上车门,照例朝着前方的黑暗开去。我注意到光线此刻变得稍微明亮,但这光亮不是来自天空而是来自地下,来自那些暗夜中的水洼的反光。这么说快到家了,我心想,大概还有三四站的样子吧,到时候再朝门口走也不迟。
很多事情被错过的原因不是延误,而是过于心急,我身后一个声音说。
我回头,发现那位同伴正将身子探向我。
真奇怪,他似乎总能猜透我在想什么。
我对数字颇有研究,他低声说,像是透露一桩事关重大的秘密——你把你手机号的最后一个数字改一下。你的幸运数字是二和三,凶险数字是五和九。因为你是1977年生人。
我脊背上的皮肤一激灵。他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最后一个数字恰好是九,而我确实是1977年出生。
像是明白我的恐惧,他微笑了,你别紧张,等你认出我来,你就明白了。
我恐惧地盯着那张在黑暗中模糊不清的脸。我想起来了,这正是我在梦中的那位队友,那位中锋。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他到底是谁,我到底是怎样认识他的,他是我的熟人、亲戚或朋友?
那只球,还在你手里,因此你依然有机会。他低声,诡秘地告诉我。
我浑身汗毛一紧。
我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将情报尽快传送出去。这情报关系到前方我军将士的生死——敌人已经意识到我军的意图,并在这支部队前方的道路上用重兵设置了伏击圈。很明显我们内部出了奸细,他不仅泄露了我军的意图而且也使我的这次送情报的任务变得十二分的危险。但此刻已经顾不了许多,当务之急是必须追上那正在行进的大部队并让他们改变路线……
秋日的黄昏凉爽而暗淡,风铃在屋檐下发出清脆寂寥的声响,一抹黄叶在我穿着长衫的肩头滑落下来。我跟随一位穿白色长裙的女子沿着爬满长春藤的回廊,踩着落叶来到庭院深处一间昏暗的密室里。女子步履轻快,那种无声无息的猫一样的姿态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她从口袋里利落地取出钥匙,打开门,带领我走向房间最里面一只五斗橱前。房间窗帘低垂光线昏暗,弥漫着浓重的檀香气息,奇怪的是我能清晰地看出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用红色锦缎包着的盒子,打开,一只小巧的罐子出现了。这是一只小陶罐,比鸡蛋大不了多少,在黑暗中闪烁着经年被摩挲发出的那种亮亮的光泽。她轻轻打开罐子,一个小巧的东西在里面神秘地蛰伏着;我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只绿头蟋蟀,长长的触角呼吸一般颤动着。女子只让我瞥了一眼,马上盖住了罐子。
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它的声音,她低声说。一切都在它的声音里,你明白了?
我肃然。我知道,这不是一只普通的蟋蟀,而是一只情报蟋蟀,所有的奥秘所有的情报都在它独特的叫声里,只有最最专业的情报人员才能破译这叫声。可是,我并没有听到它的叫声。我踟躇着是否要验证一下它是否具备那种叫声,但又明白,按照地下党的规矩,这个问题是不可以问的。
像是明白了我的疑惑,女子说:你不可能听到它的叫声。它的叫声是不可能被听到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声音。它的叫声就是沉默。
我疑惑,又似恍然。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女子一把拉住我,快走!
我被女子拉着,弯下腰穿过一个墙洞,穿过一间间废弃的房屋,终于从一个暗道爬了出去。一扇废弃的铁门吱呀一声被打开,我出门,看见那个篮球中锋正站在门口,手中握着一把枪。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说着,他瞄准我。
现在我知道我仍然在车上,我也知道,刚才我又做了一个梦,而这第二个梦竟然和第一个梦是有关联的。在第一个梦里,人们寻找的是我手里的篮球;而第二个梦中,情报是藏在一只罐子里的蟋蟀的声音里——那么情报呢,真正的情报到底在哪里?我的心猛然停止了跳动:那放着蟋蟀的罐子现在在哪里?……难道说我已经将那罐子放进了手中的篮球里,并且为了掩护,又将里面装满了沙子?可这样那蟋蟀会不会因碰撞或窒息而死?或者说,那罐子并没有在篮球里,而是仍然在那庭院里,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不是拿起罐子却拿了篮球?
我的脊椎深处一阵发麻,一种深刻的绝望让我动弹不得。汽车的轰鸣声中,我隐约听到了我身后抽动扳机和上子弹的声音。是的,我终于想起他是谁了,我想起来,在某次地下党的会议上,此人曾口中叼着香烟坐在我的身后,就像此刻正坐在我身后一样;之后化装成军警的我的同党冲了进来,时间只够我从椅子假装扑倒在地,而就在我倒地的刹那,我听见密集的枪声在我头顶上方响起……当军警从地上扶起我时,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看看我身后的那人。
于是,我们一起走到我身后这个已经倒地的人面前。他双目紧闭,身上满是弹孔和血污。我从军警手中接过枪,对准那个有着伤痕的眉毛,扣动了扳机……
我闭上了眼睛。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回到梦里,不是回到那个沙滩上的球场,而是回到更远的地方,回到那个飘荡着落叶的庭院里。我知道那只放着蟋蟀的罐子依然在那里,我必须找到那罐子……我对自己说,你得记住,不是篮球,而是罐子,一只罐子,一只放蟋蟀的罐子……
我真的又重新看见了那罐子,它现在被擦得锃亮,放置在一只高高的紫檀木书柜的顶部。我看见母亲年轻的背影——她的发髻绾得高高的,插着一只白玉蝴蝶,一颗小小的红玛瑙珠子在下面晃来晃去。她正在擦书柜。我坐在床上玩耍着。我还是个孩子,正在床上,把玩着一只小小的绿色蟋蟀——那是一只塑料蟋蟀,我将它放进嘴里咬着,黏黏的口水顺着我的嘴唇流下来,挂在被我咬得坑洼不平的蟋蟀胡须上面;一抹阳光正从窗外照进家里,在砖头地上投下斑斑点点。母亲现在已经擦到了柜子的顶部——她的眼睛看不到上面,为了将手中的抹布擦到柜顶,她使劲踮起了脚尖,她手中的抹布正在使劲朝前伸着,伸着,朝着那罐子伸去,她看不到那罐子的确切位置,但我却能看到;奇怪的是,此刻的我,这个坐在床上玩耍的只有四岁的孩子,却停住了手,我凝神望着那罐子,我预感到那罐子的重要性,我意识到那罐子将对我未来生死攸关——我看到,母亲那命中注定的手碰到了那罐子,那受到碰撞的罐子已经倾斜了,倒了,并顺着书柜顶部,无可救药、命中注定、势不可当地滚落过来……
当我从轰鸣中惊醒过来的时候,我听见了一声巨响,不知是刹车声,还是子弹的呼啸声。
然而我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梦的间隙,就像我永远也找不到那份真正需要传送的情报并把它送出去那样,我将永远乘坐在这辆永远到不了家也永远没有终点的车上。
【作者简介】钟晶晶,女,辽宁海城人,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记者、编辑多年。2001年起从事自由写作,已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多篇作品被各种选刊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昆阳血骑》、《李陵》、《黄羊堡故事》,小说集《战争童谣》、《你不能读懂我的梦》等。小说《战争童谣》获1997-1998年度《解放军文艺》奖,《我的左手》入选2005年度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现居北京,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