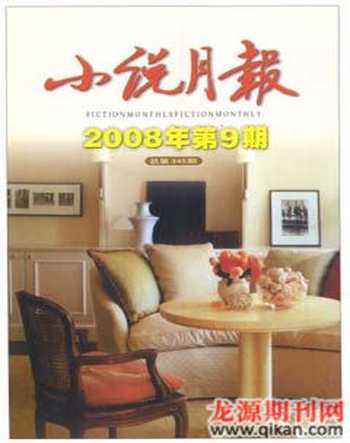跟月亮结婚
红 柯
中午十一点马一鸣和李海莉领了结婚证,就等着举办婚礼了。这时马一鸣的手机响起来,老总用试探的口气告诉马一鸣,有一大宗业务,最好你去做,效果会更好,当然喽这要看你方便不方便。大家都知道马一鸣马上要结婚了,老总显然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当然也透着老总的精明,老总很含蓄地告诉马一鸣这宗业务完成后马一鸣的实际收益,那是一个很诱人的数字,马一鸣忍不住把手机从右耳换到左耳,同时也看了李海莉一眼,李海莉给他一个肯定的眼神,马一鸣就答应了。老总说:两小时后他们的车来接你。
以往都是挤班车,老总不忍心让一个快做新郎的得力干将受委屈,就非让对方派车不可。其实人家的车一大早就出发了,快要到奎屯了,那时候老总就知道马一鸣不会拒绝。
剩下的时间恰到好处,马一鸣和李海莉去一个安静的饭馆吃饭,南方风味,清蒸鳜鱼、西芹炒百合、蘑菇排骨汤,主食是米饭,全由李海莉做主,李海莉已经进入主妇角色。李海莉的父母是江苏支边青年,依然保持着南方人特有的精致的习惯。李海莉一直在改造马一鸣这个真正的西北土著。马一鸣吃饭不讲究,大盘鸡揪片子拉条子便是天下最好的美食,跟李海莉吃饭等于去了一趟江南,在她家吃饭就更讲究了。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李海莉连鳜鱼都点了。平时都是鱼香肉丝什么的。李海莉不停地给马一鸣夹鱼,都是扒了刺的鱼肉,大半条都让马一鸣吃了,连鱼的汤汁都浇到米饭上。李海莉是不容反抗的。李海莉更像马一鸣的老总,李海莉同志说了:“下礼拜就举行婚礼,这是你多干的一份工作,不过呢,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又多出一笔收入。”李海莉同志跟所有的老总老板领导者一样,话到紧要处总要停顿一下,李海莉同志跟老头品酒一样呷一小口蘑菇排骨汤,微微一笑:“我们旅游的城市可以加上杭州了。”在原来的计划里有李海莉的老家江苏一个小县城,重点是大上海,从上海直接回新疆,体现着李海莉一贯的少而精的战略思想。这个天堂般的杭州是计划外的收获,是个意外的惊喜。马一鸣跟老总通电话时,李海莉就当机立断用她漂亮的丹凤眼给马一鸣下了命令。用李海莉的话讲:这简直是老总给你的一个天大的人情。马一鸣有点跟不上李海莉的思想,李海莉同志只好深入浅出地点破这个秘密:“同志呀,这于公于私皆大欢喜的事情不是人人都可以碰到的。”李海莉同志进而伸出纤纤玉手弹了一下马一鸣的脑袋:“说明你小子人脉很旺呀。”
在大家眼里马一鸣是个很精明的人,生意人嘛,能干到部门经理,备受老总重视就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标志,可在李海莉跟前,马一鸣的脑子就不够用了。李海莉绝不像那些聪明女子那样用污辱性的语言对待自己的未婚夫,李海莉是和风细雨式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一个含笑的眼神,一个细腻的动作,比如手指比如胳膊肘,就这么一点一点剥掉了马一鸣这个西北农民儿子身上厚厚的尘土。在大家眼里,马一鸣他妈的太顺了,从偏远的农村小学县城中学读到乌鲁木齐的大学,毕业实习在新兴的城市奎屯,干得不错,就留下了。一年后爹妈上下一新,两年后房子翻修,上初中的妹妹有了自行车,又过两年,带着漂亮洋气的李海莉回一趟老家,在村子里的轰动都不用细说了。交上女朋友的第三年,马一鸣有了自己的房子,就意味着他在城里真正安家落户了。记得刚认识李海莉时,马一鸣才感觉到自己是个老土,念了四年大学、工作了三四年,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呀,衣着打扮很时尚,李海莉走进他的生活就像他当年怀揣着大学入学通知书第一次走进乌鲁木齐一样,惊慌中透着淳朴。李海莉就像一个艺术大师,在他的淳朴上增加着精致。
吃饭四十五分钟,步行十五分钟到新房休息一个小时,接马一鸣的车就到了。喇叭在楼下响。马一鸣招呼李海莉一起走,李海莉马上要去单位,李海莉说:“你先走,不要等我。”马一鸣就急了:“顺车送一下嘛。”李海莉就用她的微微一笑加上妩媚至极的轻轻摇头,就让马一鸣安静下来了。马一鸣下楼的时候还是不明白李海莉的用意,马一鸣坐到车里的一刹那一下子就明白了,因为他进入了生意人的角色,是生意上的合伙人派来的车,李海莉坐进去确实不合适。马一鸣忍不住朝楼上的新房望一眼。新房在三楼,这时候窗帘拉开一角,李海莉笑着跟他招手,看着车子缓缓离开,李海莉那灿烂笑容久久不散。
没人打扰马一鸣,司机和陪司机来的人都不吭声,把美好的空间留给马一鸣,让马一鸣慢慢享受。出了市区,过了五公里,马一鸣自己打破了沉默,跟人家打招呼。司机不认识,司机旁边的人跟马一鸣挺熟,业务上有来往嘛。那人说:“两个月没见,你胖了。”“我胖了吗?”马一鸣摸自己的脸。那人笑:“自己胖是摸不出来的。”“那是那是。”马一鸣的手就收起来了。那人说:“咱们认识有些年头吧,你一直是紧绷绷的,处于高度警觉的临战状态,你咋就一下放松了?”马一鸣当然不能告诉人家他刚领了结婚证,下礼拜他就做新郎,马一鸣胸有成竹,就给人家微微一笑,那笑容简直是李海莉的翻版。
闲聊开玩笑,就好熬时间。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就是不聊女人,女人在心里装着呢,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女人,生怕受到损害,就小心翼翼地捂着,捂紧。有那么几次,快要说到黄段子了,快要见荤了,马一鸣成功地把话头引开了。马一鸣自己都奇怪自己有这么一副好脑子,马一鸣甚至怀疑李海莉就坐在他身边亲自坐镇指挥。那人跟司机坐在一排,后排就他一个,他频频往身边看,给人感觉他身边有人呢。每当他成功地化解对方的危险话题,对方就不甘心地扭过头往后看,那是满脸的惊讶与困惑呀。都是熟人嘛,以往都讲荤话讲黄段子呀,这马一鸣是咋啦?尤其重要的是李海莉那张笑容灿烂的脸出现在窗帘的一角,不但给马一鸣留下深刻的印象,车里那两位也同样印象深刻呀。人家就猜他们的关系,话题就老往这方面扯。马一鸣越来越狡猾,完全可以用狡兔用老狐狸来称呼了,有好几次他都在问自己,谈谈李海莉又有何妨?告诉人家李海莉是他老婆人家就不说黄段子不说荤话了。可直觉告诉他李海莉不喜欢这样。马一鸣惊出一头汗,马上庆幸自己没有犯路线错误,及时把话头引开了。他又一次为自己的灵活与敏锐心中喝彩。已经不用狡兔和狐狸形容自己了。马一鸣的脑子多好使呀,一边与对方胡吹海聊,一边给自己开表彰会,而且及时地总结经验。那经验只有一条,就是马一鸣同志完全放松了。就是傻瓜也明白,人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超常发挥。对方应该明白,打马一鸣上车,他就看出来马一鸣胖了嘛!心宽体胖嘛,体没胖,是心宽了,开朗了,放松了嘛,咋就忘了最初的印象呢?对方的错误,是构成自己正确的基础呀。就让他继续错下去吧。马一鸣誓死捍卫自己的新娘,马一鸣真理在握,理直气壮。关键的问题是马一鸣同志彻底地放松了。
车子停下来。新疆大地,车子疾驰如飞,但要停那么好几次,车上的人要解手,俗称唱歌。大漠就是辽阔的厕所。往路边一站,就可以自由发挥了。三个大男人站在两个地方撒尿。马一鸣独处一处,跟高压水泵一样突突突,浑身颤抖,干燥的荒漠土着火似的冒起白烟,根本见不到湿痕,白烟升起散开。一只四脚蛇亲眼目睹了马一鸣酣畅淋漓的撒尿过程。马一鸣系裤子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条手指长短的四脚蛇,它有一对小而亮的眼睛,就针眼那么大,那么清晰,趴在干燥的荒漠上,身体跟干土一个颜色,不留神还以为是枯枝败叶呢。这是大漠常见的小生物,也是马一鸣小时候的亲密伙伴。乡村生活总是跟牛羊马驼野兔蝗虫四脚蛇连在一起。还有冲天而起的野火。这些乡野的孩子们总是点燃干沟里的荒草,野火冲天而起,整个荒原成了轰轰燃烧的火炉。这些景象全都凝缩在四脚蛇的小眼睛里,跟屏幕一样让时光倒转,又让记忆复苏。四脚蛇站起来了,就像大地竖起的大拇指,在赞扬他。他还认识四脚蛇。小家伙功夫过硬,直挺挺站着,跟荒漠卫士一样,车子开了,它还挺着,好像在招手。
第二次解手的地方是在戈壁滩上,黑石头就像涂了漆皮,他在手里掂了掂又丢下了。
在路边饭馆吃过一次饭。饭馆后边有一棵白杨树,树叶闪闪发亮,哗哗喧响,万里无云,天蓝得让人吃惊。大家埋头吃饭,没人注意树叶和蓝天。马一鸣还是到树跟前去听了一会儿,好像树顶上有人在讲演。马一鸣好久没听到树叶的哗哗声了。回到车上,人家跟他说话,他都是啊啊,跟哑巴一样,人家就不理他了。后半截路,马一鸣一直没说话。不等于马一鸣冷漠无情。他满脸兴奋,眼睛亮晶晶的,全神贯注看外面的戈壁滩。猛然出现的小块绿洲,转瞬即逝,恍若梦幻,后来又出现骑马的哈萨克牧人,赶着一群风尘仆仆的羊,车子很快就把羊群和牧人甩开了。前边那两位大概觉得太冷落马一鸣了,就嗨嗨喊他,“想啥呢?丢了钱包是不是?”这回马一鸣没动脑子,不假思索地说出心里话:从四脚蛇到黑皮石头到白杨树到牧人和羊群,“这些年忙着挣钱,忙得没日没夜,连这些身边的东西都认不出来了,我都怀疑我是不是新疆人了。”这显然是个挺严肃的话题。马一鸣把这些都归功于这次出行。马一鸣与其说是袒露心声,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从中学就开始进入紧张状态,大学都没有松懈,走出校门,更是万分紧张。用熟人的话讲他整个人都是紧绷绷的,年轻气盛,精力旺盛,心气很高,老总总是把大宗业务交给他,他总是给公司带来极好的效益。李海莉的出现加快这种高速度。精明女子是催化剂,是发动机,是润滑油,是一股让人亢奋的力量。直到今天上午十一点,把结婚证领到手,他都听见自己长长出口气,正好埋头签名字,没让李海莉觉察到他这种可怕的情绪,李海莉是快马加鞭的主儿。在下礼拜举行婚礼之前,他可以长长地松口气了,他可以彻彻底底地松弛上那么一阵子了。婚礼肯定要紧张起来的,婚后呢?当然更紧张。不过那已经不要紧了,有这么几天的空余时间,他完全可以养精蓄锐。以后呢?他没想那么远。他还是享受目前的放松状态吧。他看外边的蓝天白云。他要仔仔细细看看蓝天有多么蓝,白云都有什么形状。
一群野马似的白云驰过天空,巨大的投影在地上移动,车子就跟在投影后边,好像车子就是云的投影。这样的话,真正的车子应该在天上了。他果然看到一朵小车模样的云,但要比车子柔软祥和舒展,不是发动机和轮子,是一股自由自在的力量随心所欲地在天上伸展。没有风,云自己在运行,没有任何目的,连灯和喇叭都没有,连窗户都没有,它只是概括了车子的大体形态,像车子又不像车子,就像一个绘画大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车子的神韵。车子进入阿尔泰山大峡谷,云依然相随,依然保持车子的神态。峡谷转弯的时候,云正好爬过山顶,就像山的灵魂出窍一样。车子拐过山峰得好半天,给人的印象云一直悬在车顶,就不是山的灵魂出窍,而是车的灵魂升到天上了。车子突然下降,奔向山谷底部的小盆地。
要去的那个县城就在山间小盆地里。盆地上空停了一大半云,就像海港停泊了许多巨轮一样。在马一鸣眼里,整个县城的灵魂就悬在那些安详的云里。
从车子里出来的时候,马一鸣那么从容舒缓,对方的部门经理也吃了一惊。都是老熟人,马一鸣一向精明干练,利索,曾有人怀疑马一鸣不是大学出来的而是特种兵训练营出来的。人家以为认错了人,马一鸣上去抓住人家的手,喊人家的名字,人家才缓过神。
晚宴上大家都说马一鸣胖了。生意人对灵魂对心态对精神不感兴趣,弦绷得太紧就瘦就精神,弦松下来就有胖的感觉了,另一层意思就是慵懒不精神。
这宗业务两天就处理完了,马一鸣的脑子简直不是人脑,处理结果报告给老总,连老总都感到意外,尽管老总想到结果可能比较顺利,如此顺利还是叫人吃惊,老总用一句话总结,你的业务水平整整上了一个台阶啊,言下之意,在年终的时候要奖励的。对方对马一鸣是钦佩至极。对马一鸣的老总就有些恨了,狗日的把一个快要结婚的新郎倌打发上阵,男人的成就感之一就是跟心爱的女人领本本子,马一鸣顺手牵羊把情感的成功扩大到事业上了。这是对方事后了解到的,一个电话打到奎屯,马一鸣最近有什么好事?天大的好事嘛。接他的人就明白了他们在窗口看到的微笑的女人是马一鸣的新娘。这狗东西捂得那么紧,给人家的印象好像是情人不是爱人。直到现在,狗日的还是把话题往外引。只能证明俩人感情好,再纠缠就没意思了。现在真正松懈下来的是对方,车子接马一鸣回来,又跑阿勒泰市了,两天以后才回来,另一辆是老总的专车,随时听老总调拨。马一鸣就有两天闲暇时间,李海莉说了:放松放松,出去转转,山里空气好。
马一鸣就懒洋洋地在街头溜达。住在县城最好的宾馆,县城就两条大街,一个小时就从头走到脚。人也不多,都是慢腾腾走路,汽车喇叭像鸟叫,群山腹地,太安静了。宾馆的饭也吃腻了,街上任何一家饭馆随便,公司挂账,填个名就行。马一鸣出道以来还没有这么自在过。他乐意在小饭馆里吃饭,有人情味嘛。
他在小饭馆吃第一顿饭的那天中午,街对面响起琴声,不是冬不拉也不是都它尔马头琴这些新疆常见的乐器。叮叮咚咚,就像泉水跳跃,就像云上山顶,轻飘柔曼,清脆悦耳,马一鸣都能看见自己的耳朵跟马耳朵一样在动,耳朵大了,薄了,整个脑子跟清水洗过一样。一群孩子围着弹琴的人,大人也围上去了。看不出弹琴人的模样。马一鸣的一切都慢下来了,跟牛吃草一样细嚼慢咽。这些年,李海莉把马一鸣的什么都改造过来了,包括吃饭的吧唧声,喝汤的咕噜声,唯一没有改过来的就是吃饭的速度,风扫残云的劲头没有了,但大舌头一忽隆就下肚的粗放型进食习惯一直没变,速度就意味着粗糙啊。李海莉同志显然把这一顽疾列入婚后的一五计划,而且是重中之重。如果李海莉同志现在过来目睹一下琴声中的马一鸣吃饭,她会感到十分欣慰,她会用录音机把这琴声录下来,作为未来小家庭的用餐进行曲。马一鸣不但细嚼慢咽,而且一口一放筷,完全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吃饭方式。马一鸣甚至相信这个弹琴的人是专门为他而奏的。
马一鸣就过去了,也不往前挤,缝隙里可以看见是一个破破烂烂白发白须的老头,那把琴像古老的弓箭,六根弦就绷在弓上,发射出的叮叮咚咚的乐声直抵人心。地上摊开一张白毡,老头就坐在毡上,琴也放在毡上,还空出大片的毡,大家就把钱币、奶子疙瘩和馕放到毡上。再仔细看,老头是个瞎子。这是中亚细亚典型的行乞方式,用乐器行乞,同时也是流浪艺人,凭一张毡毯一把乐器,就可以四海为家。这个老头你甚至分不清他是什么民族,他来的地方非常遥远,那种沧桑感只有阿尔泰山上被风化的锈迹斑斑的石头可以相比。没有人看见马一鸣失神的样子。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云是有心灵的。他就抬头看山顶的云。云停在山顶上,就像青灰色山峦的帽子。山忽然摘下帽子,朝他致意,任何问候都要脱帽,再点头,没有戴帽子的马一鸣就给山点一下头,山也不用再戴帽子了,云团飘到森林上空,成为云海的一部分。老头的琴声果然捕捉到风,风穿过白桦树,穿过山杨树,风到了云杉和红松中间了,森林开始喧响轰鸣。马一鸣必须赶到风的前边,风快要到草地上了。阿尔泰草原是中亚细亚最美的草原。
马一鸣买来伊犁特曲,马一鸣给老头鞠躬,双手献上美酒。酒瓶就蹾在竖琴跟前,太阳被收到瓶子里了,酒瓶上的红标签很容易被看成太阳的照片。老头没有喝酒就已经有了醉态。你听他的琴声,他醉了,他不用眼睛就感觉到酒的存在,这是琴声进入草原的最佳状态。老头刚到阿尔泰,竟然知道《黑走马》。冬不拉曲子《黑走马》从竖琴上发出来另有一番风味,在场的大人小孩随着琴声翩翩起舞。这是哈萨克人庆祝丰收的欢乐之歌。老头在曲子结束的时候告诉马一鸣:你的收获最大。马一鸣的眼睛就大了。老头说:“你的新娘是月亮般的姑娘。”老头指着城外的山顶。
“今晚那里将升起阿尔泰最好的月亮。”
老头从行囊里摸出两个木碗,倒上酒,跟马一鸣一起干。
“能喝到喜酒可是最大的福分啊。”
人群中的姑娘们都用一种神奇的目光看马一鸣。马一鸣把老头的举动当成仪式性的表演了,就假戏真做,配合默契,但心里还是暗暗称奇,莫非领了结婚证的人有什么异常?能让那些江湖高人识别出来?他忍不住看一眼酒瓶上的红标签,现在这个红标签不再是太阳的形象,怎么看都像那个大红大红的结婚证。有个姑娘很调皮地问他:“嗨,喜酒都喝了,你的新娘在哪里呀?”老头大手一挥:“月亮升上山顶的时候,他就有新娘了。”他心里乐呀:“我已经有新娘了,下礼拜就入洞房,我要把阿尔泰的这一幕原原本本讲给李海莉。”他想象李海莉听到月亮新娘会有多高兴。
老头是瞎子,可老头对周围的地形了若指掌,老头告诉马一鸣:“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月亮升上来的时候你要赶到山顶,你比我眼睛好使,你应该看得见那山顶是凹下去的,知道那山形叫什么吗?那叫月亮的托盘,也是月亮停下来的地方。美丽的女人都很傲慢,心气都高得要命,只有幸运的男人才能让月亮停下来,在古歌里把月亮停下来的地方叫月亮的托盘,盘子嘛,把山当盘子才是大男人,才是儿子娃娃巴图鲁,美丽的女人应该把她的一生托付给这样的男人。”老头从怀里摸出一块馒头大的石头,简直就是一个浓缩的凹形山顶,托在手里一会儿闪射出金色的光芒,一会儿闪射出玫瑰色的光芒,一会儿闪射出白色和浅黄色的光芒。老头告诉他金光灿烂的是云母,玫瑰色的是石榴石结晶,白色和浅黄色的是石英石。
“美丽的女人应该有这么丰富的色彩也应该有这么灿烂的光芒。”
这是老头从遥远的乌拉尔山带过来的,那地方蒙古人叫石带,石头多矿石更多。老头采集矿石的地方还真的叫“月亮的托盘”,用当地草原民族巴什基尔语叫“塔加那伊”,千百年来来来往往的各个民族都在那里留下动人的爱情故事。老头贴着马一鸣的耳朵小声说:“月亮的托盘,多好的说法呀,巴什基尔语最初的意思是最初的明月安眠的地方,那可是男人和女人的好时辰啊。”老头把乌拉尔山的矿石塞到马一鸣手里,“小伙子,谢谢你的美酒,这是我喝到的第一百次喜酒,比我自己当新郎还高兴哪,阿尔泰是人间天堂,我可以在这里结束我的一生。”老头收起行囊,一晃一晃地走了。
天很快就黑了。马一鸣没吃晚饭,马一鸣抽烟。一包烟都抽完了,白白净净的烟卷噙在嘴角,很快就化成青烟从肺腑间升腾而上,那简直就是灵魂出窍,灵魂上天。二十支香烟,让他的灵魂一次次上升,上升,一直在升。
等月亮升上山顶的时候,马一鸣已经坐在山顶的大石头上了。大石头基本上是个石槽,那块来自乌拉尔“塔加那伊”高峰的矿石就揣在怀里。老头说的没错,月亮从森林那边从额齐斯河的支流之一少女额尔齐斯河那边过来了,跟羞涩的新娘一样缓缓上到山顶就停下来了,把马一鸣全都覆盖了。马一鸣分不清是梦幻还是现实,他竟然触摸到活生生的肉体,还有肉体的芳香,还有体温,喘息声,歌声,美妙的乐曲混杂着森林的涛声、河水的喧哗、骏马的嘶鸣,最后就剩下天和地了。他意识中唯一清晰的就是他竟然有那么大力量,双手把女人端起来,一次一次地欢乐,一会儿冰凉一会儿热烈,他知道热的是女人,凉的是月亮。此时此刻月亮圆到了极限,女人也圆到了极限,月亮亮,女人也亮,月亮香,女人也香。这种似梦似幻的状态维持到后半夜。
马一鸣后来意识到自己到了马背上。他在前女人在后,女人的奶子暖着后背。马一鸣还记得他是徒步上山的,走得很累,出了好几身汗,下山就轻松多了,在马背上嘛。马一鸣还记得他最疯狂时的举动。当时过于疯狂,记不清了。这种男女欢乐的最佳状态叫端盘子。途中还有一些零散的残留记忆,印象最深的是大泄后的放松,山崩地裂似的四面散开。他估计不错的话,是这匹了不起的马从四面八方把他失散的魂魄和形体找回来了。那女人也真有力气,到宾馆跟前亲一下他的耳根,女人的体温体香最后一次弥漫天地,然后轻轻一托,他就到了地上,那马嗖地一下,跟一股风一样消失了。
可以想象李海莉见到马一鸣的情景。李海莉跟豹子一样冲上来。马一鸣闭上眼睛等待沙尘暴。马一鸣都做好坦白交代的准备了。落在马一鸣身上的是李海莉的拥抱,还有疯言疯语:“我以为你回不来了。我梦见好多女人在追你,她们个个都比我有魅力。”马一鸣脸都白了,忧郁中的苍白,还在发抖。李海莉说:“你太累了,太辛苦了。”李海莉给马一鸣脱鞋,双脚泡在热水里,还给马一鸣搓脚。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李海莉还要看着马一鸣吃饭,李海莉还要告诉马一鸣:“我怎么搞的,以前就没发现你小子很有男人风度,你可不许背叛我,梦中那么多女人争你。”马一鸣的小脸已经不发白了,腿肚子也不发抖了,马一鸣点一支烟,告诉李海莉:“梦是反的,是我担心失去你。”李海莉相信了。一直是这样嘛。
没过多久,也就是他们婚礼后的一个月,李海莉又不自信了,忍不住问马一鸣:“你这狗东西,我怎么越来越害怕失去你。”马一鸣就说:你想多了。李海莉有点歇斯底里,越担心马一鸣,就把马一鸣看得越紧。
马一鸣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抽烟。还有那块五光十色的矿石,就摆在客厅的架子上当艺术品。那确实是一件不错的艺术品,完全是大自然的造化,夜晚它都会闪射出神奇的光芒。只是马一鸣抽烟的样子太可怕了,老婆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坐在“塔加那伊”矿石跟前,一支接一支抽烟。每支香烟都是白白净净进去,清清爽爽出来,还要盘旋几圈,跟灵魂出窍一样飘出窗户飘到楼顶一直飘到天上。
原刊责编 谢 锦
【作者简介】红柯,本名杨宏科,陕西岐山人,1962年生,毕业于陕西宝鸡师范学院中文系。1986年远走新疆,在奎屯生活十年。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大河》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美丽奴羊》、《跃马天山》、《太阳发芽》等8部,学术随笔集2部共约五百万字。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及多种刊物奖。现在陕西师大文学院任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