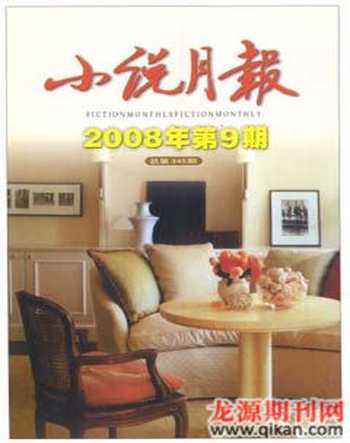云南小说二题
玉龙雪山
客人上马了。
马很矮小,个头只到人的肩膀,是匹稻草色的马,毛色干枯,神色驯服,顺着耳朵站在那里毫无主张,缠着各色彩布(布已经褪色)的鞍子搁在它背上,看着挺沉重,客人一跨上它的背,它就不停地动弹四蹄,竭力稳住自己似的。
“嘿,这小马……行吗?”
“滇马就是天生矮小,它吃得苦,吃得苦!”马的主人说着,使劲把马鞍扶了扶,让那个问话的客人坐正。客人很胖,脸儿细白得简直像个娘们儿,偏又裹着围巾,还穿着鼓鼓的羽绒服,看着倒像马背上驮了个充了气的彩色塑料球一样。“那可是个大肉球哟。”马的主人暗想,并斜起眼睛,看看前一匹马上和他一道来的轻巧苗条女客,不由得在心里为自己的马儿叹了口气。
“你的两瓶水,我来替你拿着。”马主人朝球形客人说。水递给他了。
马主人把两瓶水一左一右揣进外套口袋里。那外套是一件灰色的化纤西装,疲疲沓沓,肮肮脏脏,两瓶水塞进口袋后,两片前襟就长长地耷拉下来,那件西装看上去呈褡裢模样,跟下面很单薄的裤子和鞋帮松弛的胶底鞋倒很般配。他是个黑瘦的汉子,四十岁上下,身子单薄,连五官也都长得单薄,他就照那样站在马身边,外表神气都和他的马很接近。
客人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一匹接着一匹矮小的滇马牵过来了。这些马的相貌在马和驴之间,但它们绝不是骡子,骡子也要比它们高大得多。它们仿佛也为此感到羞愧似的,都埋着脑袋一声不吭。或许它们认定自己的终身职业毫无出息:把各式各样痴肥沉重或左摇右晃的人在满是石头的山路上驮上驮下,没完没了,莫名其妙……因此打定了主意得过且过,苟且偷生,一个比一个委顿;或许它们并没有任何思想,它们仅仅只是因为疲倦而垂下脑袋罢了。
“你看看它们,你倒是看看呀,哎……YOU BETTER THINK OF COPS MAGENIFICENT HORSES lN NEW YORK CITY。HOW CAN YOU CALL THEM HORSES TOO?(想想纽约警察神气的高头大马,难道它们这样也叫马!)……哈哈哈……”球形客人对前头那个苗条女客说,跟着就笑得喘不上来气了,身体在马身上前后摇晃。他座下的马吃惊地抬起头来,往后倒了倒蹄子,惊慌地看了一眼主人。
“客人你扶好,不要晃。”马的主人说,脸沉下来。他是有理由不高兴的,首先,自己的客人太胖,至少比那个苗条女客重上一倍;其次,虽然他没留心客人说了什么,但他这样对着马儿大笑,就不是个善意。客人知道个屁,即便是劣马(何况它不是),在主人眼里也是宝贝。这个吃得这么白胖胖肥嘟嘟的家伙才不会知道,他的马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连一天的休息都没有,除了拉客人上山,还有家里的活儿要干,吃的不过就是干草。他在家里可以打孩子甚至打老婆,但他从不打自己的马。
“老天该有眼的,怎么一来也叫他养上一匹马什么的,也来伴着它走一趟雪山,那时候他娘的就不会这样傻笑了……瞧他那个胖屁股整个一个肉砣啊!鞍子里都快挤不下,我可怜的马儿哟……”穿褡裢似西装的汉子想,“……它才八岁——正是干活出力的好年头……可碰到这样一个胖球似的客人,也够它一呛。再干个十年,它老了的时候,那才有得瞧呢。粮仓家的老马,那天带客人上山,半路上休息时,已经累得呼哧带喘,竟想自己独自跑下山去,害得粮仓追了它好久,才把它抓回来……这就叫,嗯,那个什么……当牛做马,当牛做马啊!”
所有客人在大惊失怪或者嘻嘻哈哈中被扶上马背,红红绿绿的一串,跟着,马儿们就走动起来,每匹马前面都有各自的主人牵着缰绳。一出村子,是一片开阔地,地面上分布着许多石头,因此无法种植,只稀疏地长着一些老树,树被风吹出各种奇异的形状,伏卧仰侧,十分可观。开阔地的四周一圈儿都是山,近些的呈绿色,远些的呈紫黛色,却并不见些白色,玉龙雪山被印在各种广告和旅游手册上的那个白帽子似的山顶,从这里并望不见,因为这里是雪山的背面,马队将从后山上去。这是雪山脚下村民们自己想出来的生财之道,他们用马驮客人上山,价钱比从前山坐缆车略微便宜。
马上的客人照例开始惊叹周围的风景,咔嚓咔嚓按动手里的相机,马闷着头走,穿着褡裢似西装的马主人也闷着头走,美丽的风景对于他是不存在的。他心里想的是:
“老婆总吵着要把孩子送到镇上的学校里去读中学,好端端,一个学期要交两千块,这不是胡闹吗?女人真是糊涂,她以为能赶着马送客人上雪山,就不算庄户人了。瞧,身上这件西装就是刚开始干上牵马送客人时她给买的,亏她想得出,她还以为有了‘客户就等于做上‘经理了,她差点儿没替我把领带一起买下来呢,好轻狂的娘们儿哟,给我打嘴显眼地丢人就是。现在她倒明白过来了,听凭我把西装穿成抹布了也不来管了,叫她再给买件新的试试,呸!打死她也不肯……如今把自家汉子不瞅不睬的,眼珠子只盯住孩子一个人,还兴出新章程了:一年四千块!吐血啊,那是庄户人家花钱的手脚吗?那叫败家!在村子里的学校上学,就一个钱也不花……不过有书本费,那倒还是该交的,谁能白给啊。可他娘的,如今又兴出活动费、杂费、这个费那个费,马蝇子似的烦人……他娘的连学校也学会摊派了,那些狗日的!哪里都学会摊派了,可是让我们这样养马的摊派谁去?摊派客人吗?得,跟他们每人摊派十块钱小费试试,他们立刻就把脸拉得比马脸还长,把个嘴撅得比猪嘴还翘,倒好像是在要他们老娘的命。他们以为我们挣得挺多,二百八十块一个人,是啊,听来可真不老少,可是他们又不会去费心打听,村政府在其中拿大份,哼,村政府!拉客人的眼线也得拿上一份……不过她们拿倒是应该的,客人又不是雪花,可以自动从空中落下来,全亏村里那些肯厚起脸皮的娘们儿,在酒店门口,停车场,还有直接站到街道边上找客人的呢。嘿,全凭死拖活拽……这种事我这笨嘴夯舌薄皮浅腮的爷们儿哪里干得,当然就只配牵马了,死笨死笨的力气活,下力最多,到手的只是那个数中的零头,其中还得扣掉养马的钱呢。”
在他身前身后的马,是两个年轻人牵着,一个小子,一个姑娘,都是褡裢西装同村的人。前头的姑娘手中还拿着个脸盆,是她在雪山腰上开饭庄的姑姑叫带上去的。后面的小伙子犯骚,不断朝脸盆上丢小石子,终于当啷一声击中了,姑娘就跳起身来去抓打他,小伙子笑着逃开,姑娘就追,马也不管了,缰绳就扔给客人自己抓着。马上的客人倒很高兴,尤其是骑在前头的苗条女客,做张做致,朝球形客人得意扬扬地叫道:“嗨,嗨……瞧我,瞧啊。”
球形客人就把相机对准了她,说:“DONT MOVE,STAY STILL,CHEESE!”(别动,待好了,笑一个!)
听到这一声,褡裢西装灰蒙蒙的心头突然像亮了盏灯,他猛地想起刚才胖客人对着马大笑,叫他生气的同时,他心房里的某个地方豁亮了一瞬间,像在黑地里闪过一道光。但他光顾生气,不曾细想,现在想起来了:好极了,他的客人在说洋文呢,通常,说洋文的客人都肯给小费!
那个做作的苗条女客也好,那个胖成了球的男客也好,在他眼里瞬时变得可亲可爱了。他带着尊敬的眼神开始仔细打量起他们来。“瞧啊,鞋子上印的是洋文,背包上印的也是,当然,还有羽绒服上……不过……”他迟疑地抬头看看前面,再看看后面,旋即失望地发现,马背上的客人有太多的衣服、鞋子、帽子、背包上到处都印着洋文。“如今真是洋文满世界哟,哼,连村里老马家喜欢瞎逛荡的二小子,土疙瘩一个,中国字顶多识得一箩筐,不也成天穿带洋文的衣裳,也会放两句洋屁呢,什么‘古的把儿,‘古的牦牛……操他个咬舌子儿的小兔崽子!在我们长辈面前还想壁虎爬窗子——露两小手呢……我是看着这臭小子呱呱落地的,一撅尾巴就知道他拉什么颜色的屎,还‘古的牦牛‘洋的牦牛呢!见了真洋人,他只剩下打哆嗦的份儿,鼻涕都擦不干净。我儿子要像他这样轻狂,看我不打出他的屎来……好在儿子还老实,倒也肯念书,就这,老婆心里就搁不住了,跟怀里揣着块烫山芋似的,不往他身上烧钱就对不住他……哼,女人!四千块啊,叫我抢银行去?除非每个客人次次都肯给小费……比如说一年送两百个客人上山,一人十块,那就烧高香了,另两千块家里还可以凑一凑。……罢了,还是不肯给小费的客人多哟。可就国外来的人通常都给,有的给得还真阔气,玉秀有一次拿到四十块!把人羡慕得眼珠子都要掉下地。兴许今天我的运气也来了……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是冒牌货,洋文说起来嘟噜嘟噜,葡萄似的整整一串子,能假吗?那胖子的相机,挂在胸前活像一门小山炮!中国哪里买得到这样高级的相机,如今出门旅游都是‘傻瓜相机,除非拍电影的……这样的玩意儿必定只能是外国货……哈,连相机带子上写的全是洋文呢,这就全对了。”
他嗽一嗽喉咙,伸手摸一摸自己西装的领子,看看它有没有无缘无故翘起来,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眼下没有发生。他一眼一眼地看客人,非常想跟客人搭话,可惜客人总把脸整个藏在相机后头,即使放下相机,也只顾东张西望看远处,一点儿也不来注意他。他又嗽一嗽喉咙,摸出口袋里替客人装着的水,递过去问:“喝水?”“不要,不要……哎,你让马站稳,让我照这个……”他只能偃旗息鼓,和马一起乖乖儿站住。他也知道,客人顶不喜欢他们主动开腔,尤其是去打听底细,这会得罪他们。”可是,他们,所有这些不知打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倒可随便打听我们赶马人的各种底细,只要他们高兴,甚至可以直问到我们的祖宗八代呢。你还不能不搭理。这样顺从他们,甚至讨好他们,该死,他们照样不肯给小费!”
突然他的球形客人朝他说话了:“请你把缰绳给我,把缰绳给我。”
“你……行吗?”
“唉……”球形客人几乎是把缰绳从他手里夺过去。
“他真的胖得像个球了,他要是滚下来,还不跟一块圆石头一样,一直滚到山脚底下,我得小心才是……有的客人是,你不要管他,他就高兴,有的客人是,你要每一步都管好他,他才高兴。他们难侍候,但很多客人分明玩儿得挺高兴,可还是不肯给小费哟。”
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在石头上走着,心也一突儿高上去,一突儿掉下来,仿佛在波浪上一样,而小费是漂在水面上的一块木片,一会儿漂近他,一会儿漂开去……
几匹马儿没有主人牵着,却都能老老实实走路,它们好像跟他一样老成,一样怀着忧郁的心思:走一趟是一趟,早结束早好,这一切有什么可乐的。这时小子和姑娘已经不互相追了,两人回到马身边时,脸盆倒已经由小伙子拿着了。姑娘手里则拿着刚折下的一根长枝条,走一步就在地面上抽一下,一副游山玩儿水的神气。褡裢西装就不乐意了,“她忘了自己身份了,忘了自己身份了。人活着要本分,本分的人,客人才喜欢,他们小孩子不懂。”于是他吆喝他们说,“别撒欢乱跑,管好你们的马,对客人负责!”
”大叔,我们的马不用管,管好你自己的舌头。”小伙子笑道。
”我告诉你爹抽你!”
“玉秀,手上的树条子别扔了,记得带回去给我爹!”
“嘻嘻……”
连马上的客人也一起笑了,包括那个球形客人和苗条女客。跟着就听见苗条女客问玉秀,多大了,家里几口人……
“我的胖客人倒不来问问我家里有几口人,这个人像是不好说话的模样……”褡裢西装又一眼一眼地瞄他,“他知道我家底细才好。我倒真想跟他说说孩子上学的事……我养着老爹老娘,马,一头猪,孩子当然只有一个,倒还肯念书,只是一件事不好,他穿破了太多的鞋,简直要人的命哟,他长的那是叫脚吗?那根本是两只带钢牙的嘴,专门对付鞋的,鞋一套上去,它们就欢天喜地地抱紧了啃啊,啃啊,很快就啃出洞来。呸,换一双,再接着啃就是。这还半年不到呢,已经买了两双鞋了……那不能叫脚,那根本是生来跟我作对的一双小妖精啊。得,老婆也对,孩子留在这村子里上学,到头也就和玉秀,跟这个该抽一顿树条的浑小子一样,拉着马上山送客人。别的不说,光是他那脚,还不得一月穿破一双鞋啊,客人给小费也不够他买的!这么混下去,永远不会有发财的一天。如今这世道,人人都在发财,大把捞钱,捞海了!要是不发点财,像自己这样牵马,真叫白活了。瞧瞧这些骑马的客人,人模人样,胖成个球也还人模人样,连看你一眼也懒得,不就是因为有钱吗……人家别说一月买双鞋了,平白无故就能大老远跑到这儿来,来干什么?烧钱嘛!瞧他们这些人对着这座冰冰冷的大山哎哟哎哟的怪模样……好像这个冰冰冷的大山是他们祖宗的牌位还是怎么的?”
马不知怎么站下来了,他回过神来,原来是玉秀的马先站下来,把头伸出去,够路边石头缝里的带着点雪的茅草吃——现在他们上得够高,已经看得见雪了。他的马则老实地站着等。“瞧我养的好个蠢货,别人家的马也知道捞点子‘小费呢,偏它不会。”
冷不防球形客人向他开腔了:“老乡,你们这里也有冬虫夏草吧?”
“虫草?啊,虫草。当然,这里能挖到,就是少点,越往高原上去,越有。嘿,我告诉你说呀……找虫草,那是有季节的,也就是开春虫草从地里刚长出来的时候,不过就十五天左右,过了季节,那就长成草了,长成了草就完了。是啊……虫草不容易找,你想,一地里都是小草,哪个是呢?一个人得完全平趴在地上,拿眼睛一点一点地看,常常要趴上一整天哟……对了,挖虫草要备上一条牦牛毡子,下雨了,下雪了,盖在身上,挡雨,也防寒……带油布才不管用,即使能挡点雨,可冻也要冻死,就牦牛毡子管用……话虽这么说,那也要置得起牦牛毡子才行,不是随便买得下来的,好贵哟……好,有了毡子,趴上一整天,结果能找到五个七个虫草就算不错……不容易。一季也就能挖到几十个吧……客人,你,要不要?一个十五块。都是今年挖的,货真价实,还在瓶里放着,有人来收,我没给。这里常有客人问我们买,因为货真价实。拿回去跟鸡炖了,大补,体亏的人吃最好。”
“不要。”
“带回去给老人,那是上好礼物。”
“不要。”球形客人就把脸别过一边去,又不跟他说话了。玉秀在他前头,早听去了这些话,见客人一直说不要,就朝褡裢西装扮一个大大的鬼脸。
他知道玉秀他们年轻人总瞧不起他啰唆,瞧不起他那么在乎钱,“他们这起小兔崽子赶上好时候了,有了吃的,还能挑肥的瘦的。让他们也像我年轻时饭都吃不饱试试!老天爷该把所有的事情都让人摊上一份儿才公平,不然肥的肥死了,瘦的瘦死了,这像话吗?”他有些生气了,就把手背在身后,缰绳拿在手里,没有再说话。他就照那样一直走到目的地也没有再说话。
终点并不是山顶,其实只到山腰,再往上马上不去了,这倒是事先跟客人说明白的。好在这里开阔,可以看见玉龙雪山的顶,可以玩雪,可以照相,也算是上过雪山了。山腰上有三四间歪歪斜斜的木板房,也是他们村民们建的,看着根本是潦倒之极的工棚,却就有胆子把它们叫做饭庄(玉秀把脸盆就带到这里给做饭的姑姑)。门口挂着油布做门帘,掀开走进去,当门是一张油污的大案子,上面散放着锅、碗、勺、筷、砧板、刀、盆儿、瓶儿、罐儿等一切厨房用具,大案子旁边设了两个用油桶做的大炉子,眼下生着火,呼呼地正烧得欢。再往里去有三五张黑糊糊的木头桌子,棚子深处则是乱七八糟堆放的纸盒子,筐子,煤……几乎像个垃圾场。棚子虽搭得不算小,但却叫人插脚不下,因为除去那些必需的家什,所有做饭菜的原料都一地摊开,筒装“康师傅”方便面啊,成箱的啤酒啊,灰白的煺了毛的死鸡啊,瘪塌塌的猪肝啊,暗红色的生肉啊,蔫瘪的菜瓜啊,黄了叶子的菜啊,全放在地上的脸盆里……这是云南地方饭庄的规矩,做菜的原料全展览在门前由客人挑选,然后再拿去灶上炒……虽然这里完全没有苍蝇,但骇人地不洁净,整个棚子看上去也只炉子上燃着的两团火是干净的。
褡裢西装照例不在这里买东西吃,他口袋里装着用报纸包着早上从家里带来的米糕,他只向开饭庄的乡亲要了碗热水,就着热水把米糕吃下去。玉秀和那个小伙子却坐在木头桌子边,一人要了碗大肉面,热腾腾地吃。“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本事没有,就是有本事花钱!”褡裢西装看也不要看他们。可是当他看到球形客人和苗条女客进来时,他的眼睛就一刻也不离开他们了。然而他非常失望地发现,他们什么也没有要,只要了几个烤土豆,那是菜单上最便宜的东西。
“坏了,这说明他们是那种很节省的客人,倒霉哟,这样的客人顶顶会抠门。”他告诉自己。但立刻,这个坏情况被推翻了,他听见球形男客对苗条女客说,“这几个土豆怎么吃得饱,还有好几个小时呢。还是点菜吧。”女客就说,“在这地方!亏你想得出!土豆因为是火里烤的,我才敢吃。喏,我包里带着巧克力呢。凑合一下吧。”跟着就瞧见她从包里拿出一个长条形的东西,就是她说的巧克力了。巧克力,褡裢西装是知道的,叫他一下子感到喜滋滋的事情是,他分明看到那巧克力的包装纸上完全是洋文!然后又看到女客拿出一管软膏搽手,上面也满满地印着洋文!这些洋文让他刚喝下去的热水简直不是热水了,根本就是白酒哟,他觉得身上暖融融的。
一切都不容置疑,一次次地被证实这两个客人肯定从国外来的!这个念头在下山的路程中再也没有离开他。他心情开朗,走起来也比上山轻松多了。等走下山时,太阳还没有落下山去呢。
他从这几年的经验里已经磨炼出见识来,越是在乎的东西,越是不要在客人面前流露出来,那会产生反效果,一切要做得光滑自然,主要的是,认准了对象,把服务做好,那才是敲鼓敲到点子上。他想到这一路他倒没做下让客人不高兴的事,却也没有做下让客人高兴的事,他应该再兴出点事情来,兴出点真正叫客人高兴的事,那就妥妥当当了。而且国外的客人给小费兴许不止十块呢。
走在山脚的开阔地时,他主动对两个客人说,“前面离我们村子不远,有个土司的书院,院子里还有不少东巴文字,想去看看,可以送你们过去,不算钱,嗯……要是、要是……那个……”他结结巴巴差点儿忍不住要把小费两个字吐出口来,可好球形客人嚷叫起来打断了他:“好极了,好极了,那谢谢你们送我们去看看吧。”
牵着另一匹马的玉秀一声不响,脸别过去看别处。“瞧她这个脾气儿,等她也拿到小费时,她就该谢谢我了。”他想。
他们两匹马四个人就从队伍里分出去,往偏东方向走去,远远地看见有一簇林子,越走越近时,开始看得到掩在树丛中的房舍、池塘,池塘边上长着大树——好个幽静去处。
“多的先不想,光是十块钱,那就可以把马料抵了。今天这一趟应该没问题了。我都敢给自己打个赌,瞧,我的马儿走到,假如太阳还照得到池塘边最高的杨树梢儿,我就拿得到十块钱小费。”他暗想。
当马儿抵达时,大杨树的树尖上还残留着巴掌大的一块阳光。褡裢西装满心高兴,殷勤对客人说,“你们只管进去玩儿,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不下一刻钟的工夫,太阳完全沉下去了,山脚下开始往这边刮过来阴冷的风,褡裢西装和玉秀坐在离着院子两丈远的石头上等,全觉得冷上来。褡裢西装干脆蹲下来,使劲把自己团起来,活像一只大鸟。马儿立在一边,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一样。
“别的马都走回去了,偏你要送他们上这儿。”玉秀怨道。
他只朝玉秀看一眼,把西装领子竖起来,又把前襟使劲裹了裹,两只胳膊紧抱着膝盖。脸上的神气说的是:你知道什么。
“他们要是不给小费,可真白等了。”玉秀抽抽鼻子,继续抱怨,同时也用胳膊把自己抱紧了。她渴、饿、冷、累,一心只想早早和自家的马赶紧回到家里去,围着炉子喝热粥。
他心里也希望两个客人尽快就出来。真的冷起来了,不要冻着才好,后悔早上没有听老婆的话,穿那件条绒夹衣,冻感冒了,会挨老婆骂,他是没有工夫生病的人。可是,若能拿到小费,哪怕就是冻病了,老婆那里也就交代得过了。
他突然对玉秀说,“等他们出来,你干脆向他们开口要要看……咋样?”
“我,一个姑娘家。亏得!是你要拉他们过来玩儿这疙瘩,是你的算盘,你自己说去。我不管,我不过跟着你。”
“你是孩子嘛,我怎破得下这张老脸。”
“我不是孩子。”
客人总算等出来了,球形胖子边走边打手机,听得见他在说:“……就来就来,已经下山了,半个小时到得了。说吧,哪家饭店?OK,‘云南人家……成,成……我饿坏了,I CAN EAT A HORSE(我能吃下去一匹整马)。”
他们匆匆上马,人、马全都归心似箭,一气走回村口,马的主人只来得及把客人扶下马,早有几个出租车司机围上来,撕掳着抢客人,褡裢西装急得挡在中间,“哎,哎,你们这些人……哎,哎!你们……”连玉秀在一边也帮着推搡那些打架似的司机。
可是他们被粗鲁地推到边上,两个客人已经被靠得最近的一辆出租车司机拉走,眼睁睁地见他们一下子钻进车去,车屁股后面就马上喷出一道黄烟,车开动了。车发动的声音和喷出的烟罩住了褡裢西装张嘴喊出的声音和口形。等烟散去,只见褡链西装木桩似的站着,脸色灰黄,肩膀塌下来,他的马站在他身边,也那么塌眉瘫眼的,好像它这一整天不是出力干活,而是做了件错事一般。主人和马看上去真像。
玉秀使劲一扭身子,在自家马屁股上狠拍了一掌。“走!”
车刚刚开出去几十米时,车后座上那个苗条女客突然对球形客人叫起来:“哟,该死,忘记给赶马人小费了,我都准备了的,刚才活像打架……就忘了。要不要停一下……哎……瞧啊,你那个赶马的还在那里站着呢……”
“给多少钱嘛?”
“一人四十块吧,小意思。”
“啧啧,真是小意思!就这么一点小钱,谁会在乎,忘了就忘了。师傅,拜托开快一点,云南人家……你知道老K在电话里对我说什么?他说今天晚上要在云南人家让我们大开眼界。我就不信了,云南会有什么山珍海味来招待我这张吃遍天下的嘴?嘿。”
青稞人家
“青稞人家”是一家小客栈。在香格里拉老城街口处,从石板路走进去不足五十米,左手边一条极短小胡同的尽头就是。那是个农家院子,门脸儿修得倒还体面,很新的原木雕出个帽子似的门楼子,涂了清漆,显出木头黄灿灿的本色,煞是好看。门楼檐下斜插出一个青布红狗牙边的令旗儿,上面用黑字写着“青稞人家”,谦虚本分地垂挂着,一些儿不招摇。只是走进去时要小心脚下,地面压根儿还没有修缮,车开上去,狂颠;人走上去,像接到命令一般,齐刷刷低头,踩着一块块七高八低的石头走,仿佛走在河里。
门里头是一个长方形院落,朝南一栋两层小楼,上面门窗也都是雕了花的本色新木头,一样黄灿灿地好看。东头打横有一个小平房,不曾作任何装饰,显然是厨房之类的下房。院子里什么都没有种,或者曾种过东西的,但眼下是冬天,土地裸露着,栽着三两根杆儿,上面拉根铁丝,晾晒衣服。还有根水管子当心里竖着,有一条狗拴在上面。狗挺大,黄色,但眼睛和口鼻是黑的,见到生人就吠几声,但不凶。
一个姑娘闻声出来。
是一个小姑娘,圆圆的胖脸,细细的眼睛,小小的鼻子,红红的腮帮,矮矮的身段。这样的姑娘在县城小镇到处看得到。她身上穿着也是眼下到处看得到的化纤厚运动衫,蓝灰色,右胸口照例印有字,而且还不是汉语,是黄色的字母“H•E Jian”(天知道“H•E Jian”意味着什么),运动衫领口拉链开处,露出一件带银色条纹的白毛衣,然后,灰色长裤子,白色旅游鞋,无一不是化纤织品。看上去小姑娘不会超过二十岁。
“楼上是客房,十五块一张床,楼下是标间,二十块一间。楼下的标间,一种带厕所,是两张单人床,一种不带厕所,是一张双人床。住哪间随你们。”她笑道。
这时发现,姑娘圆胖的脸和结实矮小的身体生在一起很协调,她笑起来,笑容和她的心情语气也很协调。
价格这么便宜,我们当然都要了标间,而且都要带厕所的。四个人一人占了一间屋。我把行李拎进标间,见有两张单人床贴墙相对放着,两床之间有一个木头小台子,我把水瓶、电筒、药瓶、手机几件东西放上去就满了。对过也有一张小台子,但上面放着电视,我只好把行李放在电视机四周的地上了,走动时,在上面跨来跨去的。离电视机三五步,有个小门,打开看看,里面一个白色的水池,一个蹲坑,虽然倒也是白瓷的,但还是蹲坑!打开水池上的水龙头洗手,水不知通过什么途径,都流到地下了,慌得忙不迭把脚闪开。
马上就走出去告诉姑娘:“小妹,水池漏水啦。”
“噢”,她笑吟吟地,“门后有拖把呢。”一边说一边就往我的房间走,从门后拿出拖把,很利索地把地上的水掩干了。“这边,”她一手拎着拖把朝外走,一手指给我看厨房边上的另一个门,“……也有水池、厕所,还有浴室。你们都可以用。”我跟过去,见很小的空间里隔出两间厕所,两个淋浴,两个水池。都还是白瓷的,但做工一律十分粗糙。
姑娘把湿了的拖把晾在院子的铁丝上,别的什么也没有说。
住另几个房间的人也出来了,看着眼前的事。我朝他们望望,他们接着我的视线,却什么表示都没有。
也是,水池漏,湿了地,用拖把拖干净,是件很简单的事。
我们几个一齐都站在院子里,东看西看,想到这里就已经是香格里拉,心头乱糟糟地涌动着新得到的各种印象。人人好像期待着一些不平凡:比如刚下飞机时看到极高极干净的蓝天,是一种;在来老城的路上看到一个巨大广告牌,上面印着“走进天界神川,感受香格里拉”,有一群黑色牦牛从广告牌下面横穿马路缓缓地走过,是一种;餐饮店的门口挂着一排排已经风干的生肉,那又是一种……可我们拿不准这个小客栈能不能代表香格里拉。我们选择客栈而避免酒店,正是想来“感受香格里拉”。可这个小客栈除了有新雕刻的原木门窗,我们看不到其他任何原始稚拙的东西,有的是眼下世人急功近利的拙劣模仿。
那个姑娘——我们都开始叫她小妹了——在厨房门口看到我们茫然地站着,就走过来笑道:“我这里有刚煮的山药汤,要不要喝一碗?”
我们互相看看,正是六神无主,不如就去喝汤。
一个一个跟到厨房里去。见厨房的木门上贴了一张已经褪色的白纸,上面写着:“热水免费供应。早饭每位五元,中饭、晚饭每位二十元。(供应本地特色菜)”大家看了互相一笑,虽没有说话,但人人明白,如今,五元、二十元能吃到什么东西。愿意来喝山药汤,不过就为暖和罢了。
厨房够小,也就只容得下我们这三五人。正中间有个大铁炉子,一节白铁皮烟囱斜着戳进天花板。厨房一边是用白色树胶板做的厨案,其中安着不锈钢水池,两个火头的煤气灶和放锅碗的橱柜。厨案上搁了许多东西,锅啊,碗啊,盘啊,笊篱啊,蒸屉啊,漏勺啊……不过倒还垒得整齐。厨房另一边是一张旧藤椅,一张老沙发,藤椅上团着一只烟灰色带白条纹的小猫,沙发上散乱放着的衣服围巾,显得有些凌乱。还有三两张小木凳子搁在炉子旁边。我们几个把沙发上的衣服都堆到藤椅上去,同时轰小猫走开。小猫弓身跳起,一纵下地,围着炉子转一圈,尾巴竖着,眼珠子凝成两条细线,真正是横鼻子竖眼睛,大概是抗议我们待它不够礼貌。我们就说,“嘿,这小猫!”小猫对我们不瞅不睬,气狠狠地又跳回藤椅上,盘踞在衣服堆的上面,索性闭了眼不看我们。厨房里同时还有只黑色卷毛小狗,却对我们很友好地摇着尾巴,逐个地闻每个人的裤腿。我们就说:“嘿,这小狗!”小狗就更起劲地摇尾巴。
大家在沙发或小凳上坐了,都把腿伸向炉子,只小妹站着,把山药用小碗盛了,一只只递来。
我说,“我不吃。我在闹肚子。我烤火就行。”
“山药不要紧的。”小妹说。我看看她,顺从地接过碗,就吃了。是简单的白水煮山药,放了盐,但山药煮熟之后,汤很稠,呈灰色。
放下碗,我低头听了听——肚子里并没有咕噜咕噜出声,就放了心。
司机小于说“小妹,今天晚饭我们不在你这儿吃,我们去‘藏族之家家访。明天早饭,你帮忙做一下。”
“吃什么?有馒头,稀饭。”
“就是馒头,稀饭。你再给我打筒酥油茶。”
门外,有汽车的引擎声传来,那是来接我们去家访的汽车来了。拴在院子里的大狗大叫。
早上,我们都拥进小妹的厨房,一只大锅坐在炉子上,里头是蒸馒头,另一只大锅也坐在炉子上,里头是小豆稀饭。大铁炉子是长方形的,放在屋子中央等于就是个小桌子。
小妹先递过来一只碗,里头半碗黑黑的东西。
“什么?”
“酱。”
然后,她从一只竹筒里倒出一碗褐色液体。
“什么?”
“酥油茶。”她递给司机小于。小于喝着,咂嘴,笑容满面。另几个见他得意,也要试试酥油茶。
“你要不要?”小妹问我。
“我不要,我闹肚子。”
“喝酥油茶不会闹肚子的。”
“你怎么知道?”
“喝酥油茶肯定不会闹肚子的!”
“有什么医学道理吗?”
“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喝了酥油茶没有一个闹肚子的!”
我们全都笑起来。
我笑了又笑,却因此接过一小碗酥油茶,伸出嘴,一点点地探,酥油茶有点咸味,有明显的油膻气,颜色味道都像洗碗水。
小妹笑着看我,小于笑着看我,大家都笑眯眯地看我。我就……我就一气都喝下去了!
之后,我们就吃早饭。什么菜也没有,那点酱我们用来抹在馒头上,不够分的,连酱底都刮干净了。
然而,人人都吃了很多,包括我。我们吃了一辈子粮食,却是第一次尝到最纯净的粮食香味,甜味。
大家吃饱了,也不急着上路,伸着腿坐了好一会儿,才走。走前跟小妹说,中饭晚饭都在外头吃。
我们去了松赞林寺,中午就在路边上一家“牦牛饭庄”吃午饭。叫了炒牦牛肉,红烧排骨,炒鸡蛋,炒干子,菜汤,一大碗米饭。吃完了,大家不做声,司机小于开口了:“我们晚饭不在外头吃吧,还不如回客栈里吃。”众人都交口说好。小于马上拿出手机,拨号前又停下,问:“要不要叫上卓玛?”众人也都同声说好。卓玛是昨天晚上领我们去“藏族人家”的导游,一个摩梭姑娘,热情开放,只一晚上,就已经跟我们混熟了,还互相留了电话,并邀请我们将来去泸沽湖一定要住到她爹妈家去。
小于分别打了电话。听见他在电话里跟小妹说:“炒一个牦牛肉,多放辣子,山药汤……”
晚上回去时,比计划中要早,大家心情却都很好,又一起拥进小妹的厨房。
“咦,你们怎么已经回来了?晚饭还没有做,我马上就做。”小妹笑道。
我们也都笑嘻嘻的,不回答她的问话,只说,“不急,不急。”其实我们心里都想马上吃到小妹做的饭菜。人人跟早起一样,都围在厨房的炉子前坐下,看小妹一个人忙。小妹淘了米,倒在一个大锅里,把大锅安放在屋中央的炉子上,开始煮饭。煤气灶上已经搁着个鼓形的砂锅,山药汤先已炖在里面,看得见一缕热气从砂锅盖的洞眼里往外冒,能闻到肉香,小妹在山药汤里放了排骨。
小妹在一边开始切牦牛肉。
“我们中午吃的牦牛肉,味道不好。”小于说。
“其他的几个莱都不怎么样。”另一个说。
“这里的人现在都不肯用真的牦牛肉做菜,就我们本地人,才能买到牦牛肉。”小妹脸颊红红地说。
牛肉切好时,火炉子上的饭已经开锅了。小妹放下手里切肉的刀,又拿出一口空锅,并把一个大笊篱放在上面——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只见她把煮开了的饭锅端起来,往笊篱里一倒,把米汤控干,再把米倒回原先的锅里,添上水蒸。问她为什么这么煮饭,她说,这样煮出来的饭好吃,而且“我们这里都这么煮”。说着,她顺手一倾,把滤下的热米汤全倒进水槽。
“哎哟,哎哟,你怎么把好好的米汤倒了!可惜可惜!米汤可以喝啊。”我叫起来。
小妹笑了,“哎哟,我不知道呢。”
“我们平时都倒掉,没有人喝。”她又笑着说。
“米汤,绝对好东西!……我们那里谁都喝。”我对她说,但心里想的是:雪白的米汤倒没有人喝,洗碗水似的酥油茶倒又成了好东西了!我朝另几个人望望,希望得到他们回应,可他们都不看我,只看着小妹忙活,眼睛跟着她转来转去。小妹一边切肉,切菜,洗葱,一边还一句一句回答我们的各种问题。
从小妹嘴里知道,“青稞人家”的主人是一个广州人,跑来这里开了这个客栈,但平时不来,现在冬季客源稀少,他更加不来了,自己跑到南方去过冬,把客栈交小妹管。小妹是给他打工的(一个月拿多少钱呢)。小妹是临近的迪庆县人,离这里两百来里地,父母种田。家里还有个哥哥,但也在外头跑销售,销售云南眼下流行的金六福酒。小妹一年回家看父母一到两趟。
我们问小妹,冬天就她自己在这里守着这个客栈,不害怕吗?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别的房客。
小妹笑道:“会害怕。你们走了,我就叫个小姐妹过来陪我。老板在这里有一个朋友,有时会过来看看。”
小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静,就像在说,天下雨了,天放晴了,好像害怕在她,也是一件简单的事。
还有,小妹很坦率地回答我们各种问话,却从没有问过我们任何问题,比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等等。
很快,辣椒和牛肉香味在厨房里弥漫开来,成天偎在厨房的那只小猫早从藤椅上跳过来,在我们几个人的大腿上轻巧地而肆意地行走(它不跟我们生气了),最后找到一个最肥硕的大腿面,舒舒服服躺下,眼睛一睁一闭,一睁一闭地看着炉子,任那条腿的主人用一只手抚着它的毛皮。小卷毛狗急得在我们腿中间钻来钻去,它大概嫉妒小猫的待遇。可是有谁肯把它也放在大腿上面呢,毕竟它是条狗,不是只小猫。但卷毛狗不这么想,就跑到小妹脚跟前,绕来绕去,嘴里呜呜有声,像在抱怨人们待它不公。大狗在外面也哼哼地叫,大概闻到肉香,以为忘了它,也开始抗议。小妹同时有三个灶眼要照应,卷毛狗只管在脚下碍事,她就把它轰出去,把门关了。两只狗在外面不高兴地叫着,但过了一会儿就安静了,想是互相有了安慰。
所有这些事,全让我们觉得好笑,因此人人脸上都是和乐的表情。小妹虽然手脚不停地忙活,脸上也是和乐的表情。我们这么多眼睛看着她,这么些嘴在等着她,她竟也没有慌忙,三个火头同时在烧煮,被她调停得互相不碍事。除了把卷毛小狗轰出去,她没有耽误手上的事,甚至也没有耽误我们的任何一句问话。我们全都心安理得地坐着,人人仿佛觉得,天底下有一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有个青稞人家,青稞人家有个这样的小妹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有了小妹,我们一天的疲劳都有了着落。
菜都做好了,一排搁在炉台上,小于又打了一次电话,卓玛才来。
卓玛已经不是小妹那样的黄花闺女,大概二十七八年纪(或者三十了),也结了婚,丈夫是一个藏族歌手,经常在外头演出或者比赛,因此还没有孩子。卓玛长脸儿,两个颧骨略有些高,但谨慎地向外微微凸起,不曾破坏脸部鹅蛋形总体格局。她的眉眼乌黑清晰,偏黑红的脸儿有一层光润色泽,嘴唇也亮晶晶的。这些都表明,她是化了妆的。她化妆的脸,加上苗条的高个,披肩的长发,斜挎一个宽背带,体积挺大的红色软包,围着红围巾,穿着雪白的长腰身羽绒服,风帽上还镶有一圈长绒的人造毛,腿上是贴身的黑裤子和黑靴子,完全是个道地的时髦女性。有谁会料想得到她是个摩梭姑娘,她的爹妈还住泸沽湖畔摩梭人的寨子里,那里至今通行着走婚风俗。
卓玛进门后,朝每个人笑,跟每个人说话,空气里满满的到处是她的笑脸和声音。之前,小妹一个人同时用着三个炉子,给一屋子人做饭,也在跟一屋子人说话,她却不占有很多空间。
在卓玛的笑声语声中,小妹已经一眨眼把饭都盛了,递给一人一碗。大家一接过热腾腾的饭,也不打话,就都吃起来。只在吃起来时,才注意到小妹并没有给自己也盛饭。
“小妹,你一起来吃!”人人都朝她说。
“我刚才已经吃过了。”见我们不放心的表情,她又笑道:“真的,就在你们回来之前刚吃过。”她的口气淳朴平和,容不得人不信。
我们就放下心,更加起劲地吃起来,吃得又快又香,等一碗饭下去大半时,才开始讲话。无非是说昨天卓玛带我们去的那家藏族人家房子修得如何大如何好,参加“家访”的人如何多(两百多人),场面如何热闹(有歌有舞),那个六十岁的藏族老太太歌喉实在好得惊人,烤全羊如何香,炒青稞如何耐嚼,青稞酒如何醉人,一个人五十元的门票真的不便宜等等等等。跟着还问卓玛,摩梭人走婚究竟算个什么?卓玛就撇着嘴说,世人俗气,以为摩梭人走婚是散漫不负责,其实他们的家庭很稳固,夫妻分住在各自的娘家正可以避免翁姑婆媳等许多家庭矛盾,真是轻省方便。又因为走婚,因此一个家庭连接着两个家庭,任何喜庆活动都变成双份的,才是热闹有趣等等等等。小妹在一边不随便插话,除了为我们添菜添汤,没有事时,脸朝我们,就在一张凳上坐着听。我们说的这些事,对她也许是新鲜的,也许毫不新鲜,可是在她的面容上全看不出来,胖胖的圆脸笑模笑样的,那是她天生自然的表情。
这顿晚饭吃得很长,吃完了,人人都坐着不想动弹。如今这年月,酒醉饭饱是常事,我们也常常吃宴席的。(那些饭菜跟小妹的辣子炒牦牛肉、山药排骨汤、炒芹菜、炒青菜相比,简直是罪过哟!)吃完之后,我们会带着一种类似山穷水尽的空洞心情离开,真的,那是吃完山珍海味常会生出的心情。可是在这个青稞人家,这样简陋的小厨房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让人如此满足。人被简单地吃饱了,身子被炉火烤得暖融融的,身心彻底地休息着……天哪,哦,天哪!寒冷而宁静的香格里拉,小妹,香格里拉的小妹……
到了八点半,卓玛要走,她又要去主持“藏族之家”的家访晚会了。我叫她等我一会儿,然后到房间去拿来个挎包,掏出一管COVER GlRL的口红,一个粉饼送给卓玛。卓玛非常非常高兴,毫不推辞,马上说:“我最喜欢这些东西!”小妹伸头看看,在一边也跟着高兴:“对呢,她可喜欢了。”她笑容满面地说。
我从包里又拿出一支润肤膏,向小妹递过去,“这个给你的。”小妹一愣,跟着脸红了,笑道:“你自己留着用吧,我用不着。”
“姑娘家,这个总是用得着的。带在身上,冬天,涂涂脸,涂涂手。瞧,我没给你化妆品。但这个你用得着。”
“你就拿着吧。”卓玛也说。小妹红着脸谢了。把润肤膏接过去,顺手搁在碗橱顶上。
一管很精巧的奶白色软膏,上面印着英文,在香格里拉一个农家客栈厨房油腻腻的碗橱顶上竖着,周围是一摞粗瓷碗,一个灰白色塑料肥皂盒,一瓶黄色海鸥牌洗洁净,一个碰掉一大块瓷的带把搪瓷杯……那支软膏在中间显得分外精致,因此非常奇怪。
小妹推辞,好像自有道理。
卓玛告辞走了,小妹开始洗碗。小于他们几个也就回房去了。我在炉子边上坐着不走,看着小妹洗碗,没话找话:收拾完了,可该歇着了?
小妹说不忙。还说,她还要烧一顿饭。
我几乎从凳子上跳起来:“有这种事?给谁?”
小妹说,刚才老板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晚上要来四个客人,让她给他们做饭。
对了,刚才聊天时,小妹是接了个电话,可是她接完电话,竟不动声色。
我说,“我走,你忙吧。”
小妹说,“不急,他们九点半才来。”说着顺手就开始洗菜。
我看了小妹的背影半晌,心里奇怪,这个乡下小姑娘,这样事事从容,这个定力哪里来的?可这种话,是没法问的。后来,我开口问小妹的是:有没有订了婆家?我知道小妹这种年纪的姑娘,在农村说订婆家是极普通正常的事。
小妹转身朝我笑道:“还没有。”竟无一点扭捏之态。接着她主动说,“老是有人上家里去提亲,但我没有愿意……他们都不合适。”说的时候,小妹脸蛋红艳艳的。
“是的,他们都不合适。”我大声地说——虽然我压根儿不知道“他们”是谁。“小妹,你是个有福气的人!你的将来必定是有福气的!”
小妹对着我笑,她并没有听了这句话而显出受宠若惊的表情。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吃了小妹做的稀饭馒头才走。我不知道她为昨天夜间的客人做饭忙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起来为我们做早饭的。
在青稞人家的这三天里,我已经完全不闹肚子了。
而且在走的时候,已经不再胡思乱想香格里拉该如何如何。光是知道,香格里拉有个青稞人家,青稞人家有个小妹,心里暖融融的。
原刊责编 张颐雯
【作者简介】王瑞芸,女,江苏无锡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西方美术史硕士,1988年赴美学习美术史,再获硕士学位。主要学术著作有《巴洛克艺术》、《美国艺术史话》、《二十世纪美国美术》、《新表现主义》、《激浪派》,文学作品有散文集《美国浮世绘》,小说集《戈登医生》,译著有《杜尚访谈录》、《光天化日》等。并有小说、散文发表于海内外中文报刊。现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