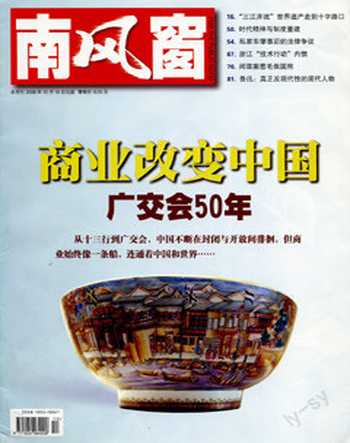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圈
婴 雄
广义而言,“土地”并不局限于物质层面。“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仿佛变成了这个转型时代的背景音乐。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指出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转型:从1840年到2040年,中国实现“文明宪政、轻松生活”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几年前,吴敬琏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强调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号召中国民众齐心协力过大关。2003年,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在接受本刊等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并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与国人共勉。
与上述观点相对应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建设如火如荼、发展越来越快。人们同样发现,这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在改革大关欲过未过之时,更像历史上许多国家一样,正经历一场“过大圈”的洗礼。
“圈时代”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圈时代”。“圈”的背后,则是一些利益集团的合谋与分利。关于这一点,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圈钱”(还记得那场著名的股市是赌场的争论吧?)与“圈地”。后者在狂飙突进的建设中派生出一场新的运动——“圈山河”,它像隐喻般的魔力昭示“圈运动”正在席卷天下、也在“圈分天下”。
不可否认,一轮新的圈地运动正在中国抬头。尽管中央政府提出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成立了“联合督察组”对“开而不发区”的圈地行为进行打击,然而,非法征地的现象至今未得到遏制,在许多地方甚至愈演愈烈。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地工业园区、开发区甚至“大学城”开始恶性膨胀,其后果是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再一次为中国“现代化”埋单。
根据国土资源部对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部分城市卫星照片执法检查情况统计显示,违法用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61%和5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与此相对应的是,各行各业都谋求自身加强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多要地、多圈地,根据国土资源部掌握的各行各业提出来的用地需要,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国土面积。
什么是“圈山河”?以江河为例,2003年6月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清查,查出仅“四无”( 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水电站就有3000多座。《中国经营报》曾发表《脱贫工程带来的返贫危机》提出警告,要求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库区人民的权利,否则一旦悲剧酿就,局面势必无法挽回。
就在不久前,一些地方发生了小水电站、小水库垮坝事件,冲毁下游群众房舍,淹没农田,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水利部有关负责人对此表示,事故的发生说明小水电开发过程中抢占资源、无序开发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美丽新圈地”?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圈地运动”的历史。关于这一点,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英国的“圈地运动”。由于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贵族们纷纷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甚至把他们的房屋拆除,把可以养羊的土地圈占起来。被赶出家园的农民,一方面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另一方面又被政府禁止流浪,多次违犯禁令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其苦难命运的推手,是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描写的“羊吃人运动”——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关于这段历史,曾有一群农民就一个名为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巧取豪夺向国王“上访”:“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
如果说英国绵延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源于养羊业的高额利润,那么今日席卷中国的圈地运动的动力则不仅来自经济暴利的诱惑,更来自“政治暴利”(政绩)的诱惑。正因为此,在今日中国无数“约翰•波米尔”的身影背后,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利。
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实际上也是英国走向现代化的积累时期。这种圈地当然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就像今天的中国,许多地方“盛世繁华”、“花好月圆”。事实上,盛行于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并不缺少才子佳人的赞不绝口。在16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塔瑟看来,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像英国这么“美好的圈地”,因为它可以生产更多的羊肉和牛肉、最好的谷物、奶油和干酪。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一“历史盛宴”的形成,更是基于少数人对于同代及后代人的变相掠夺。
两种不公平
无疑,近年来中国城市的“赶英超美”的蓬勃发展,首先得益于资本的活跃与地方政府“靠地吃地”的利益冲动。但是,这种“美丽新圈地”同样为中国的当下与未来的发展埋下了不公与不幸的种子。具体而言,它主要体现为两种不公平:一是同代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二是“代际不公平”。
关于前者,尽管全球化论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但是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透过中国乡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比较,不难得出结论——“中国有不平”。
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扩大招商,滥征、强征农民集体土地,或者通过压低补偿标准,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等完成权力寻租。与一些地方政府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部分失地农民陷入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悲惨境地,无力维权者甚至走向自焚申冤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权力与资本借“地利”大发横财。
有调查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所获得的净收益则多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城”,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三成、企业占四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5%~10%。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必然成为严峻挑战。“地球仍是圆的”,阳光照耀城市,繁华城市的背面,是失地农民寒凉的身影。
关于后者,美国国际法学者爱迪•B•维丝早在1984年就提出“代际公平”理论。作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则,代际公平已经广为接受,其核心价值观是资源与财富的使用不能向任何一代人绝对倾斜——当代人应为后代人类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的需求,托管好而不是挥霍尽他们的财富。
显然,当下的土地批租制度,无论是对环境损害,还是财富挪用,都意味着对后代人的严重“透支”。一个公民拿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本无可非议,毕竟一切都是自己偿付,然而对于政府来说,多快好省、透支几代人的土地收益,无疑值得商榷。
如有财政专家指出,短短十余年,通过现有土地出让制度地方政府收敛了万多亿元的巨额可支配财力,但是它是对50~70年的地租采取一次性收取资金的方式进行,其所反映的是某些权力部门“寅吃卯粮”或“与民争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研究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指出,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若干年土地使用期的地租之和,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有很大比率是预支未来的收益。因此建议对土地的出让金恢复其地租的经济学本质,土地的收益按年度在土地的使用年限分期支付。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为什么我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落空?对此疑问,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负责人将矛头指向现行土地收益分配办法——“多占地、多得益”及“耕地保护越好,地方越吃亏”的旧机制使一些地方或部门热衷于“低进高出”、“权大责小”,谋求“地利”最大化。
市场可以细分利益,但是未必能细化权力。“看不见的手”在“看得见的脚”面前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当人们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口诛笔伐时,更应该将矛头指向某些与民争利的“既得权力集团”。
有专家分析,经济过热的助燃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银行贷款,另一个则是土地供应。中国在金融调控方面已经驾轻就熟且效果显著。政府无欲则刚,不可否认,权力部门对于土地的调控失灵,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土地充满欲望。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专家小组成员严金明同样指出,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曾经历三轮“圈地热”,究其原因都是地方政府把土地当成生财之道,很多土地储备中心甚至把农用地预征后直接纳入土地储备,“守土有责”因此变成了“靠地吃地”。
中国现行土地批租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借鉴于香港,它从客观上解决了土地不能流转的问题和城市改造建设的资金匮乏问题。但是,1993年底分税制改革将土地出让金完全划归地方政府后,这些土地收益顺理成章地沦落为地方政府的“金库”与“提款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各地政府“PK政绩”,终于导致了今日“土地财政”中兴的局面。
今年6月份一项统计数字表明,1992年~2003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超过1万亿元,其中2001~2003年9100多亿,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5年我国执行收紧地根政策,出让金收入占比虽有所下降,但总额仍有5505亿元。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使2006年一季度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达到3000亿元,预计全年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超过五成。“第二财政”、“土地财政”继续发酵,左右各级地方政府的头脑。
全国人大常委会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时发现,土地出让金的纯收入,过去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对改善城市环境、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资金没有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其使用又缺乏严格监管,因此成为一些地方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和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主要资金来源,成为市长的“零花钱”。
“当前,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政府。”面对宏观调控的大局与失地农民的困境,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曾直言不讳。一些本该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了土地违法的主体。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土地政策改革,最有效的办法应是让政府逐步退出土地经营,回到管理者的位置上来。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保护耕地、保证土地的合理利用,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针对近期“土地严政”的出台,有经济学家断言,“中国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将淡出历史舞台。”它也意味着目前的“圈地热”将得到初步遏制。然而不可否认,中国土地所有权问题目前仍然“未解决”。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是,当我们群起呼吁“必须保卫土地”时,究竟谁最有资格奋起保卫具体哪片土地。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只有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才谈得上要誓死保卫什么。
转“型”,拿土地开刀
几年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曾向笔者感慨,乡村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上许多土地被父母官任意支配,“我们把不可再生的最宝贵的资源,委托给了一些最不可靠的人”。笔者曾在某县做过一次关于土地纠纷的采访,当地农民在路边搭了个帐篷,轮流看守。帐篷外高高悬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帐篷里面则祭着一口空棺材。这次目击让我此后看到中国若干“圈地新闻”时常常胆颤心惊。
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演讲中曾这样表达对个人财产权的敬畏:“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暴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烂了门槛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个经典的宪政寓言宣示了宪政第一步是“关门大吉”,即每个人都可以守住自己的所得。
人类文明史,到底是一部关于土地的历史。从“废井田,开阡陌”到今天的物权法立法讨论,从拿破仑横刀立马翻越阿尔卑斯山到今天欧盟开放国界,无不说明,人类关于土地的态度将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美国史诗《乱世佳人》一样,影片《大地雄心》(Far and away)同样演绎了欧洲人寻找土地的壮阔精神史:
约瑟•多内里是生活在19世纪爱尔兰的一个农民,他的“爱尔兰梦”就是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父亲临终前留给他的遗产是一段充满温情与希望的话,“一个人只有拥有土地才有价值,才有灵魂。当你拥有自己的土地时,父亲便在上帝所在的天堂里微笑,在天堂里看着一路上倒下又站起来了的我的孩子。”
无疑,中国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转型,“转型”因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然而,对于转什么“型”,许多人并不清晰。在笔者看来,所谓“型”,一“刑”一“土”,“刑”即“开刀”,“转型”就是要“拿土地开刀”。在此意义上,“转型”归根到底就是要完成一场“关乎土地的革命”。
广义而论,“土地”并不局限于物质层面,它还关乎精神层面。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所见证的音乐是“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而现在“披着羊皮的狼”竟然成为走街串巷的情歌——“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仿佛变成了这个转型时代的背景音乐。与此同时,那些鼓吹“狼性生存”的狼文化丛书同样爬上了平常百姓家的书桌。
我们说,转型时期注定是个“悲欣交集”的时代。一方面,旧的事物在发酵,另一方面,新的事物在生长,而我们之所以“自夸”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在于这个时代为这场关乎土地的“双元革命”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