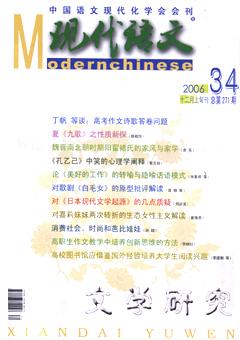新历史主义电影的精神指向
鲁晓丽 王 恒
20世纪占据主流的各种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是一种“语言论转向”,而对文学的历史之维却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文学理论再度关注历史,这便被命名为“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产生的,并成为这一转向的中流砥柱。新历史主义使当代批评家开始告别解构的差异游戏,转向新的历史意识的回归,实现了文艺批评话语新的嬗变。它反对唯文本主义,消解秩序、中心和权威,这对西方,乃至中国影视文本的影响是及时和普遍的。
新历史主义电影没有统一的理论指导,而且在具体导演的创作上运用的技巧也有较大差别,但我们通过对这些电影进行总体考察的话,仍然可以找到这些作品的一些共同特征。
一、以边缘的民间意识取代正统的主流意识
“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1]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民间”具有以下特点:“一、它是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2] “民间”是一个与“庙堂”相对应的概念,它从产生时就表明了一种对抗于“庙堂”的姿态。“民间”所具有的反抗权威的内在张力自然而然的就与以结构为底色的中国新历史主义电影创作紧密联结起来。
张艺谋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竭力表现了小人物生存之艰辛。影片通过福贵一家的苦难史,展示了生活与历史的荒诞,表现了对小人物的终极关怀,呼吁改造人的生存处境,消除社会、生活、历史中虐杀人的不合理因素,要求把人当作人来看待。正是通过回忆唤醒对历史事实(苦难)的记忆,通过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暴露出了现实中那被忽视、被遗忘的苦难的一面,完成了对历史的民间叙述。
吴子牛是一位喜欢拍摄战争历史片的导演,《鸽子树》以中越战争为背景,描写我方巡逻队在正常的巡逻中遭受越军袭击的故事。当时大雾弥漫,三位战友生死不明,葛泰孤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寻找自己的战友,这个被仇恨火焰烧红了眼的战士在找到战友的同时也发现了敌人——越南女兵。这名女兵正在为两位受了重伤的中国士兵包扎伤口,由于她戴着钢盔,令人一时无法分辨男女。葛泰在确认“他”是越南士兵后,向“他”射出了复仇的子弹。吴子牛在《导演阐述》中这样诠释这出悲剧:“他描写了残酷的战争地带中人性的冲突,击撞出悲剧的火花。从中我们看到了‘二重性‘分裂,以及无法逾越的‘距离……这些因素在以往的文学现象中,都被作为一种剧痛来描写,体验并归纳到民族局部的高度。必须指出,如果我们被仇恨、被痛苦、被复仇的烈焰所吞噬……那么,悲剧哲学便失去了全部意义。”[3]吴子牛在《鸽子树》中有明显的改写主流战争观念的动机,越战中的“英雄”是一个一开始就被吓破了胆的小兵,但他却始终没有丧失人性的善良情怀;越战中往往被描写成歹毒的敌人,在这里也成为了良心没有泯灭的救助中国士兵的女兵。影片所讲述的历史事实完全越出了正史的风景,导演和编剧对于史料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立场:对小历史的关注和大历史的怀疑。小历史从大历史的遮蔽下旁逸侧出,并不断地解构着大历史的客观真实性。
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让位于突发事件的偶然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列宁也曾借用俄国一位作家的话说:“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4]新历史主义电影明显强调了偶然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历史的走向充满了变数,在历史大网上挣扎的生命个体更像是飘摇于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渺小而又无助。
1993年由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直面历史,沉潜入政治创伤,通过一个孩子的记忆,展现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普通人在历史和政治的高压下看似必然、实则偶然的命运历程。铁头的爸爸李少龙被判成右派这个情节,突出了历史的偶然性、随意性,是一个具有卡夫卡特征的荒谬、离奇的片断。李少龙的工作单位是图书馆,这一天,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如何揪出右派,否则就不满名额。接着是难以忍受的沉默。李少龙在此时慢悠悠地站起来,推开门,进了厕所。下一个镜头,他上完厕所,手拉开门,抽水马桶的刷刷声还在响。门一开,就显现出会议桌两边两排脑袋,所有的眼睛都直盯着李少龙,此时马桶的冲刷声仍在扰乱神经。一定发生了什么。李少龙进了会议厅,又是他和众人的来回对视,这一切似乎颇有深意。但到底发生了什么?李少龙出去上厕所之时,便是他厄运来临之时,但他还被蒙在鼓里。后来,我们知道,他被判成了右派。如果他没有上那次厕所,如果……提出“为什么是我?”毫无意义,因为历史此时已成荒诞剧。
命运就在这些偶然的变数中使得渺小的个人无法把握。新历史主义影片关心的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间隙下个体生命的无常。
三、将崇高神圣的精神追求还原为琐细芜杂的世俗人生
新历史主义“提出了一种‘文化诗学的观点,并进而提出一种‘历史诗学的观点,以之作为对历史序列的许多方面进行鉴别的手段——这些方面有助于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例如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符码进行破解、修整和削弱。”[5]这正是新历史主义电影反崇高的理论依据。在新历史主义电影中,人为修饰的神圣光环被清除,新历史主义电影导演,总是试图从乡间野史中找出一些线索,勾画出民间世界的形态。“民间”本身就是一个驳杂的概念,既包含了富有生命张力的自然人性,又积淀了数千年的国民劣根性。
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取材于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影片是30多岁的男主人公的回忆录,叙述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十五、六岁时的一段经历。影片虽然是对“文革”那段日子的回忆,但却不再是《蓝风筝》中满怀的忧郁和凄凉,或者《芙蓉镇》中残酷的两派对立,更不像《霸王别姬》中那种血淋淋的暴力……这里似乎没有派系之间的打斗,没有谁是谁非,只是一群从学校和家长的管教中解放出来的军属大院的孩子。70年代初的夏天,对于千千万万中国人来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但对这群纯真少年来说,则是一派阳光灿烂的节日。他们是游离于红卫兵时代主流边缘的逍遥少年族群,生活在北京部队家属大院这个相对风平浪静并相对封闭、无人管束的环境里,本该是上学读书长知识的年龄阶段,却得不到正常的教育机会;本该是享受家庭温暖、人伦亲情的少年成长期,却失去了平常年月里所应获得的人性的培育。于是,他们便在无忧无虑中自我放逐,厌学逃学、嬉戏游乐,恶作剧、打群架,沉迷于结交异性,干尽荒唐事。他们享受着自己酿造的狂欢,同时又在生命的迷茫中,懵懵懂懂,无所终日。他们渴望自我塑造,像父辈一样出落为英雄,但无所作为却将自我个性扭曲,将青春年华虚掷。“文革”岁月中生活的畸形,反倒成为他们习惯的生活常态。英雄向往,只能在梦里以荒诞的形式作一次虚妄的兑现。
这种从民间、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边缘的叙事,正是新历史主义影片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些影片中,没有崇高神圣的精神追求,有的只是琐细芜杂的世俗人生。英雄消失了,崇高解构了,只剩下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在为自己无聊的生命打发着时间。
注释:
[1][2]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A].鸡鸣风雨[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26-34.
[3] 张煊编著.晚钟为谁而鸣——吴子牛[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62~63.
[4] 列宁.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5.
[5] 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转引自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06.
(鲁晓丽,兰州大学文学院;王 恒,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