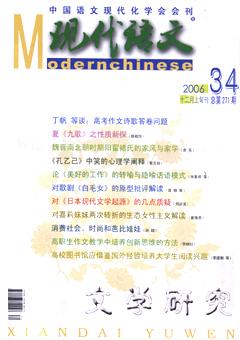论《美好的工作》的转喻与隐喻话语模式
张素珍 王菊丽
英国文学评论家伯纳德·伯冈兹在评论戴维·洛奇创作的独特性时说:“在英国文学史上,诗人和批评家兼于一身者很多,而集小说家与批评家于一身者却寥寥无几,除了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沃尔夫、E·M·福斯特之外,就是洛奇了。”[1] 伯纳德·伯冈兹对洛奇的评价揭示了洛奇在当代英国文坛的独特地位:在文学界,他是著名的小说家,被称为“校园小说”的代表;在学术界,他是著名的教授和批评家,曾在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任教近三十年,并一直担任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被认为是具有理论思辩的天才。洛奇自己也曾说:“因为我本人是个学院派批评家……我是个自觉意识很强的小说家。在我创作时,我对自己文本的要求,与我在批评其他作家的文本时所提的要求完全相同……”[2] 他还曾提到:“身为学院派批评家和对小说有着特殊兴趣的文学老师,会不可避免地对叙述技巧等方面的问题有自觉意识,而且我深信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当然也认为我创作小说的经历使我的批评受益匪浅。”[3] 洛奇反复提到的“自觉意识”指的是他在创作过程中会有意地部分或全部遵守、打破或违反他所了然于胸的与小说相关的创作原则。将自己所熟知的小说创作观念运用于创作实践,他的作品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他的创作理念。换言之,他的理论有助于读者理解他的文学作品,他的文学作品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他的理论。正如西格尔所说,“如果你窘于承认不知道你的文学朋友们正谈的一个流行的称作解构主义的理论……他的新作或许就是钥匙。”[4] 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洛奇对转喻和隐喻两种话语的相关阐述,以其校园小说之一《美好的工作》为分析文本,探讨这两种话语在情节上的表现及其对整体意义和主题强化的观照。
转喻与隐喻的现代语言学意义
虽然对隐喻和转喻的修辞学研究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但从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角度对隐喻和转喻作为话语现象进行研究却迟至现代主义时期。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代表之一Zirmunskij在1928年提出了“隐喻和转喻是区分浪漫和古典风格的主要标记”的论断。罗曼·雅各布森在1927年和1934年“大胆地提出了语言艺术中的转喻式变化”。韦勒克和沃伦在1948年也间接地提到了雅克布森的观点:转喻和隐喻可能是两种诗学结构的特点——转喻是按照相近原则构成联想、在单一话语世界移动的诗学;隐喻是按照相似原则构成联想并与多重世界相连的诗学。雅克布森在1953年发表的《语言的两个方面以及两种失语症状》中虽然较之前更为系统地阐述了转喻与隐喻理论,但对转喻轴和隐喻轴这一核心区别的论述似乎只是对失语症研究结果的思考,而他在1958年印第安纳语言文体会议上的发言《语言学与诗学》的结束语中重新提及这一区分,强调了他早期阐述中“以转喻写作模式为代价从而偏袒隐喻写作模式”的观念。
戴维·洛奇结合雅克布森的理论观念,在《现代写作模式》(1979)和《运用结构主义》(1981)中指出并拓展性地阐释了雅氏的标新立异之处在于提出隐喻和转喻是一组二项对立的概念:隐喻是在纵聚合轴上按照相似性的原则进行选择与组合;转喻是在横组合轴上按照相近性的原则进行选择与组合。按照洛奇的分析,转喻还应该是按照连续的原则不合逻辑地进行删除和压缩,这种删除和压缩的不合逻辑性使转喻话语也具有自身的艺术独特性,从而矫正了雅氏对隐喻话语的偏袒。由于词语之间的意义要么是按相似的关系连接,要么是因时空上的相近而延续在一起,可以说隐喻和转喻反映了两种基本的语言表达方式。转喻模式表现为“在单一的连续的话语世界移动而产生联想”的艺术形式;隐喻模式表现为“联系多重世界而产生联想”的艺术形式。[5]在洛奇看来,“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是隐喻式的,而现实主义文学是转喻式的。”[6]他还在《现代派、反现代派与后现代派》这篇文章中,对近百年来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归类,提出了反映英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钟摆说,即现代派与反现代派(现实主义)文学在现代英国文学中交替主宰的演变规律。他在文中借助于俄罗斯形式主义美学观点,从文学内部探索了创作风格更迭的原因,并从人类表达思想的两种方式——隐喻和转喻模式入手,指出了隐喻和转喻的区别不仅能说明文学史上存在着这种循环规律,还能说明创新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回到它所否定的风格之前的那种风格上去,因为,“如果雅克布森是对的话,那么一篇文章除了这两种写法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可能了。”[7] 洛奇据此学说,指出文学具有“转喻型”和“隐喻型”这两种基本形式:前者的达意方式与转喻相似,依赖的是小说语言的所指之间的所谓相邻关系,即人、物或事件之间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后者的达意方式与隐喻相似,依赖的是小说语言的能指之间或所指之间的相似关系,即承载文学意义的意象、动机、语言特征、事件等的有机重复。如此详尽繁复的阐述足以表明“戴维·洛奇……是一个很老练的文学评论家,他对隐喻转喻悉数尽知……”[8]洛奇的小说“以研究结构主义,巴赫金,小说理论及写作技巧而驰名西方批评界”。[9]
隐喻话语与转喻话语的并行
小说《美好的工作》的开篇采用转喻话语分别讲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人物在同一时间的活动。与转喻话语同行的是两个人物活动的并行表现的相似性所实现的隐喻话语。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开始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二日,星期一。维克·威尔科克斯毫无睡意地躺在漆黑的卧室里,等着石英闹钟发出高音调的闹音。”[10] 然后是“闹钟响了。”[11] 再后来是“壶开了。”[12] 然后是“现在,一天中最美的半小时、开车上班的半小时开始了。”[13] 最后是“栏杆抬了起来,他将车开到办公楼正门边他个人的停车位置。”[14]描述了男主人公维克从醒来、起床、洗漱、读报、吃早饭,到驱车上班整个早晨的行为,其活动的连续性延展以及由于时空上的联系而实现的转喻式延续,体现了转喻是“在单一的连续的话语世界中移动而产生联想”的话语形式。第二部分开始于作家有意识地介入:“好啦,让我们暂时撇下维克·威尔科克斯,在时间上后退一、两个小时,空间上后退几公里,去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15] 继而展开了对罗宾一系列活动的描述,从“在这个一月的早晨,罗宾起得比维克稍晚。”[16] 到“她走进文学院大楼的门厅”[17],作者同样以罗宾从早晨醒来到上班的连续活动的叙述,展示了围绕着另一个人物的转喻式话语。在第三部分中,罗宾和维克上班后各自的行为虽然是在交叉叙述中展开的,但作者对罗宾和维克的行为分别用九个片断进行穿插描述,使读者通过前后参照整合出两人各自的工作情形。作家有意识地将两个人物的相似行为分别进行叙述,维克的故事和罗宾的故事就变成了具有共时特性的选择轴上的两个选项,因此在转喻话语中赋予了隐喻话语的表现。作者在共时面上描述维克和罗宾的行为不仅体现了隐喻话语模式,实现了转喻话语与隐喻话语的并行,而且加强了这部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喻性言说,也使“联系多重世界而产生联想”的艺术形式得以成形于小说之中。两个人从性别、背景、职业、志趣、婚姻状况到品性、气质、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对立,其实就是作家对大千世界中普遍存在交流缺失的隐喻。
隐喻话语与转喻话语的交融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两个人物各自的故事慢慢演变为一个有关两个人的故事,原来并行的隐喻话语与转喻话语交融在了一起。因为政府的“影子计划”,鲁米治大学的罗宾被派到实业家维克的工厂,以期实现不同领域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这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两个人物走到一起,也使小说一开始还是两个人物的故事融汇成一个故事。为避免被裁员不得已而为之的罗宾冒着风雪驱车来到了维克的工厂,心不甘情不愿的维克只好带着她各处参观,由此开始了校园文化背景下的罗宾与工业文化下的维克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故事也进入发展阶段。罗宾初到工厂就对工人们所喜爱的裸女照进行批评;她干涉工厂任免一个员工引发了丹尼拉姆事件,结果工人们闹起了大罢工,使她和维克的关系剑拔弩张。为弄清谁抢了普林格尔工厂的生意,罗宾跟着维克拜访柯尔,一路上两人对各自的信仰互相攻击。罗宾对“断愁”和“孤独的牛仔”的广告所进行的精辟的文学阐释并没有得到维克的欣赏,两人始终处于交锋之中。丹尼拉姆事件差点引起的大罢工最后以劳资双方的和解而告终,罗宾对奉行利益准则的维克也从厌恶变成了“他是个有艺术性的暴君”[18] ,而她个人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她开始对自己的某些文学观念产生怀疑。在维克眼里,罗宾也从“一根肉中刺,变成了一个他高兴见到的老朋友……她还可以为他分析问题,修正解决难题的办法。”[19]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两人在法兰克福之行中的一夜情,“维克多·威尔科克斯和罗宾·彭罗斯在法兰克福最终一起上床是不可避免的事”。[20]他们的身心交融使读者满以为小说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信奉解构主义的罗宾却认为“没有爱这种事”,“只有语言与生物学的东西”[21],面对维克的一往情深采取了躲避策略。维克要娶她的想法以及为更多地了解罗宾的事业而下放学院阅读小说的努力虽使罗宾厌烦,却也使她感动。在维克失掉工作时,罗宾把所继承的遗产借给他开办新工厂,两人最终成为好朋友。他们虽然没有结婚,但实现了精神上的沟通。这个关于交流的故事包括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历经矛盾的产生、矛盾的解决、沟通的实现,显然是作者按照人、物或事件之间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展开的,所以具有转喻话语特征。然而故事的焦点——两人不断的矛盾及其解决——揭示了这一个表面线性发展的故事在其深层结构上还是两个人的故事:罗宾寻求沟通的故事和维克寻求沟通的故事,这一点从作家对两个人物塑造力度的并重上也可以看出。两人各自寻求与他人交流的故事所具有的隐喻性话语特征是按照相似性原则进行的,与小说开头两人各自的故事并行不悖的展开方式相比,具有隐性存在意义。因此,隐性的隐喻话语与显性的转喻话语融合在一起,续写着个体生存的意义及其寻求轨迹。如果“隐喻可以传达新信息,是一种认知工具”[22],那么隐喻话语实际上具有丰富转喻话语表现内容的功能。由于两项并存才能实现隐喻话语模式的建立,洛奇以这种隐喻话语方式将交流的必要、交流的前提、交流的可能等转喻话语模式下的主题意义一一托出。
转喻话语的隐喻意义
由于两个人物的故事由小说开头的显性并存到情节发展过程中的隐性并存实际上是依托于故事情节的转喻式话语延伸的,所以随着情节走向结局,转喻话语越来越表现出隐喻意义。小说结尾,随着洛奇笔锋直转,维克被辞,对罗宾的爱奇异消失,回到自己的妻子儿女身边,只留下罗宾自己思索着是继续留下来还是远赴大洋彼岸另一个文化的国家任职,隐喻话语中的两个选择项只剩下了罗宾一个人的故事在继续着转喻话语的延续。她一个人驻足窗前,发现“其中一块草坪上有个园丁……当学生们发现他们躺在了他马上要剪的地方,就站起来拾起他们的物品挪挪位置,像一群鸟一样栖息在另一块草地上去。那位园丁的年龄与学生们相仿,但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没有点头、微笑、言语,甚至都没有瞥一眼对方。学生们那一方没有可见的傲慢,年轻的园丁一方也没有明显的憎恨,只有一种本能的对相互接触的回避。他们的身体彼此近在咫尺,但他们居住在两个截然分开的世界……会想起他那幅普林格尔工人们访问校园的乌托邦式幻境,罗宾暗自沮丧的笑了。任重而道远。”[23] 如果以为隐喻话语至此退出话语场、只留下转喻话语的单声部是不确切的;这时的隐喻话语实为“转喻性文本的隐喻意义。”[24] 盖依罗瑟拉曾说:“描述性最强的、或最现实主义的作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隐喻,但这隐喻暗含并贯穿在连续的叙述之中,在不同的地方显示出来,最明显的是在作品的结尾,显示出作品对生活的比喻、对现实的比喻。”[25] 洛奇在全书结尾使维克不在场、只保留罗宾一人的故事的手法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真正沟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与洛奇在小说结尾通过罗宾放弃大洋彼岸的高薪职位所表现出对文化间实现沟通缺乏信心所表现的“最终的交流是不可能的”这一主题是一致的。
结语
转喻与隐喻话语及其表现形态是洛奇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创作的小说《美好的工作》中理论意识的彰显。洛奇主张现实主义文学是转喻式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是隐喻式的。转喻话语与隐喻话语的相互依存作为《美好的工作》的主要话语特征,不仅表明这部小说实现了现实主义的内容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对话,也表明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意义的不确定性,因为小说的转喻话语言说的不同领域的人实现真正交流的可能性,而隐喻话语则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无法达到真正交流。人和人之间到底能否实现交流的答案就在转喻话语与隐喻话语的对话中,它为读者参与这种对话提供广大的空间,也以独特的方式书写着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作家对表现现实的情愫。
*本论文是鲁东大学校基金重点项目(202-23480301)成果之一。
注释:
[1] Bergonzi, Bernard,David Lodge, Nothcote House, 1955, p48.
[2]王逢振:“前言”,载《戴维·洛奇文集·美好的工作》,作家出版社1998版,第2页。
[3] Contemporary Novelists. Manuscrip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Library, p623.
[4] Siegel, Fred, “Vic and Robyn Go to Work”, Commonweal; Aug 11, 1989; 116,14;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442.
[5] Jacobson, Roman. See David Lodge, 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 Edward Arnold Ltd. London, reprinted, 1979, p74.
[6][24] Lodge, David ,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 Edward Arnold Ltd. London, reprinted, 1979, p80; p110.
[7] 戴维·洛奇:“现代派、反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王家湘译,《外国文学》第4期,1986年,第68-73页。
[8] Lerner, Laurence, “The Return of the Signified”, The Spectator; Sep 24, 1988; 261, 8359;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37.
[9] 凯蒂:“学院小说家:大卫·洛奇”.《读书》第4期,1993,第125页。
[10-21][23] 戴维·洛奇:《美好的工作》,罗贻荣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17,23,27,30,49,210,237,257,284页;378页。
[22] 束定芳:《隐语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25] Rosolato, Guy, “The Voice and Literary Myth”,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ed. Macksey and Donato, p202, see David Lodge, 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 p110.
(张素珍,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菊丽,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