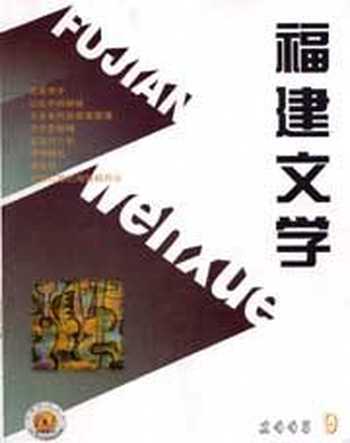疏勒河牧歌
王新军
在疏勒河中游,有那么一片地方,我们曾经叫它大槽子。印象中,出了村子顺着疏勒河向西走,一直向西走,到了有一片黑树林子的地方,再向北,过了油路、也就是312国道,再过一条大渠,从饮马农场十七队居民点的西面绕过去,向北——就是大槽子。
高处的大片荒滩被开垦耕种了以后,这一溜子低洼里的草滩湿地被夹在了中间。大槽子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它长得很,也宽得很。草好,是牛羊的天堂。泉眼一个接一个。巨大的泉眼四周,芦苇长得比房子还要高。好家伙,黑压压的,人走过去,就会有野鸭子呀水喳啦呀什么的扑棱棱从草丛里飞起来。有时是一只,有时是几只,有时候则是一大片,猛然飞起来,黑云一般,把天上的太阳都能挡住。
这里就是父亲带我放过羊的地方。因为它距离我们的村庄实在太远,跟父亲去大槽子,一年当中也不是常有的事情。正因为去的机会不多,所以经常想着去。又因为去那里的时候,父亲常常把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地挂在嘴上,时刻响在我的耳边,拘束得不得了,除了能用眼睛四下里望一望,似乎并不过瘾。比如那些巨大的黑森森的泉眼,被芦苇紧紧包围着。那些泉泉相连而形成的湖沟,里面除了水草,还有野鱼。大槽子里那么多秘密,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越是这种好地方,父亲越是不许我靠近。那时候,做父亲羊群里的一只羊,都要比我自由得多。那时候在大槽子里,能做一只羊在我看来其实也挺好的。那时候我就认为,父亲对我的约束是小题大做了。不就是放个羊嘛,把自己当成个威风凛凛的大司令似的。放羊,谁不会?羊自己有嘴有腿有眼睛,只要到了有草有水的地方,它们饿了就会吃,渴了就会喝。这难不住谁。我这样的心思,完全被父亲看透了。
那一天,父亲很突然地对我说,他想荚美地睡一觉。那意思是明摆着的,我马上就把父亲撂过来的话接上了。不接显然是不行的,这就像两个男人过招,人家都放马过来了,你不抵挡就显得太那个了。我说:“那我去放一天羊吧。”
父亲故作愕然地立直身子,看着我说:“你……不行吧!”
我瞥了一眼被清晨的太阳映得瓦蓝瓦蓝的远空,大声说:“咋不行,不就是放一天羊嘛,又不是上战场。”
父亲也把目光从我身上收回来,向远处投过去,佯作十分勉强地说:“行呀,那你就试一试吧。”
父亲其实当时已经看出每一次我皱起鼻子后隐藏在身体深处的那种小公牛才有的执拗了。
父亲能把那么一大群羊的心思一只只揣摩透,把我个十来岁的娃子,他是不放在眼睛里的。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执拗,就叫父亲有些受不住了。因为我的那种执拗,看上去仿佛我已经也是一个父亲了的那种样子。完全是自以为是那种的,完全是自不量力那种的。父亲当然要拿我一把了,不这样他就不是我的父亲了。当羊群里出现了那种捣蛋羊的时候,父亲轻而易举就能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我嘛,一个碎娃子嘛,父亲根本不放在眼里。
父亲指着那一圈羊说,好,你就试一试吧。这话一下子就把我的性子激了起来。我用不惯父亲那根差不多被手上的油汗浸透了的放羊棒,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用鞭子;鞭子好,举手向上一甩,再向下一抽,鞭梢子绕出几个麻花,嘎的一声脆响便能在空中爆炸开来,像过年时候从手里扔出去的粗炮杖,对羊是极具威慑力的。但因为是独自出牧,我还是觉得应该拿上最乘手家伙才放心一些。我把羊毛鞭,牛皮鞭,胶线鞭,麻绳鞭统统拿出来,摆弄了半天,最终还是无法确定或者说难以定夺的时候,我这样问从身边走过来的父亲:“哪一种鞭子抽在羊身上,羊最疼?”
父亲在我面前停住,没有马上回答我,他用那两只褐黄色的眼珠看着我,不是看着,而是紧紧盯住我的眼睛。那一刻,我蓦地发现父亲的眼睛是那样深,比我先前看到的大槽子里最深的那只无底黑泉还要深。那两枚草黄色的眼仁一动不动,让我在那个夏天的日子里有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寒冷。那丝寒冷从脚后跟处生起,直冲脑顶。我的头发梢子都凉飕飕的。父亲就那样看着我,事实上父亲只是看了那么一小会儿,也许几秒钟。但那几秒钟却被我的某种意识在脑海里无限拉长了。我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这时候父亲突然开口了,他放慢速度,低沉着声音说:“娃子,鞭子抽不疼羊,能抽疼羊的是人的心——你腔子里那个心有多狠,羊就有多疼。”说完这句话,父亲就撇下我自个走了。
父亲的这句话,一直叫我琢磨到了今天。
后来当我琢磨出一些意味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起父亲手里的那根滑油油的放羊棒来。如果不是用来打羊,父亲手里老是握那么一根气势汹汹的棍子做什么呢?我甚至以为父亲当时说那句话的时候,是害怕我如果发起脾气来,会把他的羊打坏。我注意的结果是令我吃惊的:父亲经常握在手里的那根放羊棒,其实是很少在羊身上去找落点的。每一次,当羊去了它们不该去的地方的时候、我以为那肯定是父亲把棒撂过去打中它们的时候,但每一次我都失望了。父亲总是要呔——呔——或者哦——哦——地喊两声,如果羊知趣地回头走过来了,父亲脸上就露出那么一丝娇柔的欣慰。然后拄着那根放羊棒,继续向远处张望。如果羊在听到了他的警告后仍然犹豫不决,或者根本就是蹬鼻子上脸的那种置若罔闻理都不理,父亲就会嗨地一声,一甩膀子,将手里的棒子撂出去。但往往这种时候,棒子落下去的地方,距羊的身体其实很远。羊被哗一下吓回来了,父亲才慢慢走过去,拾了他的放羊棒,在那里站一会儿。这时候,父亲脸上露出的也是那种带了一丝娇柔的欣慰。父亲像一个胜利者一样站在那里,显出非常伟岸的样子。
那一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拥有权力的快乐。那么大一群羊呀,我让它们到哪里它们就得到哪里,我让它们吃草它们就得站下吃草,叫它们什么时候走它们就得马上给我走。那天的羊被我折腾坏了,我像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比现在的那些小科长小处长要高明得多。羊被我玩得团团转。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却被羊美美地玩弄了一把。我的心情完全就是一个小政客冷不防被对手从政坛上一把掀翻的那种样子,我差不多都要绝望了,心情灰到了极点。那天中午,因为羊被我吆来喝去一直就没怎么正经吃草,我却还为没有走得更远而感到意犹未尽。毕竟是在大槽子嘛,大得呔嘛!
太阳已经偏西了,羊不可能空着肚子或者说只吃个半饱回家。羊固执地来到了一片湿地边,那里有一片丰美的水草,羊肯定是受到它们的诱惑了。但那片地方父亲平常是不愿意让它们靠近的。父亲曾经说,别看那里水草好,其实是一片紫泥溏子,羊到那里去,是要吃亏的。但我记起父亲那句话的时候,已经晚了。羊群像一伙囚犯突然获得了自由一样看着那片开阔的湿地就冲了过去。
起初羊只是散开在那片宽阔的湖沟一侧吃草,被羊踩浑的泥水也只没住羊的多半个小腿。我知道,这样的深度对于一只夏天的羊无足轻重。但是,有那么一只羊——黑
头白鼻梁的老母羊,它吃着吃着就不自在了。它看了几眼湖沟中间的水草,张开鼻孔嗅了几下,就自以为是地向前迈了过去。它终于衔了一嘴鲜嫩的水草的同时,四只蹄子也陷进了脚下的烂泥里。仿佛底下有四只神秘的手把它们拽了下去。它挣扎了几下,非但没有走出来,反而越陷越深了。在它已经感觉无望的时候,它就安静下来开始咀嚼衔在嘴里的嫩草。恐慌和绝望使它一时不知所措了。整个羊群就是这时候从一片惊慌中安静下来的,它们看见那只黑头白鼻梁的老母羊正站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吃着嫩草呢,它们却看不到它四只蹄子下面的危险。然后,有一只不甘示弱的羊向前走了几步,还没有来得及伸出嘴巴就陷了下去,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
所有的羊就那样争先恐后地往前冲,它们不顾我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的挥鞭阻挠,完全是慷慨奔赴奋不顾身的那种样子。它们有的甚至兴奋地跳了一跳,然后就落在湖沟中间的烂泥里不动了。
这里是大槽子深处,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被陷入稀泥中的羊群的镇定吓呆了。
当太阳落尽我赶着一群被污泥染成黑色的羊回来的时候,父亲在村西边的那座木桥上用一片祥和的目光迎接了我。我早巳精疲力竭,被羊群远远地甩在后面。父亲根本不用问,看那些羊,父亲就什么都知道。
我一连睡了两天才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气色。
有了那次经历,或者说有了那半天在烂泥里独自对一群羊的营救,我的身体里好像多了些什么。三天后,父亲在饭桌上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父亲说:“男人嘛,泥里头好好滚上一回,就啥都知道了。”母亲对父亲这话不以为然,摸了摸我的头,怜爱地说:“你看嘛,把娃整的,脸都瘦下了一圈圈。”父亲说:“娃子家嘛,不泥里水里滚一滚,咋长大咧?说得。”父亲这么说,母亲似乎也只有赞同了,又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这一次,我把她的手挡开了。我确实觉得我已经长大了。
后来,我又长大了一些的时候,又和同伴们去过几次大槽子,还在那里用农场职工从麦地里拔出来的燕麦草,烧着吃过几次青麦子。——青麦子放火堆里烧黄了,在掌心里一揉,用嘴噗地吹掉麦衣灰,呼地扬到嘴里,一嚼,嘿,贼香。吃完了,每个人嘴上都有一个黑圈圈。去泉边洗,如果不认真,有时候洗不掉。
再后来,我们家的羊就全部卖光了,我也再没去过大槽子。
大槽子,这几年听说也因为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泉水干了,草不绿了,鸟也飞走了……这些年,听说那里已经被新的开发者垦成了大条田。只是因为碱大,缺水,一年一年闲撂着。春天,风起时,横扫河西走廊黑洞洞那一片,最先就是从那里刮起的。
这些天,因为常常想起父亲,所以想起了大槽子。于是动笔记下了这些与大槽子有关的文字。
散文责任编辑: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