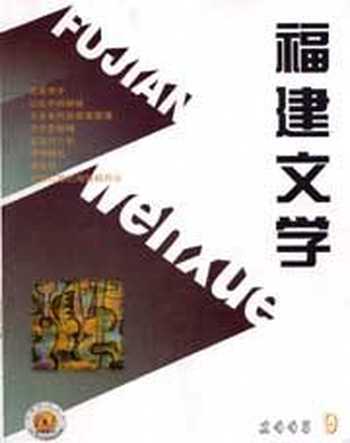《两地书》里读鲁迅(外一篇)
关海山
鲁迅先生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历来以冷峻的面孔、战斗的姿态活在其崇敬者的心中,而事实上,那仅是先生生活的一个方面。每个人都有多重性格,只看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区别罢了。与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先生同样有炽热的情感、缠绵的爱恋、无助的孤寂、忧人的愁烦,以及虚浮的幻想、琐屑的计划——1925年至1927年间先生与许广平女士的来往信函结集而成的《两地书》便是向读者展现了如此这般的鲁迅先生。
《两地书》是先生与许广平女士热恋期间的通信集,实际上是一本情书。在这本情书里,虽然并“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只是信笔写来,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但因为信札通常只是写给第二个人看的,也许写作之时并未准备将来竟要拿去发表,故字里行间谈人生,谈读书,谈当局,谈新闻,谈政治,谈对之感兴趣的一切话题,无拘无束,遣词造句也更朴实,更率真,反而较别的文章更容易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
情书的特点贵在情真。先生与许广平交往之时,已愈不惑之年,但双方那滚烫的爱,实不亚于青春男女。1926年先生应林语堂之邀去厦门大学讲学,初到甫定,便连续收到许广平的两封信,“高兴极了”,立刻致信给对方:“这几天,我是每日去看信的。”随后把自己即使非常细小的生活末节也不忘告诉对方:因为厦大当时的校园环境尚不太好,杂草丛生,颇多小蛇,所以,“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教课一段时间后,“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并且将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大。”多么诙谐而又坦诚的表白啊!更有意思的是许广平,“这封信特别的‘孩子气十足,幸而我收到了。‘邪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邪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料不到先生又能回信一封:“我那一日的信既已收到,那很好。邪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这哪里看得出来竟出自一位文学大师的婚恋,简直就是痴郎情妹的憨直、调皮,浓情切意,跃然纸上!岁月悠悠,有时候一天收不到许广平的信,先生便坐卧不安;有时候,双方一天都要写两封或几封信:“今天下午刚发一信,现在又想执笔了。这也等于我的功课一样,而且是愿意做的那一门……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些。然而也不喜欢托人带出去,我就将信藏在衣袋内,说是散步,慢慢地走出去,明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秘密事,但自然而然地好像觉得含有什么秘密似的。待走到邮局门口,又不愿投入挂在门外的方木箱,必定走进里面,放在柜台下面的信箱里才罢。”以致只要写好了信,哪怕半夜三更,也必须即刻投进邮筒,方可安睡。
由于信札的特点,于其中更可看出先生的人品和道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魄!但是,对于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先生却总是嫉恶如仇,横眉冷对:“白果尤善兴风作浪……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生活中,抱此高尚态度的恐怕是不乏其人,然而,真正能够做得到的,又有几多?
三句话不离本行。自然,书信中怎会少了对于文学的观点与探讨?像那句著名的“诗论”“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关杀掉”就出自1925年6月28日先生致许广平的信中。还有一些语句,幽默酣畅,一针见血,很能体现先生的为文风格:“看目下有些批评文字,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而骨子里却还是‘他妈的思想,对于这样批评的批评,倒不如直截爽快地骂出来。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人我均属合适。……我常想: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于新的用新法,对旧的仍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的法律:打屁股。因为这是他所佩服的。”放至今天读来,仍不失为需人深思的座右铭。
通览《两地书》,又使我们认识了作为“凡人”的鲁迅先生。猛看乍想,如此矛盾、抵牾的两个形象实在太难让人合而为一了,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完整的“鲁迅先生”。我想,这个事实非但不会丝毫有损于先生的高大形象,反而更会增加先生在人们心中的亲近感与真实感——同食五谷杂粮,不生七情六欲,怎能让人信以为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