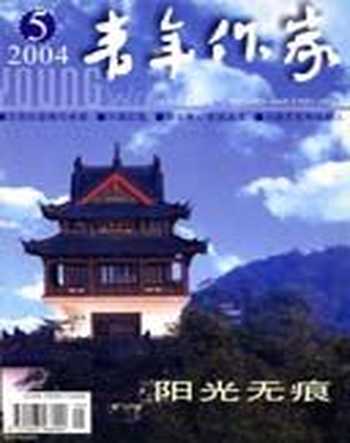孤城夜场云顶寨
赖 武
当有机会走近一座封闭的城堡或寨子时,除了引发人们对城市初期防御与交易功能的联想,还可能唤起种种有关家族聚落和延传方面合情合理的思索。隆昌云顶寨几近蜕化与残缺的古城格局正是这样成了关注者考察其文化演变的突破口。
云顶寨外的云顶场,由跑马道与寨子相连而呈丁字形。石板路,铺面街,也是买卖兴场渐渐发展起来。该场的建立与生意都与寨主郭氏家族密切相关,即由郭氏家族控制并为其服务。本地人说场上房子95%为郭氏所建;寨子兴旺时,场上商业也兴隆,从酒店茶馆到钱庄商号到山货铺、绸缎铺、药铺、米铺等一应俱全。当然,这种景象已不知逝去了多少年。
沿着跑马道朝上走几步就到了赫赫有名的云顶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杂草丛生的古城墙,在最先到达的通永门城洞前有一石碑,略述城墙情况:该城在清咸丰九年(1859年)由当地郭氏族祖修建,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新维修,占地245亩,城墙长1640米,有六个门洞。城内有154个天井云云。
据载郭氏始祖郭孟四在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从湖北麻城入蜀,走剑云顶山垭,挑行李的箩筐滚下山去,于是干脆就地插田耕种,定居于此了。后代郭廉、郭元柱先后在明代中进士,居高官。郭氏世代簪缨,渐成云顶大族。郭廉归林,就曾于山顶筑巢,因山高取名“云顶”。世族官绅,人丁资财俱富,田亩庄院并阔。到明末万历年间,更因地方上贼匪出没而垒石为墙、筑寨保安;直至清咸丰九年(1859年)郭人镛“奉父命建云顶寨”,光绪二十年(1894年)郭祖楷对城寨扩建加固,才形成了今日如县城般规模的城墙。
进了城寨,顺着石板小路拾级而上,除零星房舍,似已没有完整院落。在一个演武厅旧址的坡上,阔大的台地已犁成田园,早已不闻刀剑声,且人烟稀少,山野气息扑面而来。天近黄昏,不能深入,从日升门钻出便见明月高悬,而夕阳斜晖洒在城墙上,周遭沉寂,仿佛激烈的攻守战刚刚偃旗息鼓,此情此景,心中自然咏出“孤城落日斗兵稀”的诗句。
夜宿场上梁三哥家,晚上就在他家堂屋里吃的饭,我们边喝酒边聊起云顶寨的遗事,梁三哥晓得的事真多。他说,寨子里庭院建在起伏的山坡上,形势风光都好。此处脚踏二市两县(内江、沪州、隆昌、沪县),按军事要塞在山顶筑城,上有炮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里面有煤有井,有火有水,粮食牛驮马载,城墙砌后用糯米浆子刷过,加上武装(最多时期,除寨丁外另有两个营的兵力),当真是有金汤之固。
郭氏为五百年世家,经历三个朝代,民间有“云顶国”之说,因其地盘纵横县南40余里,如古代诸侯小国:且兵多粮足,固如城堡:加之族权高于一切,族长政由己出,有生杀予夺大权;甚至不受制于官府,权势财富在当地无有能敌。
但当你摸摸城墙砖与寨里残留的建筑,看看草深掩没的石径与荒废了的军事和生活设施,你不由得对一个家族经过多少代人艰辛奋斗达到辉煌再走向衰落的结局而发出深深的叹息!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当国家尚且处在动荡不安、朝代更替之时,一个家族何谈稳固及持续鼎盛呢?
说到郭氏移民四川,梁三哥熟悉张献忠进盆地后移民们的插占为田,但当时的移民入川带有强制性,很多是绳捆索绑来的。今天见老年人走路好背手便由此相延成习;被绑者只有大小便时解开绳索,故川人进厕说“解手”。梁三哥又说本地人坐滑竿是脚朝下,背朝上,好像也是出于戒备,想看到上山的是什么人。郭氏豪族,一姓之寨,树大招风,怕人算计的心理是有的。
最有趣的是云顶寨的夜场,即夜色迷蒙的凌晨赶场。开场时,能见山道上一路而行的火把;交易时间短(一般为一小时),且“偷偷摸摸”,像是抢来的东西,故号“强盗场”。
我睡在梁三哥家的大花床上。为看次日所谓“强盗场”的情景,只好请梁三哥的妈妈第二天早点叫醒我们。他妈妈八十多岁了,每天要喝二两酒,身体健康得很。婆婆说,卖猪肉的凌晨4点过就要爬起来杀猪,5点钟就要弄到市场上挂起卖。于是,我决定要看杀猪。还好,宰猪就在梁三哥家街对面,所以次日赶过去,从宰到烫到剐到分解,整个过程,都看清了,才半个多小时,肉就弄到街边肉架子上了。
5点过,场上已有人影晃动,灯光从几家开起的店铺泻到街上,卖东西的蹲在街沿边,乡客穿梭其间,无喧哗声,感觉到底有点鬼祟,像贩违禁品。买卖主要集中在丁字街口,仔细一看也多是菜蔬、副食、日用杂货一类。让城里人看来,这些乡间生活所需多半不值得这样起早摸黑地做买卖吧。夏天亮得早,到6点半,天大亮时,夜场已散,老街又恢复平静。时间虽仅一个小时左右,然总觉这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集市除满足生存之需,不同地方又包含着本乡长年约定俗成的因素。作为特殊的社交场合,集市在乡村生活中隐隐起到了调节心理平衡的作用。说夜场有交往的意义,未免显得牵强而令人难以置信。自从几年前乡政府搬下山,夜场时间短,人也更少了,这买卖中到底掺和了多少长年因袭的行为动机或埋伏着别的什么复杂心理,谁也说不清。
早晨的阳光给云顶寨镀上一层富丽的色彩。逆光中挑水人身影的起伏仿佛是这里一天劳作的开始,并活跃着云顶寨的家族生活气氛。顺着石板路再进云顶寨,面对零星的小院落和山间不时可见的人文遗存——廊院、亭榭、桥道等颓垣残壁、雕刻修饰,情不自禁地又兴起对这“城”里几百年间豪门巨族的兴衰之叹。
既是“城”里,住户无论是否郭氏后人,多少都有着故寨宗族的统束,哪怕仅仅在心理上。不过,富华与威权已荡然无存,除了留给后人追忆与想象,逼真的与写实的就是复归自然的景观。尤为可人的是那称为如意池的大堰塘,上有落虹桥,桥头观鱼亭与池东古庙虽已不存,但池塘灵气依然,塘边果林,池中鸭群,诗人感兴,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清新而明丽。据说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郭仲华返回桑梓后便于池旁筑房,辟园种果,真林泉雅人。
在城墙里想城墙外,虽说都属云顶寨,但彼此的生活及关系在过去长长的日子里想来也有些戏剧性。而今天的云顶场则更能提供探寻本地世族人生的历史线索。顺街走下来,或见天井里的婆婆大爷,老宅伴着老人生活深沉得难以捉摸;或见很大很空的房中一小孩就着大方桌做作业,思维该是很放得开的;又见一老式中药铺,柜台里老人有学者之仪容,虽无顾客,但神态安详。在人少店稀寂静的乡场上,一个像样而洁净的中药铺不能等闲视之。旧时卖中草药多半懂传统医道,郎中应划为文化人之列。云顶寨的老人仿佛都出自书香门第,其面目多有文坛耆宿的风范,即使落虹桥上一看林人也难以掩饰地透着饱学之士的睿智。
梁三哥家也开着中药铺,并有一古色古香的匾,上书“得长桑诀”金字。梁三哥说他父亲靠行医为生,父传子再传孙,为医学世家。“桑”指垂老之年,“诀”是窍门,要健康长寿,须有好的医疗保健方法,梁父正是远近有口碑能延缓人衰老的名医,梁三哥说“我父亲从没有医死过人”,故有此匾。
后又踏进一家摆设古朴的房里。除古家具外,特别抢眼的是靠墙一转角矮柜上放置不少古陶瓷,在屋顶亮瓦透射光线照耀下散发着静穆的光泽,这种洋溢着古典气息的客厅在如今都市也是久违了。这并非气派豪华的客厅于细微处显示着主人家精神趣味之非同一般,它从另一侧面揭示出大家族物质优裕的生活背景,主人家姓万,正是对街药铺老人之子,娘家姓郭,果然与那寨子里世族血脉相连!令人感叹的是一个家庭要在现代物欲横流的社会拒绝五花八门的时尚诱惑而保留传统家庭格局,小心翼翼守候祖产,所谓不败家,当真不易;骨子里还要有承传祖先生活观的意识,包括趣味倾向,才有可能在这种传统摆设中怡然自得。屋里装饰细节展现了女主人的慧心巧手,她内心的自信及精神的依托似乎还远不只落实在室内装饰风格上,隐隐地还从某种意义上肯定这对一个家庭的稳固与长盛不衰是何等宝贵。
一个家庭没有丰厚的祖传家业便不能坐享其成,而社会动荡,人生坎坷,最不易留下的就是那些曾经长年使用、代代相传的家用物品;更兼有不思进取懒于创造的不肖子孙长的几年短的几月几天就把一个富裕的家业弄垮了。败起家来豪族也一落千丈,如郭家五百年厚实积累坍塌散落至此,谁能收拾?
老人说,败家从坛坛罐罐开始败起。易碎之物能传几世几代,亦足见一家庭之稳固。对于家庭、家族、家国而作的历史观照,后人又岂能仅仅满足于拾掇前世留下的文明碎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