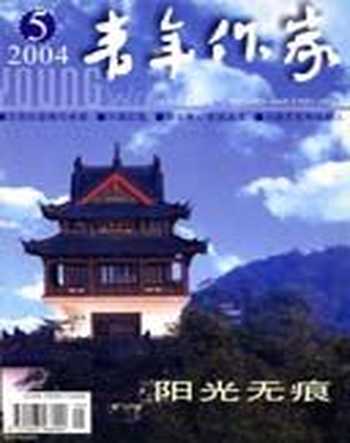停在我心里的温柔
落 苹
1992年初夏降临的时候,我和霖的爱情落下了帷幕,所有的情节就像一幕仓促的演出一样忧伤且不可挽回。然而那些柔软丰盛的记忆却停留在了我的心里,它们沉默如灰烬,同时又充满了火焰般的蛊惑——
我和霖是在一所靠近海滨的大学校园里相遇。霖是典型的北京男孩,面容清俊,身材挺拔,语气里总有轻微的调侃。他读的是中文系,非常唯美的一门学科。而我念的是冷僻的物理,很闷,很艰涩,整个班上只有我一个女孩子。
大一那年的圣诞节有一场喧闹的化装舞会。我因为做实验而迟到,面具还在我的同伴那里。我匆忙地在人群中穿梭,慌乱地呼唤同伴,灯光斑驳,那一张张纷乱的脸闪烁似鬼魅。
蓦然间我发现一位男孩,他戴着极其温和的猫脸面具,与我同伴的那个一模一样。我不由分说地牢牢抓住他的手臂,他轻轻挣扎,并试图解释,但我以为这一切都是一场玩笑。终于,他无奈地取下面具,露出陌生的脸孔,然后挽起衣袖给我看我留下的“罪证”,他的胳臂淤青了一大片。我很尴尬,惟一的念头是赶快逃赶快逃。
我一言不发地拔腿就走,他啼笑皆非地从后面拉住我,说:“这儿这么大,我来帮你找人吧。”那晚,我始终没有看见我的同伴,而他也不再带面具,一直陪着我。我们到落地窗前看碎雪在绚烂的灯火里纷飞。临近午夜他教我跳舞,很慢很优雅的那种。在偌大的舞厅中,只有他的脸是真实的。
他就是霖。很快我就知道霖在学校里是多么出色,每天傍晚的广播中都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他不断地放送好听的音乐。在去教室的路上,我常常忍不住驻足倾听,想起许多遥远模糊的往事,有一种浅淡的、无法言说的情绪蓦然袭来。可是功课是一团兵荒马乱地忙,我没有工夫挂念谁,霖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烟火罢了。
然而霖开始时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图书馆、餐厅以及我爱去的网球场,他不说什么,远远地对我笑,眼神很干净。深冬的一天午后,我照例去琴房后面那片安静的丛林,找个石凳子坐下,疲倦不堪地背公式,渐渐背得恍惚起来,昏沉欲睡。突然间有人弹起了钢琴,是我幼年时听惯了的一支叫做《绿袖子》的曲子,单调、重复,但是旋律异常美丽。我怔怔发起呆来。门开了,琴声戛然而止,霖走了出来。他在我面前蹲下来,把我的手握进他的手心,凝视我的双眼,轻轻说:“别打瞌睡,小心着凉了……”
真正决定接受他却是在两个月以后。那一次,在阅览室外,我偶然听到他和朋友谈起我,他叹息着说:“她对文学一点知识都没有,会把卡夫卡与昆德拉混为一谈,惨得不得了……但是越惨越爱她。”
最后那一句全是爱怜,又有点斩钉截铁的味道,刹那间,矜持的我懂得了他含蓄的等待,我明白错过了这样深情的男孩子,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大学里的恋情清澈而简单,我们不过是天天一起上自习。我习惯熬夜,霖在我身旁,携着Walk—man,翻翻小说,困得东倒西歪。他睡着的样子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望着他,我会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
在那之前我已着手准备去国外攻读学位。大三时,美国的小姨替我联系了一所学校。寒假我去了趟美国。霖在北京,给我打越洋电话,他的黑夜是我的白昼。小姨家正有一个聚会。在热闹嘈杂里,霖缓缓地说:“我在一万公里之外,心里只有你。”
就这么一句话,让我哭得几乎崩溃。我又回来了,我渴望我们的爱情在异域继续生长。没有想到,霖是坚决地不出国,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中文作家。他告诉我,他可以为我放弃北京,甚至放弃任何城市,我们可以去中国的任何地方,包括茫茫沙漠,或者是寸草不生的戈壁,都可以。但是他不出去,他要活在汉语里。
我们挣扎过纠缠过哭泣过哀求过,最后一起放弃了这个话题,他仍然在我看书时睡觉,我仍然在打网球时把他杀得片甲不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可是幸福有了大块大块零乱的阴影,感觉摇摇欲坠。大四来了,收到哈佛录取书通知那日,我独自在商场逛,专心致志地看霖酷爱的摄影器材,看了很久很久,满眼都是泪。
长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逃避。我对着镜子,练习那个表情:淡淡地看他一眼,若无其事地走开。我不想有一个泪眼凄迷、撕心裂肺的别离。6月,霖签了回北京工作的合约。他约我见面,我们说了些不相干的话,要了两杯红酒,克制地相互祝福,像两个普普通通的朋友,往昔忧欢都不再提起。
霖喝了酒,安静而舒畅,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回头望着我笑。有一辆车经过,遮住了他的笑容,又一辆车经过……忽然间,霖大声叫出我的名字,他说:“我爱你,请你永远不要忘记!”我在那样的告白里泪雨滂沱。
在美国的七年,我只是在读书,任由许许多多优秀的男人滑过生命的边缘。起初我以为时日的改变会让伤口痊愈。可是霖的爱情竟然是我惟一温柔的牵念,我是如此强烈地怀想当年穿着纯白芬芳的丝衬衫、被霖宠得一塌糊涂的日子,怀想他掌心的温暖皮肤的气息。初恋时那段年轻明亮的岁月就像熠熠生辉的招贴一样镌刻在时光的长廊中,永不湮灭。
2000年5月,我回国定居,选择了北京。我深爱的霖在三年前遭遇了父母双亡的惨痛,孤身去了内蒙古。那时他还没有结婚,甚至没有亲密女友——朋友知道的消息,就是这样。我决定去找他,去内蒙古,永生陪伴他。我张皇着迟疑着盼望着,从暮春到寒冷的冬天,我四处打探他的确切地址,我渴望有那么一天,能够站在他面前,微微笑着从容地说一声:
“嗨,霖,我回来了。”那样子,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别过。
可是,我爱的男人,此刻你究竟在哪里?
(ps:寻找易霖,北京人,1997年在内蒙古一所中学教书,1999年辞职从事自由撰稿。如果有人认识他,如果此时他依然独身一人,请转告他,我思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