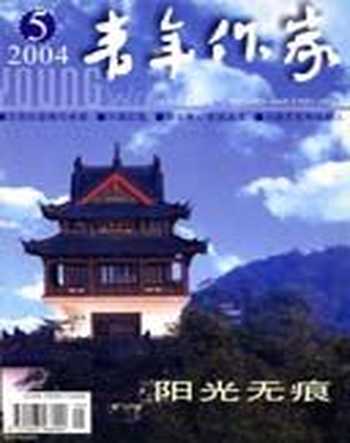川剧文化和成都人
曾智中
关于川剧,已故作家汪曾祺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有一位影剧才人说过一句话:‘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欣赏水平的高低,只要问他喜欢川剧还是喜欢越剧。有一次我在青羊艺术剧院看川剧,台上正在演《做文章》,池座的薄暗光线中悄悄地进来两个人,一看,是陈老总和贺老总。那是夏天,老哥儿俩都穿了纺绸衬衫,一人手里拿了一把芭蕉扇。坐定之后,陈老总一看邻座是范瑞娟,就大声说:‘范瑞娟,你看我们的川剧怎么样啊?范瑞娟小声说:‘好!这二位老帅是以家乡戏自豪的——虽然贺老总不是四川人。”
这段记载非常值得玩味。
七月流火,扇着芭蕉扇观朴野的川剧,是一幅典型的巴蜀消夏图。
而“影剧才人”的话。说穿了,说明白了,就是欣赏水平高的看越剧,欣赏水平低的看川剧。
可川人陈毅却“大声”问:“你看我们的川剧怎么样?”
越剧泰斗范瑞娟“小声”地答:“好!”
彼“大声”,此“小声”,耐人思量一也许她觉得剧场里不宜喧哗,也许为对方的声威所震,也许她内心深处觉得“川”不如“越”所以底气不足,也许她既爱“越”又爱“川”……
也许这一切都不是。
而我们不妨从他们所观的川剧折子戏《做文章》说起。
读小学时,一同学在课堂上鼾声大作,被邻桌唤起,教语文的班主任脱口而出:
春来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又冷,
收拾书箱好过年。
全班轰堂大笑,那同学窘得满脸通红,老师好像也觉得有些失之刻薄,赶紧讲课,这情景给少年的我们极深的印象。
成人后方知道这是《做文章》中宦门公子徐子元上场时念的一首定场诗,而在这之前,他还念了一段《字字双》,也足以令人喷饭:
头戴一顶花花巾,崭新:
身穿绫罗色色新,光生:
三年读本《百家姓》,聪明:
方知家父叫“严尊”,官称,官称。
照成都人的说法,此人是“资格”的“耍哥儿”,只知“晃”,不知“学”,故考期临近,惶惶不可终日。但他“我父在朝,官居一品”,开后门从试官那里预知题目,叫他照题作文,以便应考。哪知他耍尽十八般武艺,也挤不出一滴墨水,只得求书童单非英代做文章。
随着剧情的深入,喜剧的色彩越来越浓烈:
单非英小的替公爷出个主意。府内人多,不如请个人帮你做。
徐子元帮我做?对!你这话把我提醒了。(看单非英)单非英,不然,就请你帮我做。
单非英哟,我恐怕不行哦!
徐子元你茶都倒得来,一定得行。
单非英倒茶是小事嘛。
徐子元做文未必就是大事情!
单非英好倒却好,我没有座位,怎好写字。
徐子元噎,噎,那不是座位是啥?
单非英那是公爷坐的,我不敢坐。
徐子元公爷叫你坐,你就坐。(拉单非英坐)
以下“磨墨”,徐子元的“蠢”与单非英的“精”,更显得妙不可言:
单非英哎呀,这天气真热,刚才磨的墨就干了。待我去叫个人来磨墨。
徐子元不要去叫,不要去叫,旁人看见你替我做文,岂不笑我!公爷还是要点面子。
单非英公爷,你不晓得,我做文就不能磨墨。手磨软了,就不能写字了。
徐子元那么我来磨墨嘛。
单非英公爷还会磨墨?
徐子元唉,磨墨是我的家传,我家三代人都会磨墨。
单非英请问公爷,这话怎说?
徐子元我曾祖写字,是爷爷磨墨;爷爷写字,是爹爹磨墨;爹爹写字,是我磨墨。
单非英我今天写字喃?
徐子元还是我……哎呀,我说失格了。
“失格”,成都话,丢脸,丢面子。徐子元是自己丢了自己的面子,单非英顺着徐子元的话头,自然而然地当了“爹爹”,照成都人的说法,是占了徐子元的“欺头”。
欺头,又写作“颠头”,有的学者认为,古人出丧,前面有一具纸扎的大鬼,称为“方相”,开道引路;此外丧家还要用米粉和面粉做一些鬼脑袋模样的东西,沿途抛洒,与“方相”的作用一样,可以辟邪,路人都可捡而食之,谓之“欺头”。也有的学者认为买东西时店家额外添的那一点叫“欺头”,比如你买5斤炖肘子老板给你加一根棒子骨,你称10斤葵花子老板给你添一捧炒花生,等等。
在成都话中,说某人爱吃“欺头”,就是说他爱占别人的便宜,这是挺使人生厌的行为。
但有一种占“欺头”,在川人中却非常盛行,时间悠久,范围广泛,乐此不疲——这就是冒充别人的长辈,在幽默取笑中,我辈分涨一尺,他地位矮三分,看对方的尴尬和窘态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无伤大雅,取乐的智力水准得到大大的提升,使平淡的日常生活的空气中充满了愉快的分子。笔者当工人时,曾见一位工班长逗一位女工的小儿子,他认真地对那小孩说,不要喊我爷爷喔,喊我爷爷我肚子要痛喔!那小孩于是拼命喊爷爷,他一面痛苦地捂着肚子,一面拼命地抑制那快要抑制不住的笑意。
所以,《做文章》每次演到这里,场子里都要腾起快活的大笑;而笑得最爽、最会心的往往是成都人,就像他们自己又占了一次别人的“欺头”似的。外地人也会笑,但其痛快的程度相应地要低得多。
文章做好,徐子元兴奋得语无伦次:
徐子元(唱)接过文来仔细瞧,
一点如桃,一撇如刀。
写得好,写得妙,
比我的爹爹书法还要高。
单非英公爷夸奖。
徐子元今天把你费了心了,我钱头有二百柜子——哦,柜子头有二百钱,你拿去买顶帽子。
文章交卷,徐母大喜,叫徐子元立即送文章过江到崔天官府中相面对文招亲。徐子元情急之中,逼单非英代劳,可另外一个书童不服气,不愿侍奉单非英前去。
徐子元你敢说不去!(欲打)
书童娃去,娃去。娃跟他去。
徐子元那就快走。
书童我怎么称呼他呀?
徐子元唉!他是替公爷办事。好,好,好。你喊他一声公爷,公爷给你一百钱。
书童喊十声?
徐子元十百钱。
书童喊百声?
徐子元一百钱。
书童喊多了怎好记账嘛?
徐子元你就在你那丝绦上打疙瘩,有好多算好多。回来跟公爷算疙瘩账。
剧情发展到高潮,单非英上马,书童连呼:
书童公爷慢点,公爷小心,公爷……(在丝绦上打疙瘩)
徐子元你在做啥!不要在这里就打疙瘩,要过了江才上账。嗨!不要记冤枉账讪。
书童我该不得上当呃?(下)
我曾经在成都北郊的小镇弥牟镇上见过一个草台班子演出的这折戏。午后两三点钟的太阳,从茶馆顶棚的明瓦中斜照在台口徐子元张皇的脸上,书童一边在丝绦上打疙瘩,一边冲台下挤眉弄眼。
他的正在掺开水的父亲和正在收茶钱的母亲强忍笑意,也朝他挤眉弄眼。
茶客们则开怀大笑,立在门口的那位老者几乎笑岔了气——他的身后牵着一条牛,牛的腿上沾着泥和青草,他的腿上也沾着泥和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