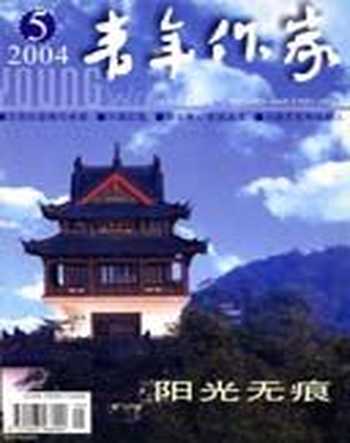教授喷嚏
马步升
本来不打算把这件不名誉的事情公诸于世的,徘徊几年了,我终于要涉险迈步了。一件事情如果长久窝在心里不吐出来,犹如患有积食症,那份难受,诸位明公想必多少都是有些体会的。
事关师道尊严说话不可不慎,而促使我下决心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恰恰为师道尊严故。因为师道的前提应该是尊严。先贤有训:为尊者讳。可尊既不尊,讳又何必。而当尊还须尊,当讳还得讳,折冲尊俎,还是尊其名讳,以“教授”指代,述其行状,务求真切。教授是我的授业老师,幼承家学,长投名师,以传统国学为业,根底匪浅。后入右派籍,发配边地执教,虽遭打击,却授业解惑,得其所在。这样,我就成了他的学生。教授还是教授那会,刚改革开放,人心思奋,教授虽人届中年,欣逢盛世,得释重负,便意气奋发,术业日进,一时学名远播。这几年,教授是当之无愧的教授,青灯黄卷,孜孜矻矻,教书育人,不遗余力。在我国,重视人才的最显著标志,便是给个官做,不管他是否合适。到我出校门时,教授开始涉足政界,官封科级。我们几位同学劝他别做官,一个名教授当小科长,掉价。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学而优则仕,要使政治清明,必须贤人主政,我虽是小科长,可这个科因为有了我而改良了土壤成分。以此类推,全国有千千万万我这样的科长,大环境不就改善了吗。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还年轻,书生意气重些,再过若干年回头看,你们就会知道我今天当这个科长的非常意义了。
天缘凑巧,我给教授当了科员。此时的教授一身二任,起早贪黑,腋下夹着公文包,鼓鼓囊囊,一半文件,一半专业书籍,行色匆匆,惜时如金。初,科长教授正在上课,单位令他停课开会,他怒形于色,慨然言曰:这两个小时我属于我的学生,国家主席来了,我也得把课上完再去见他。学生们感动得泪花盈盈,以在如此傲岸敬业的老师门下为徒倍感荣幸。过了一年多,教授变了,在书房和教室的时间少了,在办公室和会议室的时间多了。他的官衔年年走高,5年后,品秩正局。而这期间,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已很难见到他的点滴文字,专著却一年推出多部,语涉文史哲经教育时事政治等等领域,可谓视接千里,精骛八极,触类旁通,游刃有余。而每本书的封面上挂的都是“主编”头衔,书中内容没有一句出自他手,需要他做的只是签上大名而已。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每本书的面世是离不开他的,他得动用权力筹资出版,并动用权力发行。
教授越活越会活,手捧每一本新书,辄洋洋自得,不分场合地点炫示于众,心情太好时,忍不住还会主动签名赠我一册,我手捧非业师所著的业师新著,往往惶恐无着,想说一句“谢谢老师一定拜读”之类的客套话吧,就好比要把与老师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人,当成老师的亲生子女对待一样,怎么着也觉别扭腻歪,弃置不顾吧,老师却又真真切切是此人法令上的生身父亲。老师都认可了,做学生的何敢不认?脱离现场后,又不能当垃圾处理,只好装进专门安置闲杂书的柜中,闲杂书也有偶尔一顾的价值,这便免不了看见老师的挂名之作,看见一次,沮丧一次,对学问的神圣感也在渐次消淡。
教授的官位一路飙升,各种荣誉头衔纷至沓来,研究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如此等等一大堆。住进了能容纳普通市民好几户人的专家公寓,配上了进口名车。当然业务上还是主编年年当,论著一件无。教授什么都在大踏步前进,包括白发,以及腰的弯度,就是年龄在大踏步后退,十几年间,他只长了几岁,有人以他申报的年龄推算,14岁,他已大学毕业了,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绝无20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教授高歌猛进,当了大单位头,我也小有进步,在他属下的一个小部门效力。那几年,我们虽是事业单位,可我们小部门的收入不错,都是合法的,每年总有上百万元的进项,几十人活得还算滋润。同事私下说,如今大权在握的教授已贪到了无耻的地步,什么都要,什么都敢要,就是不要脸。每逢人在我面前说这话,我一概严词批驳,不留情面。我向来的处世态度是,当面骂我可以,忍得则忍,忍不得动拳头动刀子在所不惜,但别骂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要骂,一边骂去。其实,他们说的许多事,我何尝不知道呢,我不愿也不忍承认罢了。谁让教授是我的业师呢。我与教授的关系也若即若离,不到情非得已,决不到他家去,不得不去他办公室请示工作时,也是千言万语浓缩为三言两语,说完即走。不去他家还有一层原因,我那师娘更是可怕,一个农村妇女,受益于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了城,得到一份工作,于是,夫贵妇荣,水涨船高,她的学问大过了丈夫,官当然比丈夫更大。在教授还未当官时,我有时登门请益学问,师父还在沉吟思索,师娘则快嘴快舌,天上地下,阴阳两界,家长里短,绳头线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番狂侃,满嘴荒诞不经,师父未及开言,先自晕了,我还未聆听师父训诲,早已让师娘绝倒,而师娘渐入佳境,我只好瞅准她找水润口的空隙,抽身夹紧尾巴落荒而逃。教授当官后,下班后便会时常遇到急务,下属得登门请示工作,师娘哪怕正在忙家务,也要急慌慌奔至客厅,抢占最佳说话位置,首长未及开言,首长夫人率先挥动一双女人的手,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替首长作主了。可这主意必须要首长亲口说才合规矩,我便移目于他,他沉吟再三说:那就这样吧。本单位外单位,去过教授家的人,口口相传,一时,师娘大名不让师父。有一次,我将师娘得罪不浅。一件十分头疼的急务,教授听了汇报,也大感头疼,师娘一如既往,四仰八叉歪在沙发,指手画脚,不着调儿,我头疼难挨,把文件朝她面前一拍,厉声说:你要是作得了主,请在上面签字,要是作不了主,请你闭嘴!师娘目瞪口呆,自从教授发迹以来,她可能从未遭此礼遇,一时恨死了我。我再去请示工作,她阴沉着脸不理我,我也不理她。较了大半年劲,她耐不住寂寞,故态复萌,我也只得听她胡诌。
这一年,系统内部给了一项优惠政策,与我所在的小部门有关,执行下来,可收益数十万元。我们是二级部门,不能直接与上级发生关系,需本单位领导在报告上签字盖章,方可上报。我去请教授签字,他拒签,拖到离有效期仅剩一天半时间了,几十万元眼看要泡汤,几十名职工眼巴巴看着班子成员,而我们束手无策。秘书提醒说,咱们想干指头蘸盐?得掏买路钱。我大吃一惊,进入社会多年来,从未给任何人送过哪怕一分钱,而这是本单位内部的例行公事,小部门有效益,要按比例给大单位上交的,犹如父子关系,哪有儿子给老子行贿的道理,再说,这也是违法行为。秘书笑道,不送钱,你要是能让你老师把字签了,狗不吃屎,我吃。
到下晚班时,字还签不下来,部门紧急召开班子会议,决定请教授在本市一家新开的豪华饭店用餐,他欣然赴宴。酒酣,他仍不接签字笔。秘书将我叫出厅外,悄声说,你咋这么不了解你的老师,我问还要怎样,他说得找女人。我不觉大怒,说你这是侮辱人格,他笑说,我还是那话,狗不吃屎,我吃。我嗫嚅半天说,我张不开口。他笑说,你的老师在这方面是一条灵虫,不用明说,你说到哪里哪里坐坐就行了。可我不知道本市哪里哪里有这鬼名堂。他给我说了一个地方。饭毕,我鼓起勇气说,咱们到哪里哪里坐坐。教授当即心花怒放,顿时手舞足蹈。我与秘书陪教授到了哪里哪里,给他开了一间豪华包房,托服务台叫来一位粉脸铺张的小妓女,教授如久早之禾苗,急切切携妓入室。从身后看去,白发粉项,天然成趣。我与秘书枯坐大厅,喝茶抽烟,恼怒万分。秘书见空气沉闷,便调笑说,子见南子,子路不说(yue)。我恼道,子非孔子,子路非子路,南子亦非南子,在人家三人面前,咱连针尖大的脸都不该有的。干脆,子见南子,子路不说(shuo)罢。
不由人不恼,又不得不闭嘴。我想,老师嫖妓,那是人家的私事,咱无权干涉,可至少应该避开学生,更不可让学生请客呀。沿用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古训,说出来的话就难听了。以我向来的办事风格,顺则办,不顺拉倒,从不看人脸色,低声下气。可这件事关乎集体利益,办砸了,谁又会饶了我?反正我是为给大家办事才丢人现眼的。正是怀着这点可怜而又可耻的借口,我才走向这场合的。我的私生活未必一尘不染,但对这种地方却从不正眼一瞧,而初次涉足,却是请老师来一展风流的。我坚持认为,这种事是下等人干的,虽然混迹其中的多的是达官贵人豪客名流,虽然热衷此道的奈保尔先生拿到了诺贝尔奖,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奈保尔获奖的理由在于上半身的卓越创造,而非下半身有什么过人之处。
4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教授得胜荣归,我恼极而乐:别看我的老师文文弱弱的,这方面的功力也许与泰森还有一拼呢。乐过,又万分害怕,我在古书中看到过什么“马上风”之类的天方夜谭,老师年纪大了,万一有个什么不尴不尬,老师又是高干名教授,我给谁能交待得了呢,可又不能去察看,只好赌自己的运气不至于差得离谱。我只盼他好歹能够给我谈笑凯歌还,权当是可怜学生呢。而那一刻,我去意已决,善始善终,办完这件事,我就走人了。
还好,教授出来了,全须全尾,一样不少,而且神采飞扬,与小妓相依相偎,情话绵绵,意犹未尽余勇可贾之态可掬。服务台叫结账,领班说了几个专业术语,大概是按服务项目的等次计费的,我听不懂,账单出来,我大吃一惊,以为挨宰了,她让我去问消费人,还没想出来恰当的话,小妓说,该干的都干了呗,有什么好问的。说完箍住教授的腰,仰脸媚笑道:先生,是不是呀?教授胸脯一挺,豪迈地说:对头!他顺势揽过小妓的粉脖,撮起牙床塌陷的嘴唇,快要接近目标时出了意外,一记教授级的喷嚏铺张打出,一股恶臭四散飞迸,小妓惊叫掩鼻,苗条闪身,白发粉面惊悚相对,又是一种别样风景。
老师嫖妓,学生埋单,足够一个大学生一年生活费的人民币,让我年逾花甲的老师一精射了,学生羞得无地自容。不敢抬头面师,老师犹自老骥伏枥,壮心勃勃。趁教授高兴,秘书不失时机拿出文件,他仍然拒签。这一刻,我彻底傻了,站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教授却没事似的,扬长而去。秘书撮起手指扎了一个数钱架势。看来,不走这条路是不行了,连夜召集班子会,作了详细的会议记录,每人都在上面签了字。第二天一大早,大家齐集办公室,派秘书送钱。教授要奋笔签字的当儿,夫人披头散发冲进客厅,她还有买了衣服皮包等物的上千元发票,要我们一并报销。秘书打电话问怎么办,大家一合计,还能怎么办,头都磕了,还在乎作揖吗,如数报销呗。于是,每人又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
此后,在院子或会议室遇见教授,我不敢抬头看他,我一直有学生嫖妓让老师逮住的羞耻和惶恐,他却若无其事,腆着将军肚,红光满面,谈笑风生,在主席台上,一如既往地引经据典,口辩滔滔,古圣名句,今贤语录,华章俊采,一地锦绣,而这时,我越发不敢抬头看他,最令我担心的是,怕他忍不住打出一记惊世骇俗的喷嚏来。
堕落的生活其实是对自我的一种彻底解放,真正放弃对责任的承担和对道义的迷恋后,首选的往往是对自身生物性的挥霍,而自身生物性的能量如同地下矿藏,再丰厚的储备都有罄尽之时,那时,繁华过后是荒芜,空空荡荡的岁月是自由的,也是令人惊怖的,我的道德学问俱佳的老师沉沦了,周围的很多人都在沉沦,而我也数度徘徊在沉沦的边缘。我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做不了任何于他人有益的事情,我能够护持住那一点可怜的自我,或许便是对群体的终极贡献。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群索居了,而同时,教授也在极不情愿地办理退休手续。在那些个日子里,我还明白了原来不愿承认的一个道理,即堕落的生活是会让人上瘾的。有两样证据可支持我这个看似荒诞的观点,一则是,教授退休后,赖着不搬办公室长达一年之久;一则是,从良的妓女从来都是少数,自身的肉体资源耗尽后,又当鸨娘,身居屠门,趸肉而贾,掂量着油腻腻的进项,更容易忆起花样年华吧。
事实证明,我的离群索居的愿望近乎可笑,这世界哪还有混沌未辟之地呀,连珠穆朗玛峰顶都有人在呼吁环保呢。从一种沉沦的危险中逃出来,又面临另一种沉沦的危险,一年后的一个夏日午后,教授远涉千里找到我,从公文包里抠出几篇学术论文,请我向有关刊物推荐发表,他有些羞涩地说,好多年忙于为社会做贡献,把自己的事荒废了。这时的教授,仅一年光景,光华褪尽,一脸死灰,肚皮倏忽塌陷了。人蔫了,我却觉得他倒像个给我授业时的教授了。遥远的师生之情恍惚奔来眼底,我差点受到感动。客观地说,他的几篇论文也堪称探幽抉微,自非凡品,而我却断然拒绝为他提供帮助。为什么会这样,我至今也说不出个理长理短来。惟一能说出口的理由便是,当我快要被感动时,心下却凛然一惊,突然想起他那个喷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