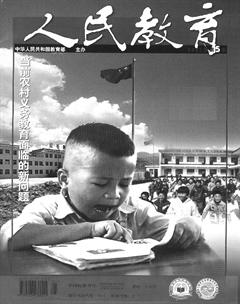心灵写诗
A 曾经是一个少年“诗人”
小时候的我应该算是一个少年“诗人”。
现在常常有朋友认为我搞教育是受了父母的影响,其实,虽然我父亲在教育局工作,母亲在小学教书,但我小时候从没有做过“教师梦”,而整天做的是“文学梦”。
我刚读小学便遇上“文革”,几乎所有文学名著都成了“封资修”,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诗词》成为我惟一的文学启蒙读物。我不但能将所有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倒背如流,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写出一首首“革命诗词”。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欢庆党的“九大”召开,我写了一首《卜算子·庆九大》:“红日出东方,战旗映彩霞。革命小将心向党,万众庆九大。斗私又批修,胸怀亚非拉。待到全球一片红,江山美如画。”这首伺”后来在全校大会上朗读,还受到了工宣队队长的高度评价,说什么“红小兵能写出这样好的词”是“教育革命的成果”。
当时除了背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唱词之外,我还偷偷看了一些“禁书”。《欧阳海之歌》、《红岩》、《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草原烽火》、《苦菜花》、《红旗飘飘》等作品,曾经是那样地激动了我少年的心!这些书不仅点点滴滴地在我的心灵中铸进了忠诚、正直、善良、坚韧等品格,也为我打开了一扇扇文学的窗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后来的写作。
在那个年代,老师出作文题大多都是《不忘阶级苦》、《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之类。今天看来,的确没什么文学性,但我总能写得比同学们更有“文采”,因此我的作文常常被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
我最喜欢写的还是“诗”。记得初二时,老师有一次布置的作文是要我们写诗,我写了一首名为《在广阔的天地里前进》的长“诗”:“在明朗的海空上,矫健的雄鹰展翅翱翔;在广阔的天地里,革命的青年茁壮成长……”老师居然不相信是我写的,发作文本时她把我叫到一边问道:“真是你自己写的吗?”看到我满脸诚实地点点头,她才当着我的面在作文本上写了一个大红的“优”。老师哪里知道,我已经将贺敬之的诗集抄了好几大本了《十年颂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回答今日的世界》、《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等诗篇,我早已烂熟于心了。
读高中时,我又迷上了李瑛的诗、徐刚的诗,并模仿他们的风格也写了不少“诗”。还有那首北大“工农兵学员”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也曾让我热血沸腾。那时正逢“批林批孔”运动,我的“笔杆子”有了“用武之地”,我的一首首“激情澎湃”的“诗”,频频出现在学校大批判专栏上。那时候,“红卫兵上讲台”作为教育革命的一项新生事物方兴未艾,语文老师认为我的“诗”写得“好”,便叫我给同学们讲“如何写革命诗歌”。于是,整整一個星期的语文课,都是我站在讲台上大言不惭地给同学们谈所谓“诗歌创作”,俨然一位“诗人”
我的“写作才能”也深受班主任老师的赏识,当时学校要求班上出的所有文章——广播稿、请战书、挑战书、应战书、决心书、倡议书,等等,她都交给我写。毕业前夕,学校要求各毕业班写“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的申请书,班主任自然又叫我执笔。我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大张,结尾还这样“抒情”道:“我们高76级1班全体红卫兵战士,强烈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用我们的热血染红共产主义绚丽的黎明!让鲜红的太阳照彻全球!”
高中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落户,一年多以后恢复了高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想都没想就填上了“中文系”。我自认为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学基础”,理应进中文系“深造”。虽然填志愿时,我在冲文系”前面填的是“四川师范大学”,但这仅仅是为了增加录取的保险系数,以便早日跳出“农门”。于是,1978年春天,我带着文学梦走进了四川师范大学.
坐在大学教室里,我才感到自己离文学其实还远得很:李白的诗歌,朱自清的散文,巴尔扎克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真正的文学经典,我居然闻所未闻!于是,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我间或也写一些诗歌或小说,并且满天投稿。我曾经把我的“作品”寄给我很仰慕的作家萧殷同志“斧正”,还曾写信向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叶子铭老师请教“文学创作”。让我颇感失望的是,除了收到萧殷老师和叶子铭老师热情洋溢的鼓励信之外,所有投稿无不石沉大海。
大学实习,我来到一所县城中学教高一语文。也许是我性格比较活拨而且和学生的年龄也相近吧,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实习结束时,学生们流着眼泪拼命追赶着我返校的汽车……回到学校,我还久久沉浸在对实习生活的回忆和感动之中,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首以实习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叙事诗《校园钟声》。虽然这首诗仍然没能发表,但却是我第一次带着真情用笔写“教育”。或许可以说,《校园钟声》是我的“文学梦”与教育的美好“初恋”吧。
正是怀着这种对教育“初恋”般美好的憧憬,1982年春天,我告别了大学,走上了四川乐山一中的讲台。
B 开始把教育当诗来写
从教之初,我并不安心工作。我老想着哪位“文坛伯乐”能发现我这颗“文学新星”,然后调我到更适合我的岗位(比如什么作协之类的单位)去,我总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暂时”的。
但是,天真无邪的初一孩子们却把我当做他们“永远”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来爱戴。记得上课不到一个月,我嗓音便嘶哑了,有学生悄悄地将药塞进我的宿舍门。我拿着药在班上问是哪个同学送的?孩子们调皮地笑着,却没一个承认。金色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教室,洒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太阳的光泽。这温馨时刻的一双双眼睛触发了我的灵感。当天,我写下一首短诗《眼睛》。我在诗中真诚地赞美孩子纯真的眼睛,进而赞美孩子们纯洁的童心。这首小诗后来在报上发表,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的消息传到班上,教室里一片哭声。孩子们为了让李老师能随时听到他们的声音,放学后留在教室里,面对录音机唱了一首又一首的歌,然后将录音磁带送到我的病房!当然,孩子们对我的爱更多的时候是“润物细无声”的:或是早晨走进教室,一声亲切的问候:或是我外出开会离开学校时,那眷恋的眼神;或者仅仅是夹在作业本里的纸条:“希望李老师晚上早点睡!”我越来越感到,教育给我带来的心灵的愉悦决不亚于文学。
我开始把教育当成一首诗来写。为了让我的教育充满理想主义气息,也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班集体,我和学生为我们的班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未来班”。我们设计了班徽,绘制了班旗,还创作了班歌。班歌的歌词是我和学生共同写成的一首诗《唱着歌儿向未来》,然后寄到北京,请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同志谱上曲子。后来“未来班”作为一个优秀班集体被全国多家报刊报道,也成为我教育诗篇中的第一行美丽的文字。
我决定让文学成为我和孩子们共同的爱好。我不但把《青春万岁》、《爱的教育》、《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搬进了语文课堂,而且经常在放学后带着孩子们到郊外去搞“文学写生”:在学校外边的岷江之滨,在乐山大佛对面的绿岛上,在朴素的农舍前或静静的小河边,我们一起用心感受大自然的美,然后当场用文字将这种美描摹出来。我还多次在寒暑假,与学生一起到大自然去长途旅游: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下面,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生穿着铁钉鞋,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嵋之巅;我曾與学生在风雨中经过八个小时的攀登,饥寒交迫却兴趣盎然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和学生的这种风雨同舟、相依为命之情让我感到无限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我赐予学生的,也不是学生奉献给我的,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平等分享的。
每次旅行归来,我和学生们都会写出长长的游记互相交流。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作文时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过程展示给学生看,并以我体验到的写作乐趣感染学生。但很多时候,有些学生的作文比我写得还好,因为少年的眸子往往比成人的目光更明澈,尚未蒙尘的童心往往对自然对生活有着比教师更独特更细腻也更真实的感受。每当作文讲评课上我和学生交流作文的时候,教室里总是洋溢着节日般热闹的气氛。学生很喜欢与我比赛作文,如果谁的文章被公认超过了“李老师”写的,孩子们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而我也会比他们更兴奋。这时候,很难说是谁感染谁——对美的感受和表达,成了我们共同的乐趣。
1986年暑假,我和妻子到云南、海南、贵州、桂林等地旅游。在旅途的每一天,我都以书信的形式写一篇游记,然后将这篇文字寄给我的一位学生。那个暑假,我在外旅游了54多天,就写了50多篇游记,刚好班上50多个学生每人一篇!我不是想以此“教育”学生,真的,我只是在面对大理的白云、海南的碧波、桂林的奇峰、贵州的飞瀑,深深陶醉其中的同时,忍不住想让我的学生也和我一起分享这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美。
我喜欢写诗,也指导孩子们学写诗:“其实,一个新颖的比喻或拟人,一个奇特的想像,写下来就是诗嘛!”于是,属于他们年龄的诗句便流出了他们的心灵:“星空像一盘棋,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究竟谁输谁赢,永远是个谜”;“岷江滔滔东流,好像长长的五线谱;江面点点风帆,便是那美妙的音符”;“月亮哭了,泪水化作了星星”;“雨,是出走的孩子,它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诉说着天上的故事”……学生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头脑中竟有那么多诗的萌芽。
在我的倡议下,学生们组织了一个文学社,他们自写自编自印了文学社社刊《凌云》。我在创刊号《序言》中写道:“……我终于没成为‘诗人,而只是个教书的。然而,当我赞叹于学生交上来的一篇篇稚嫩而清新的诗文时,当我兴奋于学生自编‘作文选集、自办油印刊物时,当我欣慰于学生的习作在报刊上发表时……我感到了我的‘文学梦正由我的学生一点一点地变为现实。”渐渐地,他们的诗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青年报》、《读者》、《中学生》、《现代中学生》、《中学生读写》、《少年文史报》等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每当这时,我都有一种丰收的喜悦,好像是我发表了作品似的。
这份喜悦使我对教育开始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和情感,想当“诗人”的欲望渐渐淡化,因为我发现,教育本身就是一首纯净的诗。
C 用笔记录心灵的诗篇
当然,仅有兴趣和情感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我感到了自己教育理论的匮乏。于是,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赞可夫、布鲁姆、布鲁纳、巴班斯基、于漪、钱梦龙、魏书生……都纷纷走进了我的生活。其中最让我着迷的是苏霍姆林斯基。
我特别为这位富有人情味的教育家30多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教育手记的精神所感动。正是几十年的教育手记,使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被誉为“活的教育学”、“教育的百科全书”。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感情真挚而充沛,思想朴素而深刻,语言平易而精彩,且不乏文学的魅力,通篇没有令人敬畏的`12论框架”和故弄玄虚的深奥术语,只是心灵泉水的自然流淌。在读过一些即使硬着头皮也难读懂的教育“理论”著作后,读到这样朴素亲切而富有感染力的教育名著,令我感慨不已!这样的文字,其实我也可以写呀!当然,我那时绝对没想过将来也要写什么“著作”,但用文字记录下自己育春的足迹,总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于是,我也试着以日记的形式写我的教育手记了。
第一篇手记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因开玩笑而伤了班上一位残疾学生的自尊心,于是当天晚上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到了他的家里,向他赔礼道歉。现在看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当时却一定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不然,我不会写得那么详细:我开玩笑时的得意忘形,孩子委屈的表情,我真诚的内疚,我晚上家访迷路时的焦急,我在学生家里和他们的对话,以及告别学生后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满天星斗时的轻松与喜悦……我当年的每一篇手记大多是这样一些真实而琐碎的故事:那堂自己感觉很好的语文课《小麻雀》,我和学生在春天原野上的一次次“疯狂”,我与一位陷入“早恋”而深感苦恼的学生的谈心……在写这样的手记时,我没有一点写文章”的感觉,只觉得是在用笔挽住每一个平凡而纯真的日子,是在记录我生命的流程。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教育手记,记载的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堂语文课。
那是1985年5月的一天,上课铃声一响,当我走进教室时——
“起立!”随着值日生清脆的口令,孩子们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然后是比平时更整齐更响亮的童音;“祝—李—老—师—生—日—快—乐!”
在我目瞪口呆之际,小小的讲台已堆满了鲜花、生日蛋糕、影集、笔记本、手绢、书签等各种礼物。台下,57双眼睛正闪着兴奋而得意的光芒望着我。同时,孩子们调皮地用富有节奏的掌声为我祝贺!
当时,我心中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惭愧。因为就在课前几分钟,我还在办公室为奖金“分配不公”而与校长论理。
我走下讲台,缓缓说道:“同学们,我受之有愧啊!……李老师并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高尚。但是,今天同学们又一次深深地教育了我:教师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报酬,决不仅仅是金钱,而更多的是丰厚得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这,才是今天同学们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但从此以后,我将把今天这个日子当做我的又一个生日。谢谢同学们,谢谢!”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天的确不是我的生日,但学生为何错把那天当做我的生日,至今还是个谜。16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起那堂课时,我耳边好像还回响着学生们那热烈、真诚而又带着几分顽皮的掌声和笑声,因而禁不住心潮澎湃!
就在这篇题为《生日》的教育手记发表后一个星期,我接到北京《班主任》杂志编辑的来信,说我一个月前寄给他的《教育漫笔》将在刊物上连载!
他说的《教育漫笔》,是我在1985年除夕的爆竹声中完成的。寒假第一天,我带着孩子们来到大渡河畔。我们在沙滩上斗鸡、摔跤、用薄薄的鹅卵石比赛“扔水漂”……除夕那天我回到了母亲家,心里还充盈着与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欢乐。想到3年来教育赋予我的喜悦,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使我赶紧拿出笔,任激情在纸上燃烧!伴着窗外响起的阵阵迎接牛年的爆竹声,我不停地写呀写,直到傍晚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就要开始的时候,5000多字的《教育漫笔》终于划上最后一个句号。那时,我不知道这篇有着浓郁的苏霍姆林斯基风格的教育手记算不算“论文”,更不敢相信后来在我偷偷地把它投寄到北京刚刚创刊的《班主任》杂志后,居然能被连载!
接着,我又将一篇总结“未来班”教改成果的文章寄给《班主任》杂志。编辑在发表这篇9000字的长文时,特意加了一段编者按:“这是一份很好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是一位年轻的中学班主任,他从大学毕业就开始朱来班的实验研究,他的探索是成功的。细读这份报告,每一位班主任都会受到启示。”
真诚感谢苏霍姆林斯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的教育手记从四川乐山一中,一直写到成都玉林中学,写到成都石室中学……
D 与青春同行诗意盎然
教育者的写作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写作,实践是它的源泉,阅读是它的基础,思考是它的灵魂。特别是“思考”,对于教师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一位教育者应该同时又是一位思考者。而教师的写作,便是教育思考很重要的途径.
1997年的暑假,我从成都玉林中学调到成都石室中学,在搬家的过程中,我無意中又看到了那一捆尘封的教育手记。翻开我19年来所写的一本本教育手记,我禁不住被自己感动了:那一页页发黄的文字,化作一张张老照片在我眼前变得清晰起来,分别多年的学生们正跑着跳着向我拥来,他们纯真的笑声萦绕在我的耳畔……正是在那怦然心动的一刻,我做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我要把我和学生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分享这教育的幸福!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打开电脑,拉出键盘,敲出了第一行字:《爱心与教育》。我完全没有写书的感觉,只觉得十几年来教育在我心中积蓄的思想感情如潮水一般在键盘上恣肆奔涌,敲键盘的手指禁不住也微微颤抖。
整整三个月,我的业余时间都是这样在阳台的电脑前度过的。也许在旁人看来,如此不停地敲击键盘是何等地乏味而枯燥,但我却感到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我仿佛不是在敲电脑,而是在弹钢琴,是在演奏来自教育来自学生心灵的最美的乐章。眼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页页很纯洁很动情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又很自然地幻化为一幅幅很美丽很鲜活的画面,那是宁玮善良而坚韧的面容,杨嵩纯真而调皮的微笑,岷江之滨的熊熊篝火,滇池湖面的灿烂阳光……我的整个身心再一次沉浸在和学生一起度过的被青春染绿的日子里!
《爱心与教育》出版后引起的强烈反响,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收到近千封读者的来信和许多读者含泪打来的电话。1999年,《爱心与教育》同时获得中共中央宜传部“五个一工程”大奖、冰心图书大奖和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科研成果一等奖。
这以后,教育与文学共进,思想与激情同飞。我又陆续出版了《走进心灵——民主教育手记》、《教育是心灵的艺术——李镇西教育论文选》、《花开的声音——我班的故事》、帆中芦苇在思索——李镇西随笔选》等著作。手捧散发着油墨芬芳的《李镇西教育文从》,我有一种丰收的喜悦:教育和文学给了我双重的回报——文学为我的教育事业插上了翅膀,同时,教育正在圆我的“文学梦”。
20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我暂时告别了成都石室中学,来到美丽的苏州大学,师从朱永新教授攻读教育哲学博士。在明亮的图书馆里,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聆听卢梭的诉说,聆听裴斯泰洛齐的教诲;在高大的银杏树下,我披着金色的落叶与马克思对话,与杜威交谈……大师们思想的潮水越过遥远的时空一泻千里滚滚而来,拍打着我的心岸。我常常禁不住激情澎湃,于是,不再年轻的心湖又重新扬起了青春的风帆。
因为情寄教育,我的人生便永远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