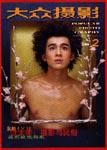与“摄鬼”同行
钟 旭
我不懂摄影,总觉得那是件很奇妙的事情,但不幸却结交了一党痴迷摄影的朋友,我称他们为一群“摄鬼”。每到周末,抑或节假日,我所有的空闲时间全交由他们给安排,常常是人在梦中,电话就迷迷糊糊地响了:“嗨,哥儿们,赶快起床,收拾行装,这回可得去三五天!”这下完了,好不容易赶上个睡懒觉的机会,又让他们给搅黄了,眼睛未睁开便开始穿衣服,这常常让我暗自生出许多“交友不慎”的感慨!

每次出行,按他们的说法那叫“创作”。也没我什么事,无非就是替他们背背三脚架、举举闪光灯,再不就是维持秩序,将那些扛着摄像机的不相干的人撵开——哪怕他是中央电视台的。更多的时侯,我都是静静地坐在旁边,冷眼看着他们为那些本不值得激动的场景疯狂地“谋杀菲林”。拍摄之余,常听他们神侃,指点摄影江山,激扬创意文字,谈光与影、明与暗,论性与情、灵与肉,从陈长芬的长城到赵铁林的打工妹,不一而足。侃到酣处,眉飞色舞,面红耳赤,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痴迷状却也让人生出几许同情来。常有这样的情景:几个摄鬼围坐一团,你一言我一语,你一个馊点子,我一个坏主意,凑成一个创意,相视抚掌大笑,自以为天下无二,世上无双。正摇头晃脑自鸣得意孤芳自赏之际,被我一瓢冷水浇个透湿,便又一齐哀叹:“中国摄影从此倒退十年!”
因为常在一起创作,便生出许多笑话来。一次高君约大家去花江拍摄红叶。说是漫山遍野,十里红叶,其景如火焰山般壮观,落霞与孤雁齐飞,红叶共长天一色云云。待到车行百里,大伙兴致勃勃跋山涉水赶到花江,不禁哑然失笑,相顾无言——倒也是十里红叶,不过是每爬十里山路才见一株可怜的、孤独的红叶!另有一次,卢君获得绝密情报,说雷山县永乐镇附近的苗寨将举办数十年一遇的牯藏节,并神秘地对大家说起苗族牯藏节的由来和历史,绘声绘色地描绘出苗家人杀牛祭祖的古朴仪式和一次宰杀十几头大水牯牛的惨烈情景……同行诸人都被卢君的话所打动,耳边似已响起苗家杀牛祭祖时“咚咚”的木鼓声,眼前仿佛看见血流成河的悲壮场面,大家都被一种亢奋的情绪所左右,满怀创作的冲动,全副武装从贵阳出发,历经几百公里的长途奔袭,当晚赶到永乐,又连夜弃车而行,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冒雨直奔地处云遮雾罩、崇山峻岭之中的苗寨。待到目的地,天已微明。尽管我们紧赶慢赶,但仍然来迟了,祭祖仪式已经结束!然而更加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是当地苗族牯藏节是杀猪祭祖而非杀牛祭祖,望着地上横七竖八、圆鼓鼓、白花花的一片猪肚皮,大家都啼笑皆非。卢君更是一脸的无辜,仿佛深怕自己素来诚实的品格被人怀疑一样,百思不解地喃喃道:“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这事已过去许久了,但想起来仍让人忍俊不禁。卢君当时所拍的照片至今仍深藏柜中,羞于示人,因为他担心会有人猜想他是在贵阳市郊外的生猪屠宰场“创作”的。

不过,这党“摄鬼”为他们所称的摄影艺术所付出的辛劳以及甘愿承受苦累的精神却使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们背着几十公斤重的器材跋山涉水,他们天不亮顶着寒风期待日出,他们住5元钱一夜的小店,甚至与农民同吃同住,夜间——任老鼠从鼻梁上掠过,任臭虫蚊子在身上咬出一身疙瘩(有一女摄友竟在身上数出193个疙瘩!这足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一切,特别使我感动,也是我毫无怨言地愿意为他们背三脚架、举闪光灯的原因。我分享他们的喜悦,宽慰他们的懊恼,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变得充实起来,至少现在已改掉了睡懒觉的习惯。
卢君曾经很认真很诚恳地对我说:“其实你也应该学学摄影,这并不困难。关键是要用心去体会,用情去构思,把你对大千世界的瞬间感悟记录下来。”我把嘴一撇:“你可别,这可是苦差事,还让我为你们背三脚架、举闪光灯罢!”话虽然这么说,没准下回出门的时候,我还真会偷偷在行李包里塞进一个理光GR1。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