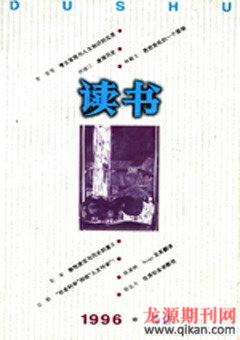调侃大师解构经典
刘亚丁
正当国中的学人为“重构文学史”忙得不亦乐乎时,我们的北方邻居俄国人却忙着解构他们的文学史。在用各种离奇古怪的方法重读名著的热浪中,一女流之辈独出心裁,从浩如烟海的报刊书籍中,搜罗出戏拟挖苦漫画主流作家的小品短诗编定成书,题为《哈哈镜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
这本书一面是树大招风,文坛上一出名就变成了靶子,难以招架四面八方射来的枪子。一面是默默无闻,有人借写骂名人而挤进名人圈:有人不畏权威,仗义执言。
阿赫玛托娃名气不小,有“俄罗斯的萨福”之美誉。她有一首《诀别之歌》写与恋人诀别的悲情,缠绵悱恻,煞是动人。其中有“昏昏然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竟把左手的手套戴到了右手上”等名句为人传诵。她的另一首诗,题为《蓝眼睛的国王》。这些就成了戏拟的靶子。有位俄罗斯男人,扛着西班牙骑士封号般的笔名:堂·阿米纳多,从刺斜里杀将出来,立马高叫:“阿氏妇人,休将好名声带走!”随即高声吟道:“啊!/我通晓爱的真谛,/将相思之苦饱尝,/——我将左手的手套/戴在了右手上!/昨儿个我进了包间,/爱上了个蓝眼睛的国王。/我原以为,捡文雅的话说,/那心上人儿该抱定爱情至上,/可到而今敌不过男人的暴力/我痛苦难当!……/我将大披肩套上纤纤素手,/却把紧身内裤穿在了肩上。”骂人用语之恶毒,与后来在大会上骂阿氏的日丹诺夫不相上下。足见文人相轻,中外皆然。这位“西班牙骑士”什帕良斯基走的是跟骑士完全相反的路子,骑士靠傍贵妇得势,他靠骂女诗人出名。
其实,这本书并不是借文学公报私仇个案的卷宗汇集,其中有很多严肃的东西值得思考。庸俗社会学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苏联是颇为主流的。可就有些小人物不信邪,放胆唱出些不和谐音。卢那察尔斯基挟教育人民委员之尊,成了苏联当前及古典文学的首席批评家。有个姓布霍夫(笔名Л·阿尔卡季斯基)的小品文作者,发表了一出题为《卢那察尔斯基风格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短剧,用类似于归谬法的手法,让古典名著按卢氏的要求脱下“资产阶级的衣装”,而进入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令人读后领悟到庸俗社会苛责前人的荒唐可笑。作者的预见力不但令俄国人叹服,在我们的样板戏中也得到了印证。
将古人现代化和神化,也是某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流弊。有感于此,德·哈尔穆斯写了一组“普希金逸闻”。其中一则是:“一九二九年夏天普希金是在农村度过的。他早早起床,喝完一罐牛奶后,就跑到河里去游泳,游完泳后他就躺在草地上睡觉,一直睡到吃午饭。午饭后他又到吊床上睡觉。碰到一个满身臭气的农夫时,普希金冲他点点头,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可满身臭气的农夫摘下自己的帽子说:‘没关系。”这则显然是虚构的逸闻,意在消解当时学术界制造的两种神话,其一是,普希金总是冥思苦吟,挥毫不已,以致晨昏颠倒,废寝忘食。其二是,普希金作为人民诗人,无比热爱受苦受难的人民。哈氏在一则则充满机智的逸闻中,把普希金还原为一个原原本本的诗人。
对话、争论、谩骂,这是《哈哈镜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提供的新景观。客观乎,真实乎,这不是笔者所能断定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从来就不是某位首席的独奏。
(Русск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