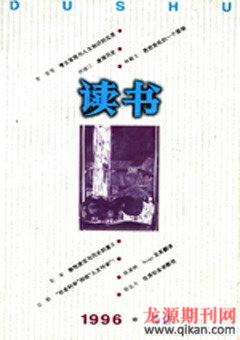唐突历史
刘浦江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吗?
有人说,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意思是,所谓历史,无非就是人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对过往的一种阐释。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时几乎不可能毫无介入,政治、国家、民族利益,乃至个人感情,都是使历史研究缺乏科学性的重要因素;等而下之,就连经济利益、地方利益等等,都可以驱动历史学家改编历史。
对历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政治。一部中国史,是是非非,在二十世纪历史学家的笔下实在是变化无常。举武则天为例。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武则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说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六十年代,情势为之一变,郭沫若写出历史剧《武则天》,又连续发表文章,对武则天充分肯定,断言“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并引用武则天自诩“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的话来证明她的德政。郭沫若的有些说法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比如他说武则天“是维护均田制的,……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则天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没了”。为了洗刷武则天政治手段残酷的恶名,郭沫若声称章怀太子李贤不是武则天害死的,认为此事不见于两《唐书》的记载,《资治通鉴》的说法没有根据;尽管后来袁震撰文指出新旧《唐书》的《酷史传》中都记载有武则天害死李贤的事,郭沫若却依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袁震说,如果李贤不是武则天害死的话,那他的棺材为何放在巴州达二十一年之久?郭沫若解释说:“天下大事很多,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的棺材就在巴州放久了一点,算不得什么。”在历史剧《武则天》中,郭沫若把谋害李贤的罪名栽到了宰相裴炎的头上,——当然,这是文学创作,他想怎么写都可以。从郭沫若以后,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七十年代前期,对武则天的评价上升到顶点。粉碎四人帮以后,是非又被颠倒了过来,七十年代末的代表性观点是,武则天是唐初士族地主阶级中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她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都呈现了全面的倒退,这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逆转。有的历史学家还对武则天的政治手段加以抨击,说她“一贯用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等等。八十年代以后,历史学家开始用比较心平气和的口吻来谈论武则天,对她基本上是加以肯定,但用词显得很有分寸,与郭沫若的一味颂扬又自有不同。
武则天大概万万没有想到,她身后的是非竟会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这么搬弄来搬弄去。回味这几十年的褒贬,总觉得在武则天的身后有一个影子。夸张一点说,从对武则天的评价中,可以描摹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
历史人物无定评,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说,关于岳飞镇压杨幺起义的问题。五六十年代,农民战争是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农民革命享有极高的评价,于是乎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镇压杨幺起义是岳飞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大家对此齐声谴责。孰料文革以后,农民战争受到冷落,对农民起义的评价降低了调子,与此同时,岳飞的声望却蒸蒸日上,于是其间的是非就被颠倒了个儿。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人试图证明杨幺政权的性质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与伪齐相勾结的反动地方军阀集团,是破坏南宋抗金斗争的割据势力。自此以后;便不断有人想要为岳飞开脱此事。而最为精彩的,大概要算是一九九一年在杭州举行的纪念岳飞八百八十八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出现的某些高论。有人解释说,岳飞之所以要去镇压杨幺,是为了抗金事业的大局,不得已执行朝廷的命令,为的是解除后顾之忧,进军中原,收复失地。更有一位学者指出,岳飞为了抗金大局,对洞庭湖地区的起义军进行镇压,而起义军中的周伦、杨钦等人则深明民族大义,主动请求招安,以便一致抗击外敌,这种行为显示了农民起义军领袖们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因此,所谓岳飞镇压杨幺起义,实质上是南宋抗金部队与民间爱国武装在共同保卫民族利益前提下的联合;岳飞不仅不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是历史的功臣;周伦、杨钦等不仅不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而是真正的爱国志士;至于杨幺不愿接受招安,固然与他个人思想的偏激和狭隘有关,但钟相的被害使他产生强烈的阶级仇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杨幺也不要进行过多的指责。
读了这些文章,不禁哑然失笑。历史学家有权力这样随意解释历史么?岳飞为什么要镇压杨幺起义?就因为他是赵宋王朝的臣子,他是朝廷的武将,他领着国家的俸禄,镇压起义乃是他的天职,岳母刺在他背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就包含着这一层意思。至于说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是非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再说部分起义军将领为何接受招安?毋庸解释,这显然是从他们的个人利益来考虑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把他们受招安的动机描绘得那么崇高,那么冠冕堂皇,但凡稍有点头脑的人有谁会相信呢?
历史研究一涉及到国家和民族问题,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微妙和非常的棘手。自秦朝以来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大一统的王朝史,统一——分裂——再统一,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要轮廓,每一次统一国家的分裂都是下一次统一的开始,每一位分裂时期的君主都以完成统一大业为己任,“分久必合”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大一统的观念深深浸润于所有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于是历史学家就有了某些忌讳。忌讳之一是“分裂”。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论著中尽量避免用“分裂”这个词,而改用“分立”来替代。这里面的讲究在于,“分立”可以理解为一个统一国家内暂时存在着若干个割据政权,而“分裂”则似乎是指各自完全独立的政权。忌讳之二是“民族”。资深的历史学家从不滥用“民族”这个词,他们恪守这样一个原则:凡是属于今天五十六个民族之内的,如蒙古、满族,涉及到他们的历史时可以称之为“民族”;若是不在这五十六个民族之内,如契丹、女真这样已经消亡了的民族,在谈到他们的历史时决不称之为“民族”,而只称为“族”。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从来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私下揣摩,大概是因为在各民族之上有一个中华民族的缘故,——附带说一句,“中华民族”这个词,其实说到底也是大一统观念的产物。
以上说的,还只是用词的忌讳,尚无大碍。不过从这些忌讳中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一旦涉及国家和民族问题,历史的价值评判大概是很难做到公允的,比如“民族英雄”。金史研究者认为金兀术(完颜宗弼)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而宋史研究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说兀术的一生积极参予了对宋朝的侵略战争,他只能代表本民族统治集团的狭隘私利,不能代表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不能称为民族英雄。显然,后者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评判历史。兀术是不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我们不妨站在女真人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兀术为金朝开疆拓土,使女真人得以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庞大帝国,他怎么不能代表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这难以作为评判民族英雄的标准。凡是为本民族开拓疆土的人物,对对方来说是侵略,对本民族来说则是英雄,历史的逻辑似乎就是如此。
历史上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不是一个概念,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如果拿今天的中国去摹刻历史,就不免要闹出一些笑话。石敬瑭为了引契丹为援,以夺取帝位,不惜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并甘愿认辽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此事的是非褒贬,历代史家早有定评。八十年代初,有人撰文为石敬瑭翻案,认为契丹也是今天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只能说是内部的归属问题,指责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是混淆了国内民族矛盾和国外民族矛盾的界限。这位学者还振振有词地说,正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才导致了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试问,如果认为不能假长城以南一寸土地于少数民族,怎么会促进民族融合,造成今天多民族的统一中国呢?”
这位学者忘了,他研究的是历史。在石敬瑭的时代,契丹和后唐还不是一个国家,割让燕云十六州只能视为卖国行径。按照这位历史学家的逻辑,倘若千年后中国和当年的侵略者变成了一个国家,是不是就可以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场侵略战争称之为内部归属问题呢?汪精卫们的汉奸之名是不是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呢?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是历史学家曲解历史的一种经常性冲动。南宋宁宗时由宰相韩
辛弃疾等人对开禧北伐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嘉泰四年,辛弃疾从浙东安抚使任上入见宋宁宗,言金国必亡,建议付托元老大臣对金备战,据《庆元党禁》记载说,韩
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史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历史学与政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中的种种非历史倾向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貌。甲午海战中方伯谦被杀的“冤案”问题,就很耐人寻味。据说方伯谦被清政府处斩之后,方妻就曾经进京告过御状。三十年代,方家后人又为他大鸣不平。但这在历史学界并没有成为问题,因为方伯谦的临阵脱逃是一段早有定论的历史。尽管八十年代以后有少数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也是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最近十来年,方伯谦的后人多方奔走,为方伯谦鸣冤伸屈,经过不懈努力,一九九一年在福州举行了由福建省八团体联合发起的“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后来以《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为名汇集出版(知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此书被称为“学术界目前关于方伯谦问题研究的大全”。这部“大全”收录近四十篇论文,共计五十万字,但却只有一篇千把字的短文是主张代表史学界多数人意见的传统观点的,其它则全是连篇累牍地为方伯谦鸣冤诉屈的翻案文章。从某种角度来说,它确实称得上是一部“大全”,因为这部论文集里收的并不只是此次讨论会的论文,它还把历来为方伯谦翻案的文章也都搜罗进去了,但观点相反的文章却一概不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福建省社科院主办的《福建论坛》,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上搞了一个名为“方伯谦研究”的专栏,所发表的九篇文章全是为方伯谦鸣冤的,连一篇装装门面的商榷文章都没有。
方伯谦果真是被冤杀的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临阵脱逃。为他翻案的人说他不是“逃跑”,而是“退却”。甚至有这样一种高论,以为方伯谦在险境中主动退却,从而为北洋水师保存了一艘军舰,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这种论调之荒唐,就连有些为方氏鸣冤的人都感觉不妥。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济远舰是什么时候退出战场的?有人试图用中日两国的时差来证明济远舰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才撤离战场的,但两国之间的时差只有一小时,而济远舰却早于舰队四个小时回到旅顺,况且同样是出自中方的记录,怎么会有时差的问题?替方伯谦翻案的人又说首先逃离战场的是“扬威”而不是“济远”,但有学者指出,扬威舰驶离战区是为了救火,和“济远”径直逃回旅顺性质不同。
有意思的是,早先方氏后人为他鸣冤时,以为其冤枉主要在于:有些人比方伯谦的过失更大,不该把他当成替罪羊。而这些年的翻案者已经不是这种说法了,在他们看来,方伯谦根本就无罪,不是罪大罪小、该不该杀的问题。有人质问说,如果方伯谦真的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不在战斗刚一打响时就逃跑,而要打到一半时才退却?
关于这场翻案运动,有一些背景需要说明。方伯谦和济远舰上的大部分官兵都是福州人,当时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西方教官有一种看法,认为“武官之胆怯,无过福州人,断不敢与日战,……至福州人之外,类多一身是胆。……济远一舰则全系福州人,故临敌先逃。”——当然,这种评论肯定是不公允的,如刘步蟾、林泰曾等勇敢善战的福州籍将官,当时也不在少数。直到今天,为方氏鸣冤的人们仍在为重写这段历史而继续努力。在我看来,这场翻案运动是一群历史学家在为捍卫一个家族和一座城市的名誉而战。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名人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对历史名人的争夺,就成了当代历史学的一项特色内容。为方氏鸣冤的这场翻案运动似乎就带上了不少地方色彩。当然,最受人看重的首先是名人的籍贯,譬如山东有两个县都自称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家乡,并都为此展开了宣传攻势,历史学家厕身其间,各执一词,令人莫衷一是。籍贯之外,历史名人的死地也为人青睐,于是就有了李自成的归宿之争。
据清朝官修的《明史》记载,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窜死湖北通城九宫山。一九五五年,湖北通山县的一位小学教师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供了他的一些调查材料,认为李自成不是死于通城县九宫山,而是死于通山县九宫山,后来经过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使这种说法得到确认。郭沫若也表示,他为通城县的闯王陵所作的题词,以及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县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以注销并改正”。于是在通山县又新建了一座闯王陵和一个李自成展览馆。
但是在湖南澧州一带民间,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传说,说是李自成在大顺军失败后遁迹石门县夹山寺为僧,并终老于此。乾隆年间任澧州知州的何
湖北方面当然不甘沉默。一九八五年,湖北省邀请全国七十多位明清史专家聚会通山县,举行李自成归宿问题的专题讨论会,据说与会者多数对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持确信无疑的态度。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而湖南石门县对此却不予理会,依然在石门夹山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闯王陵,比通山的闯王陵要气派得多。近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去石门采访,看到当地中学的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李自成遁迹石门的历史,石门的地方官员并不讳言他们利用历史名人来振兴地方经济的意图。
李自成的归宿,本不值得历史学家们投入这么大的精力,五十年代的讨论固然与当时农民战争史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总还算是学术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战就几乎没有什么学术的味道了。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尊重历史,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家的职业信条。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于京西大白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