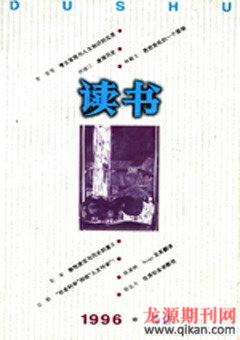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
陈星灿
当某人自称或被别人尊称为考古学家的时候,那不过是沿用了一个习惯的说法,其实是颇有点不准确的。因为人类的古代文化是如此的灿烂辉煌,多彩多姿,任何一个伟大的考古学家,穷其一生的精力,也只能为重建古代历史的大厦添几块砖瓦而已。因此,严格说来,他只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方面的考古学家。
考古学在十九世纪初年诞生以来,不仅为人类认识自己和自己生活的舞台作出了也许是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而且本身也变得日益壮大。即以我国为例,考古学的分支就有多种。从横的方面说来,有农业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水下考古学、冶金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甚至还有天文考古学和根据文化特征历史形成的地区考古学。考古学的许多分支从单纯的利用田野考古的材料研究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到有意识有目的的成为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是人类认识历史的视野被拓宽的结果,然而事实上却又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和进步。从纵的方面说来,习惯上我们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商周考古学、汉唐考古学等等,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本土性和多元一体格局,造就了我国各时代考古学既有区别又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特殊面貌。
如果把镜头对准整个地球,除了南极洲古代的人类不曾涉足外,其他的地区都留下了人类文化的烙印。研究世界古代文化的考古学就更是门类庞杂,变化多端,差不多各个地区的考古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但是,世界考古学的研究基本可以包括在以下的分类中,即:史前考古学、原史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史前考古学(prehistoricarchaeology),顾名思义,是指“历史以前的考古学”。这里的“历史”是指狭义的历史,即能够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那一部分人类历史。简言之,史前考古学就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考古学。传统上我国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新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即被称为史前考古学。原史考古学(protohistoric archaeology),直译应为“最初历史阶段的考古学”。如果历史是有文字的历史,那么原史当也是研究文字时代的历史。对于这个名词,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英国著名考古史家格林·丹尼尔(G.Daniel)认为,所谓原史,即文字已经产生,但是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实物资料与文字同等重要,或者比文字还重要。另一位考古学家霍克思(C.Hawks)认为,那些产生了文字但把文字用作非常领域(如宗教)的社会,或者把文字写在某种材料上而这种材料又没有保存下来的社会,或者一些没有文字但是历史却被周围有文字的民族记录并保存下来的社会,这些社会的历史应该称为原史或“类史”(parahistory)。研究这个时代即文字产生初期或可资利用的文献不完备时期的考古学即为原史考古学。如果勉强比照的话,也许商周时期的考古学算是原史考古学。不过我国一直没有采用这个概念。历史考古学的歧义很少,是指研究有文字时代历史的考古学。我国商周以降的考古学即是。实际上考古学的分类方法要复杂得多也细致得多。学习考古学的人要想成为全知全能的通才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也非常艰难。我们学习考古的人常常被问及各种各样的问题,提问的人既有研究历史方面的专家,也有普通的公众。他们往往怀着很大的希望热切地想从考古人的嘴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然而他们几乎很少得到满意的回答——如果考古人不是略去他们讨论的细节和众多的争论甚至驰骋自己的想象的话。这还往往是在考古学者自己熟悉的领域。我的六岁的儿子问我,人是怎样从猿变来的,我含糊地告诉他那是进化的结果。这当然不能让他听明白,可天知道,要回答这样一个平常的问题,即使对一个拿了古人类学和解剖学两个博士学位的专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这样说并非为考古学家开脱,实在是人类的古代文化太复杂、太瑰丽也太富于变化了。实际上,面对着人类祖先二三百多万年的过去,我们已知的东西要远远少于未知的东西,如果说成是沧海一粟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考古学是根据物质遗存研究人类的古代历史。这一特点一方面决定了考古学是一门非常求实的学问,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另一方面,考古学又是历史学的分支,是直接为复原古代历史服务的。那么,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之间有没有距离呢?在历史时代,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存在丰富的文献,考古学虽然非常重要,但其作用主要被看作是“证经补史”。考古学处于相对附庸的地位。那么,研究史前历史的史前考古学是不是等同于史前史呢?考古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即持肯定的看法。(见《什么是考古学》)但是,严格说来,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早在考古学的滥觞时期、考古学家就注意到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神话传说等对史前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一八三八年,丹麦考古学家尼尔森(Nelsson)在《斯堪的那维亚北部的原始居民》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对考古器物进行研究不是获得史前知识的唯一途径。他强调传说以及称为比较方法的重要性,“能够反映远古时代光芒的证据,我认为不仅仅是各种形式的文物古迹,以及刻划在它们上面的图形,而且还应该算上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往往产生于传说,因此也是远古时代的遗存。”他十分强调使用比较方法,即比较史前的人工制品与现代原始民族所使用的具有相同形式和功能的器物。尼尔森应用比较方法,创立了一种按生存方式为基础的史前史分期法。他把人类发展史划分成四个阶段:一、蒙昧阶段,人类的童年,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活手段;二、游牧阶段,人类的青年,以畜牧为生,另外依赖小部分猎物;农人阶段是第三个阶段;第四阶段为文明阶段,其特点是铸币、文字的发明和劳动的分工。这种分期法是后来泰勒、摩尔根、恩格斯以及苏联和我国以生存方式划分史前时代的先声。丹尼尔认为这个分期法比“同时代丹麦人的三期说更符合于历史”。显然,考古学虽然是史前历史的主要来源,但绝非是唯一的来源。这主要是由考古学的局限性和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全面了解的渴望决定的。一方面,要通过遗存了解过去的全部历史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留下痕迹;留下的痕迹并非都能保存下来供我们研究;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遗存只是侥幸保存下来的古代人类活动遗迹的极小部分;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不仅受个人实践的局限,也同时受到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局限,因而遗失甚至破坏了不少的古代信息。另一方面,人类对古代历史的兴趣日益增加,他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是否有人居住和在什么时候居住过,他们更关心居住的人是怎样的一种人,又是怎样生活的。如果把古代的历史比作一个人,那么考古学就是依靠侥幸保存下来的人的片段的骨骼和牙齿复原此人的面貌和行为,但一般公众不是对这些冰冷的骨骼和牙齿而是对此人的行为和心智更感兴趣。因而可见,在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遗存和人们对历史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如丹尼尔所评论的那样:“考古学提供了人类的技术经济史,但研究人类历史的学者不仅想要了解人类工具发展的过程,还想得知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以及人类思想道德观念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学家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攫取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所推出的结论,又为什么到现代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寻找答案。”
如何把考古材料转变成历史一直是困扰考古学家的大问题。五十年代末期,我国当时的新一代学人曾对考古学研究中的“见物不见人”现象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八十年代以来,在我国史前的大的文化框架和文化谱系基本建构完成的情况下,又有年轻的学者发出“我们今后做什么”的惊叹。显然,要让沉默的石头、骨头和陶片说话,必须通过某种中介,而最基本的两种中介就是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比如我们在一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了一些人工打制的石片,石片上有不同的擦痕,考古学家设想这些擦痕有些是由于割肉,有些是砍树木,其余是由于切割譬如草类等较软的植物材料而形成。要证实这个假说,首先要用与出土石片同样的石料制作同样的石片,然后分别用它们切肉、砍树、割草,反复试验,最后如果试验用的石片上呈现出与出土石片类似的擦痕,那么考古学家的假说就可能成立。这就是实验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实际上开始得很早,有人在十八世纪就开始这项工作了。爱尔兰的罗伯特·鲍博士是这一研究的先驱。他颇为艰难地吹响了史前时期的一个号角,结果发出的却是一种酷似野牛狂吼的声音。不幸的是,他所做出的神异的努力导致了他血管的崩裂和最终的死亡。
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实际上从考古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把某些陶器叫作罐或碗,那是因为它们和现代社会还经常使用的罐或碗相似的缘故。它们的形状相似,我们便假定它们有同样的功能并给予同样的名称。这其实就是民族考古学。但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民族考古学要复杂得多。民族考古学并非仅仅利用民族学家的调查材料与考古发现进行对比,相反,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细心的观察,以期对考古遗存的类似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比如美国考古学家约翰·耶伦(John Yellon)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南非昆桑人屠宰动物的方式以及屠杀、烹饪和食用所留下来的一些骨头的碎片。同时,绘制了许多年代已知且近期废弃的遗址图,记录下房址、炉灶以及垃圾堆积的位置,并且同曾经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进行交谈,以此作为推算较为精确的人口数量和研究居住者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这项研究对于理解旧石器时代的生活图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依靠这些中介,我们才可能回答涉及人类行为甚至心智、思想方面的问题。比如,在东非的奥杜威峡谷发现了距今二百五十万年前的人工制品,包括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各种多边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器物是从一块熔岩卵石上剥落制成的。由于这些最初的石器没有固定的形状,有人怀疑最早工具制造者的心智能力与猿相似,因而提出“奥杜威工具的一种猿的观点”,认为奥杜威工具的所有空间观念存在于猿的心中,否认该地的工具制造者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尼古拉思·托思(NToth)教授为了验证这种说法,用了多年的时间去完善他的技术,对石器制作的每一个过程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他的结论是意味深长的:“最早的工具制造者具备超出猿类的心智能力,这是没有问题的”,“制造工具需要有一种重要的运动和认识能力的协调”。
从静态的古代遗存追溯动态的人类行为和思想常常是非常危险的,尽管我们发展了中介的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倘若一个考古学家在类似北极的地理环境中发掘出一个距今两万年前的营地遗址,那他(其实我也会的)自然会与今天爱斯基摩人的情况作一番比较。但是正如考古学家布里恩·费根(BrianFagan)所说的那样,这种类型的比较研究显然过于简单和幼稚。首先,人类社会不一定都经历相同的演化阶段;其次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适应周围环境的方式,仅此一点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其文化的所有方面,甚至那种适应方式和两万年前的情况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的确,任何事物的含义总是受到文化的制约。人们根据民族学的材料对西欧旧石器时代的洞穴绘画作出多种解释,这是普通公众和历史教科书最希望从考古学得到的东西。然而著名的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质问道:“即使我们证实了洞穴绘画在其中起了作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的部分内容,我们就了解它的整体意义了吗?我对此表示怀疑。……试想一下一个人手执一根权杖,脚下有一只羔羊的图像对一个基督教徒的意义。再想想这对于一个从未听说过这个基督教故事的人来说,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含义了。”
对于意义的追寻差不多是人类特有的东西。但依靠仅有的一点古代遗存要对它们在古代社会的意义作出推测,其艰难可想而知。无论是民族考古学或者是实验考古学,作为中介,它只是我们通向古代的一座桥梁。它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增进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的理解,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解释是无法被验证的。当然,在考古遗存与民族志的和实验的材料之间建立的联系越多,解释就越可信,通向古代的桥梁也就越坚固,反之则不然。公众对于意义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承认我们——特别是考古学家——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我这样说也许会让热心的读者失望,不过要是看到下面的一席话,您大概不会认为我是危言耸听: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大部分技术上原始的人类群体行为在考古上是看不到的。例如一个巫师领导的宗教仪式中,必须包括讲述神话、唱颂歌、跳舞和纹饰身体——这些活动没有一样会进入考古记录。因此当我们发现石制工具和雕刻或绘画物品时,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这些东西只为我们打开通向古代世界的最狭窄的一扇窗子。(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
一九九六年八月一日写于双榆树青年公寓五五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