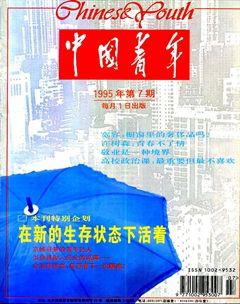武汉有个“弱者保护神”
“我们都知道武汉有个
‘集体包青天”
一对从贵州赶来的老年夫妇正在声泪俱下地向面对他们的工作人员哭诉冤情:1994年12月,他们正在劳改的儿子被劳改农场的领导安排检修高压设备故障。当时,他们的儿子根本不懂电工技术,更没有电工操作许可证,而且还是一个近视眼,又患有甲亢。但儿子老实,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检修前,场里事先已经安排好停电4个小时。然而,仅仅1个多小时,他们的儿子还在高压电器上“检修”,电闸被人合上。在高压电的打击下,他们的儿子惨死……泪水在两位老人的脸上流淌。据他们讲,劳改农场的领导在“处理”了现场、使老人的儿子死时的惨状大有改善后才通知他们,说他们的儿子“因公死亡”,并决定按“职工因公死亡”的待遇从优抚恤。但事实是领导用10多年前的有关文件欺骗他们,仅仅给了2000元钱就打发完事,而死者还遗下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两位老人泣不成声。我从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可以猜断他们决不是那种意志柔弱的人。但再刚强的人,又何以能够面对甚至承受这儿子屈死的惨痛呢?他们随身带着整整一口袋的方便面,从遥远的家乡来到这里伸冤。老人说:“请青天大人们给个公道吧!”这里的律师告诉我:他们看了老人带来的材料,认为当时判老人的儿子劳改即是过重,他们决定受理此案!
一位来自武汉市某区的年轻妇女哭诉道:她的公公是某房地局的领导,当初是公公相中她并差人说媒而使她嫁过来的,可叹她遇上了一个罕见的婆婆。婚后不久,其婆婆就当着她的面宣称男人只要拿钱回家,在外面怎么样都行。结果子从母言,她的丈夫不久就在外面寻花问柳,最后逼她离婚并将她与未满3岁的儿子扫地出门,使她与孩子无地容身……工作人员当即认定这是一起伤害妇女和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并决定受理……
为什么满腹委屈的人纷纷到这里申诉?
1992年5月,一面“保护弱者,伸张正义”的旗帜在秀美的珞珈山下赫然亮出,这就是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中心”下设妇女权利部,未成年人权利部,残疾人权利部和行政诉讼部,分别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以及《行政诉讼法》等进行具体的法律服务工作。按照他们的表述,“中心”的工作就是要为处在社会弱者地位的妇女、残疾人、成年人和那些“秋菊”们争个说法。到1995年1月,“中心”已接到并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信函2100多件,热线电话300余次,正式受理案件60余起,已胜诉结案40余件,几乎每诉必胜。
在“中心”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一面书有“社会弱者保护神”的锦旗,这是一位善良的母亲带领她那失去双臂的孩子赠送的。1993年6月的一天,年仅4岁的肖雄刚由他母亲带领来到弱者保护中心。他的母亲抓着儿子空荡荡的两个袖筒,哭诉了孩子失去双臂的经过。5年前,他们由湖北天门市迁到武汉郊区安家。在他们住的房屋后面有个配电房,变压器安装在很矮的水泥墩上,虽说有围墙,但小门常年开着没有人管,曾经发生过耕牛入内触电死亡的事件。一天,肖雄刚误入配电房玩耍,手触变压器后被强大的电流击昏过去。经抢救,小命保住了,但双臂因电击坏死而截掉,生活从此不能自理。母亲哭着找到村里要求赔偿,而村里以她们是私迁而来为由不予理睬;找至乡里亦遭推辞。母亲不甘心,上访告到区里市里,均无结果。母亲伤心之至,绝望中,听人说起武汉大学有个专为社会弱者说话、免费帮助打官司的地方,便怀揣一线希望找到“中心”。经实地调查取证,“中心”的律师确认肖雄刚是由于配电房安全设施不全而导致伤害的。“中心”常务副主任任华哲律师亲自代理诉讼。法庭上,任律师说服力极强的代理陈述以及大量证据使法院最终确认被告方负有不可推卸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判给原告赔偿费2.7万元。事后,“中心”认为2.7万元作为受害人一生所需的生活、学习、医疗费用等远远不够,受原告委托再次上诉,终于由市中院判决将原来的赔偿费提高1万元。这是中院司法判决的一个突破:以前的赔偿费从没这么高。这个案子的胜诉轰动社会,形成极大的影响。难怪记者在“中心”采访时碰到的那对上访老人逢人便说:“我们都知道武汉有个‘集体包青天!”
民告官,再也不是梦
1994年4月,一位农村青年找到弱者保护中心,控告其所在县的公安局,要求“中心”为他伸张正义。这位青年名叫胡宇清。
胡宇清是湖北省通城县农业银行信贷科的信贷员,毕业于金融专科学校。他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曾经3次荣获全省金融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10月28日,他突然被县公安局以“诽谤罪”收容审查,非法关押长达35天。何以为此?“中心”的律师经过艰苦的调查,搞清楚了事实真相。
1993年7至8月间,通城县农业银行连续出现3次“大字报”(匿名公开信),指责当时任行长的杨某利用贷款权利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并且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有“超生”行为。一石激起千层浪,3次“大字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引起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区农行的注意。9月,上级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县农行实施调查。然而,调查组的调查方式与调查结果均令县农行的职工感到意外和不满。调查期间,不仅杨某没有回避,而且调查的范围很小,仅限于行内中层干部,有的群众要求反映情况,调查组却不接待。10天之后,调查组作出杨某是清白的结论。
一俟调查组离开,杨某便转守为攻,气焰更加嚣张。他利用与县公安局某科长的关系开始追查匿名公开信的作者。由于胡宇清一向刚正不阿令杨头疼,杨便放风暗示胡是“大字报”的作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胡调到一个偏僻的乡镇营业所。
在调查组进驻县农行期间,胡宇清曾给地区农行领导写信提供具体线索。之后,针对调查组的不实结论,他又连续写信表示强烈不满。他没有想到,这些信最后竟然全部转到杨某手里。由此,10月28日他被关押收审。
在被收审期间,他遭到非法待遇,挨过打,家被抄。他是以“大字报”嫌疑和写匿名诬告信为由被收审的。但对“匿名信”的内容真实与否,县公安局根本不予调查。非法关押35天之后,他被父亲“取保候审”。出来以后,胡宇清多次向县公安局讨“说法”,得到的回答竟是“这个案子我们想挂多久就挂多久!”万般无奈之下,胡宇清找到了弱者保护中心……
民要告“官”,谈何容易?通城县法院始而不肯立案,后经请示地区法院行政庭,总算立案了。
1994年6月,胡宇清起诉县公安局的案子在县法院行政庭开庭审理。当日,老百姓像赶集似地早早来到法院,里里外外把法庭挤个水泄不通。他们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武汉大学的“包老爷”是否真的公道,民能否告倒“官”!
“中心”郑曦林、孙劲两位律师义正辞严、切中要害的法庭陈述,终于使法庭动容。1994年7月,法院宣判胡宇清胜诉,政治上还以清白,经济上给予应有的补偿。受尽冤屈未曾落泪的胡宇清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纵横。更令他震撼的是,他的胜诉使有关上级再次关注对杨某的举报,1994年9月,地区组成第二次调查组进驻县农行,经过认真查办,使真相大白。10月28日,即胡宇清被非法关押收审一年之后,县农行原行长杨某在该县矽山宾馆被依法逮捕。
“保护弱者权利,维护法律尊严”,胡宇清将自己书写的这副对联精心裱好挂到“中心”的墙上。他动情地拉着律师们的手说:“我原以为这是一场梦。事实告诉我:民告官,再也不是梦啦!”
愿痴情长久
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记者终于得到一次机会与“中心”的主任万鄂湘教授进行1小时的交谈。此前,我知道他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的所长,武汉市人大代表,但万万想不到他竟然如此年轻,不敢冒昧动问他的年龄,但猜想他没超过40岁。
问起缘何要办这个“中心”,他说:武大法学院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我任系主任时,面临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教学实习没有自己的基地,二是当时正值国家“八五”重点科技选题申报,我们报了一个公民权的项目,被批准了。理论上的研究需要实践证明,又恰逢国家连续颁布了好几个法律,所以,教学科研的需要和理论上都具备了创办“中心”的条件。这期间,我有机会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在一起,我向他谈了想法,表示名称不好定。李沛瑶考虑了一下,说:“就叫‘社会弱者吧!”我们“中心”便有了现在这个名称。它的创立使我们在教学、科研和实践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现在,“中心”的顾问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有李沛瑶,还有新华社的一位副社长。李沛瑶还给我们题了词:“为了社会弱者的权利”。
问及“中心”成立近3年,工作人员为何始终在不取分文的前提下为老百姓服务,万教授告诉记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把高层次、专业化、长存性作为“中心”的特色。几年来,“中心”的工作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最优秀的律师义务依法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他说:我们不是像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活动日那样干一些不属于本行的事情。我们要求自己在专业领域内为社会弱者服务,通过这种服务检验、锻炼和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从而体验到一种近乎物质意义上的满足。他说:为社会弱者服务不是应一时之需,也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仅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过硬的业务素质、高度的责任感和持久的精神,这正是“中心”工作捷报频传的根本所在。而治本溯源,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呼唤所有人都来关心和帮助弱者的生活与权利,才是“中心”最大的心愿!
“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痴情于自己的事业。而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者都痴情于“中心”,希望它长久不衰地为千千万万老百姓解除冤屈痛苦,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弱者”的氛围,不让冤屈的泪水白流,还社会一片湛蓝的天……
愿人民的“中心”痴情长久!
(摄影: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