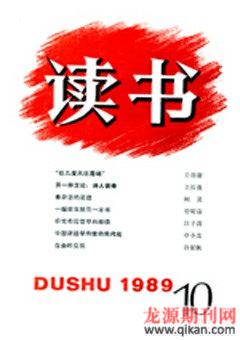中国训诂学传统的现代化
申小龙
训诂学是中国语文研究中历史最为悠久、范式最为典型的学科。它既是汉语研究的发端之学,又是几千年语文传统的集大成之学。历代学者从训诂探究着中国文化阐释的无穷奥秘。历代书塾又以训诂开启着童蒙弟子的文化智慧。这样一门同时联系着中国人的学文化和文化学的宏大学科,它的继承与发展成为历代语文学家关注的课题。尤其是在近代引进西学以后,如何以健康的心态面对中西文化传统的碰撞,如何以冷静的气度重新选择传统并赋予创造性的转化,这是摆在一代文化人,尤其是训诂学者面前的历史课题。许威汉先生的新著《训诂学导论》在训诂学传统的现代化上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回答。
训诂传统的选择与优化
“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道物之貌以告人”,这三句话可以构勒出传统训诂学的基本轮廓。从本质上说,训诂学是沟通古今语义的桥梁。通过这座语义的桥梁,一代又一代华夏学人研读着前人的思想、哲学、宗教、历史、价值观念乃至欢乐和痛苦,然而这座桥梁远非自足的。它伴随着经学的兴盛而伸向彼岸,既是此岸经学母体的一种肢体延伸,又是彼岸先人经书密码遗传的一种文化专利。于是,“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语义的桥梁异化为经学的拐杖。汉代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学校),定为五经。其教学要求是“古文读应尔雅”,然后“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所谓“读应尔雅”,意即讲解应该正确。“尔”者,近也。“雅”者,正也。而如何方能“近正”呢?舍故训别无他途。于是,如《汉书·艺文志》所言:“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许威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训诂学以经书为中心。小学本是经学的附庸。最初的目的在于通经,后来范围扩大,也不过限于“明古”。因而“崇古”是传统训诂学最大的局限。先秦的字义,几乎成为小学家唯一的研究对象。即使是现代方言的研究,也不过是为上古字义寻找一些证明而已。训诂学史上有所谓纂集派、注释派和发明派。纂集者述而不作,勤于收罗而不问是非;注释者阐微纠偏,要做前辈文字家的功臣或诤臣;发明者因声求义,以声韵的通转考证字义的通转,引导效颦者作种种狂妄的研究。这些由特点而折射其优点和缺点的学派,虽然学术源流千姿百态,然而由尊经而崇古乃是其共同的历史局限。
如何以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理解传统,阐发传统,选择和发展传统,这是摆在“五四”以后训诂学者面前的艰难的历史课题。王力先在近半个世纪前曾经倡导一种“新训诂学”。这种训诂学要矫正前人训诂只重汉代以前,汉代以后很少论及的毛病,把语言的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就值得去追求它的历史。许威汉先生认为这已经远远不够了。传统训诂学搜集编纂之功有余,归纳概括之力不足;虽长于分析,却拙于综合,研究方法不够科学,理论淹没于材料之中。因而训诂学的理论建设是这一古老学科的当务之急。训诂学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加强对训诂学史和训诂学方法论的研究。而作为这些工作的基础,是对传统训诂术语作科学的现代清理,确立现代训诂的元语言。许威汉指出:术语是科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环节。没有内涵和外延确定的术语,科学的抽象思维便难以进行。术语标志着某种现象已被从本质上概括体现出来,也标志着许多与之近似的现象已被区分出去,科学术语的确定与科学原理的总结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从这一独特视角开始训诂学传统的选择与优化,我们认为是颇有见地,也颇赖功力的。
用科学的语言表述传统训诂学的范畴,这一工作前人也试图做过。然而要表述得准确清晰却很不容易。《训诂学导论》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开辟了多种表述渠道:
理论概括。对于某些范畴术语给予直接的理论定性。例如“谓”是,个常用的训释词。许威汉指出:它用来表示以一般释特殊或以具体释抽象。如《论语·阳货》“君子学道以爱人”,孔安国注:“道,谓礼乐也。”
用法辨微。对于难以直接定义的传统训诂术语,从它的实际运用辨析其内涵。例如“犹”这个训释词有四种释义功能:(1)以意义相近的字来解释。如“漂犹吹也”。“漂”本训“浮”字,因“吹”而“浮”。(2)以引申义释本字。如《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赵歧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3)以本字释借字。如《文选·册魏公九锡文》“若赘旒然”,李善注引何休《公羊解故》:“赘犹缀也”。(4)以今语释古语。如《诗经·魏风》“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诗集传》:“掺掺,犹纤纤也。”
范畴对比。“浑言”(笼统地说)、“析言”(分析地说)又称“散文”、“对文”。一般地说,“浑言”彰其同,“析言”明其别,旨在揭示同义词之间内在的联系与区别。例如《说文·鸟部》“鸟,长尾禽总名也。”段玉裁注:“短尾名佳,长尾名鸟,析言则然,浑言则不别也。”对比与“浑言”“析言”相应的“散文”“对文”的用法,许威汉指出:“散文”、“对文”的说法早在唐代就出现了,强调的是同义词的使用方式。清代的“浑言”“析言”则是训释方法,应属两个范畴。但它们有密切的联系:对于不同场合使用的词语,一般要有不同的训释方法。
求同存异。传统训诂学的范畴并非都是严密的。在对这些范畴术,语作现代清理的时候,有必要会其规律性之大同,存其小异。例如“读为”“读曰”和“读若”、“读如”这一组经常混用的训释用语,会其大同则前两个是用本字破假借字,例如《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后两个是注音的,例如《说文》:“哙、咽也。从口,会声。或读若快。”然而后两个也可以有用本字破假借字的用法。许威汉指出,这是古人使用术语不严密而产生的混乱。正是这种混乱造成前人对“读若”性质的不同说法。
以上四种表述传统范畴术语的方法,为训诂学体系的优化作了有益的探索。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传统训诂学范畴术语在方法论上还有不少应予扬弃的东西。名实不符是其一。例如把由于词义的发展、方言的变异而引起的字音变化名之为“一声之转”,令人不得要领。名无界说是其二。例如“假借”这一术语或指若干引申义依托同一形式,或指意不相关的同音字互相借用,其中又分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和“本有其字,同音替代”两种情况。于是词汇、文字、语音等不同平面的现象纠葛缠绕,难以界说。一名多实是其三。例如“引申”既指一个词由本义推演而形成新的意义,又指“义自音衍”的文字孳乳现象。正由于术语定称的歧义重出,传统训诂学使用术语往往采取兼容并包的办法,遇到假借字、通假字、古今字、同源字以及异体字,一律释为“某通某”。一个“通”字模糊了训诂释义的科学眼光。有鉴于此,许威汉提出对旧的训诂范畴加以改造的思想。例如“义界”是用于定义的,对于类似义界的现象,可否增立辅助性术语“准义界”?“互训”往往不一定“互”,而是今语释古语、常用词释难词,可否略加改造,为“直训”?词义延伸而不造新字,旧时或称“引申”,或称“转注”,或称“假借”,后两种混淆了词义现象与文字现象,可否选择“引申”?“词气”这一范畴不知所云,难以确指,可否废弃?分析字形时拆卸出的不能独立成字的部分,可否总称“构件”?“古今字”说解歧出,可否改称“区别字”,列为同源字中的一种?如此引申开去,“同训”“递训”“类训”“同义互训”“反训”“直训”等能否调整为一个训释层级系统?从《训诂学导论》提出的种种范畴改造更新的思路来看,作者已大大跨越,一般训访学著作祖述传统,只求其然的学术规范。他要辨其所以然,要为古老的传统注入科学和理性的血液与生命,要努力寻求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作者治训诂而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发展”意识正是现代人健全的“传统”意识的写照。在作者眼里,训诂学并非旧时代的“遥远的回响”,训诂学的传统并非某种一成不变的国故。更重要的是,训诂学传统之于“我”并非某种身外之物,而是“我”参与其中的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是传统。当代训诂学家面临的问题既不是匍匐在小学的颠峰下膜拜礼赞,也不是“脱胎换骨”而成为西方语义学的传教士,而是以“我注六经”的态度对训诂传统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理解和选择、解释。而由于这种“我注六经”的新的学术规范使训诂传统不再作为古董而藏之名山,奇货可居,而被输入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与创造,因此训诂学的继承与发展实质上又是一个“六经注我”的过程,《训诂学导论》自觉地将传统接过来,打上自己的印记,输入这一代人的创造与理解,使之为当代生活之需要服务,这正是学术文化发展的一种健全的形态。
训诂理论的更新与拓展
《训诂学导论》名为“导论”,往往“导”中有论,“论”中有“导”,始终保持着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性与新鲜感。近人朱宗莱《文字学形篇、训诂举要》中曾列举七种训诂方法:一形训,二音训,三义训,四以共名释别名,五以雅言释方言,六以今释古,七以此况彼。细察之,其中四至七皆为义训。训诂之法不外乎从形、音、义出发的训释。许成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对这三种训释角度都作了新颖的探讨。
由于汉字的块然具象的特点,形训对于探索字义本源有特殊的作用,《颜氏家训》曾云:“学者若不信《说文》之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划有何意焉。”《说文解字》的小篆字体是秦代统一文字,释义又与十三经注释一致,据《说文》以考形义自然是训诂的主要门径。然而许威汉指出,在考求形义的时候,有必要区分笔意与笔势。只有较早的文字笔划才是笔意。随着字形的发展,点划往往只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字形与字义的直观联系切断了,笔意成为笔势。例如小篆的“民”的形体已无笔意,只有上推到古文字中的“民”,其从女作捆绑状,意即俘虏或奴隶。以形索义须以笔意为据,防以笔势索义。有人释“妻”为“十女同耕半亩田”,不想“十”为头饰,“彐”为“手”,这就很可以使形训者汗颜了。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学在方法论上的一次革命。清郝懿行谓“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戴震谓从音理上推阐的古同声纽的字其义多相近,黄元吉谓同一韵的字其义皆不甚远。然而,音义相关的理论根据何在?训诂论著大多语焉不详。《训访学导论》则作了精譬的阐述。音和义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某一语义要求用什么语音形式来负载,一开始就具有偶然性。但音义的联系一旦经社会约定之后,早起的词的音义关系即对后起的音义关系产生“回授”作用。先产生的词的音义关系在由它派生发展(孳乳演变)而来的新词上表现出的回授性使意义上的相承及于语音上的相承。于是“约定”之前音义无关,“俗成”之后音义往往相联系。“回授性”是“有理性”,“偶然性”是“无理性”。无理的偶然一经约定俗成,便产生有理回授的可能。约定在从无理性趋于有理性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未经约定自然也就谈不上有理回授。音义关系的回授性促使特定的声音与特定的意义结缘,产生了为中国训诂学传统所津津乐道和孜孜以求的音近义通现象。训诂阐释的重要轨道也就是循音义相关之迹而通假借、明方言、寻语源。
如果说形训和音训都有文字物质形态上的依据作为训释的支撑点的话,那么义训的支撑点就只能是语言环境——上下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音训和形训都不能据其一端以妄加推测,都必须接受上下文义的检验。因此据文证义是训诂方法中的“根本大法”。有人把音训比作小学家手中的“犯罪凶器”,就是因为不少人跳开了语境文义而孤立地作“音近义通”的臆测推导,训诂的手段异化为目的,留下训诂学史上无数的遗憾与苦涩。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词语按照语言规则组织成句子,它们在句中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套用语法学界一句运气不佳的名言,那就是“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因此词义的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认可都必须经过文句意义的贯通赋予其灵魂。《孟子》:“为长者折枝,曰不能。非不能,是不为也。”朱熹解“折枝”为“折断树枝”,赵岐则判为“解罢枝”,即松动疲劳的肢体。从上下文意而言,当以赵说为胜。“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两处“可怜”,一为“可惜”,一为“可爱”,亦唯据文证义方才晓喻。在这里,上下文义为语词提供了唯一可以认定其身份价值的意义场。
《训诂学导论》的理论建树不仅在于训诂方法论的精湛见解,而且更体现于作者对于具有汉语特点的词义发展规律的独具的慧眼。我国语言学界流行词义扩大、缩小、转移的说法。这一说法源自德国语言学家赫尔曼·保罗的《语言史原理》。它对汉语词义引申演变的研究起过独步一时的作用,几乎主宰了一部汉语词义变迁史。然而,透过其冷峻严整的理性表象,人们不免有浅尝辄止之感——一种民族语文的失落感,它并没有使汉语词义演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正如许威汉所说,在于没有紧密结合汉语特点,立足于吸收我国传统词义研究的丰富营养。例如清人段玉裁对于词义引申的探讨比德国学者保罗的词义扩大、缩小、转移说早一百多年,其内容之丰富当为首屈一指。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许多理性认识散见于字例的训释中,未能升华为理论之体系,这未竟之业正有待现代语言学家的继往开来而后来居上。许威汉指出,训诂传统中的零珠碎玉是建筑汉语词义理论华构的基础,同时,要使之有机地合成华构还得匠心独运,群策群力,从汉语实际出发,借鉴西方理论而不只在名词术语上做文章。这一番见识对于汉语词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可谓入木三分!作者正是在这一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将汉语词义的引申区分为理性引申、形比引申和礼俗引申。其中理性引申包括因果的引申,如“习”由鸟屡次拍着翅膀飞引申为反复练习、通晓;时空的引申,如“往往”由空间(《史记》:“旦日卒中往往语”)引申为时间;反正的引申,如“藐”由“广”义引申为“小”义;虚实的引申,如“益”由水满、增加引申为“更加”。形比引申,例如“本”由树根义引申为事物的基础、发源和决定因素。
在西方人探究语言的历史长河中,对于语言的功能和价值的肯定曾经历了三重转换,即语言的隐喻功能和神话学价值,语言的逻各斯功能和形而上学价值,语言的修辞论辩功能和语用学价值。然而中国语言学从它脱胎于经学母体的第一天起就认定了语言的阐释功能和释义学价值。源远流长的训诂学成为人类语言学史中最为宏富深邃的动脉。我国现代语言学从本世纪初以来就关注训诂学传统的现代化,然而在乾嘉学派的巨大历史光焰下难以自省与自拔,以致除却言必称“段王之学”,就惟有拾西人词汇学之牙慧。近年来一批新的训诂学论著面世令人耳目一新,其共同特征是在训诂学传统现代化的努力中,具备了一种从容而有选择、平静而不急功近利的文化心态。这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训诂学在长期的理论反思与理论准备之后,开始呈现出的一种健康的运动形态。《训诂学导论》的出现,预示着东方古老的训诂学传统将从本体论到方法论都获得较为充分的当代意义,以前所未有的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我们衷心期待着。
(《训诂学导论》,许威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