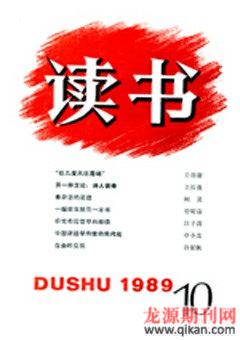阿道尔诺与绝望的“否定”
吴 康
阿道尔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极深广的研究,揭示或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课题。他一生都在毫不妥协地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最后在他的论敌的羞辱中悲剧性地死去。阿道尔诺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批判虽然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情调,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染上了资产阶级现代思潮的色彩,但是,对于一位具有开放精神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的思想成就是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哲学领域中他的“否定的辩证法”观点的提出,以及他对现代音乐的卓有成效的社会批评,无疑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占有一席地位。
《阿道尔诺》的作者马丁·杰是其生前好友,作者在全面把握阿道尔诺生平著述材料的基础上写成。虽然行文略嫌晦涩,引证过于广博,但能在如此简短的篇幅中,概述阿道尔诺坎坷的人生及多才多艺的学术活动实非易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其思想的深度准确地切中了阿道尔诺思想的脉搏,因而能够把握实质,从整体上再现当代思想大师——阿道尔诺。
在导言中,作者极简洁地概括了阿多尔诺思想力场中的五种活力: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主义、上流文化保守主义、犹太情感及拆构主义。作者认为,在他思想的五种合力场中,最主要的引力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他思想星丛中的最灿烂的明星。
阿道尔诺哲学观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个论题:由于先前的唯物主义不能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去理解人的主观性,所以相反,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并维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阿道尔诺认为,马克思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仅仅不断地重复着唯心主义的主观性观点,而他的任务就在于恢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初衷。
唯心主义最狡猾的伎俩在于他们以一种所谓的抽象的集体主体来替代主体概念。如黑格尔,他的辩证法从一种抽象的主体出发,通过否定自身而进入客体,再由否定客体而回归到集体主体。马克思之后的著名思想家卢卡奇也只是不同程度地重复了黑格尔这一主客观同一的模式。在他的所谓“总体”的概念中,他提出了一种构造性主体,即现实的元主体——无产阶级,因而创造性的主体意识在他那里被归结为“阶级意识”。阿道尔诺认为,这种主客观同一理论只是对逝去的原始同一状况的追忆。“主体形成以前的那种无差异状态是对自然盲目之网的恐惧,是对神话的恐惧”。“主体与客体的幸运统一这幅原始状况的图画是浪漫的,但今天却不折不扣地成了谎言”。因为这种主体旗帜下的同一实质上导致了对客体的支配。
《启蒙的辩证法》所揭示的正是这种支配的历史展现。文艺复兴以来兴起于近代欧洲的思想启蒙正以对人的主观性的强调为其号召,它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当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启蒙是必要的,它使主体挣脱自然之网而独立地发展起来了。但是同时,启蒙发展了人控制支配自然的权利,发展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一方面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文明与繁荣:在经济上它表现为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政治上表现为现代资产阶级大革命,哲学上表现为登峰造极的黑格尔式同一性理论,在文化思想的其他领域,它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一旦发展到极端就走向了它的反面,由于它以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它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两个可怕的后果:其一是对人的内在自然的限制,工具理性仅仅与人的某种生理功能相适应,而人的其他功能都遭到了可怕的压抑,人的全面的自然要求走向片面化。因此,与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相适应,人退化为单面的怪物,片面的物质享乐与精神贫乏撕裂着现代人。另一后果是人对外在自然的破坏。人对自然的蹂躏导致了自然的无情的报复。正是这两个可怕的后果破灭了工具理性所支撑的现代神话。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现代神话残酷而血淋淋的破灭。理性所造成的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生产力,本应用来造福人类,但不料竟成为了毁灭自身的战争怪物。因此阿道尔诺预言:“并非所有历史都是从奴隶制走向人道主义”,还有另一种“从弹弓时代走向百万吨炸弹时代的历史”。启蒙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它在历史的进程中走向了反面。因而只有“否定”才是辩证法的唯一要素,它粉碎了任何泯灭主客体差异的“同一”论幻想。
主客体同一的实质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心与物的分离。它在历史的过程中表现为劳动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而分工的实质在于抽象。正是因为抽象才使得主体上升为抽象的一般性的要素。因此,要摆脱主客体的分离,要填平分工所带来的鸿沟,必须恢复客体的应有地位,而要恢复这一地位,首先必须排除抽象。阿道尔诺认为,信任“经验”是主体排除抽象的最好办法。经验以历史的记忆为基础,它是人对自然最初状态或儿童时代的体验的追忆,这种追忆能适当地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显然,阿道尔诺的哲学观主要在于他的批判方面。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对充满危机的现代西方社会作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并相当深刻地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在建设方面,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失望,其理论找不到任何现实力量,因而只能陷入毫无肯定性的悲观主义,只能从理论的思辨和具有微弱声息的所谓的“乌托邦”中寻求他的希望所在。
由于反对集体性的元主体概念,阿道尔诺必然坚持恢复心理学在总体中的合法地位。因为心理学首先以一种经验主体为其对象,它是反对以所谓更高级更普遍的主体名义压制主体的合法保垒。并且,在心理学中,人的自然本质才能得到充分的显示,它是个体真正肉体享乐权利的最好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经济主义者把劳动和生产视为人类的自由之所,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和政治倾向则相反地赋予集体实践以这种权利,阿道尔诺对心理快乐和感性快乐的强调意味着,他把同样的价值给予了消费领域”。
阿道尔诺对心理学的强调主要表现在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批判上。阿道尔诺感兴趣的是本来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学说,他对弗洛伊德后来的观点是基本上否定的。他认为精神分析的“移情”方法是对被治疗者的玩弄。他也不赞成弗洛伊德文明与享乐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永恒冲突的观点。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对弗氏后期理论中的死本能的详尽阐发,他始终保持着冷淡的沉默。至于弗氏以自我统率本我和超我的三重人格学说被他作了彻底的否定,那个自称已被完成了的整合而成熟的自我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罢了,“精神分析学从总体上使人屈服于合理化和适应的机制”。
弗洛伊德有价值的是他道破现代创伤的早期理论,只不过他采取了一种夸张的手法。例如弗氏著名的所谓女性的阴茎妒忌的观点。从常识来看这是一种胡说,但从资产阶级的社会现实来看,这种观点正道破了一种痛苦的真实,因为它正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妇女的身心压抑的状况。同样,弗氏的阉割焦虑比他的信徒们提出来的竞争的自我模式更切合于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在这个集中营的时代”,“阉割比竞争更能代表社会现实”。
阿道尔诺更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学的家庭理论,在家庭这个社会环节上,弗氏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从而弥补了他早期理论的缺陷。家庭是人与社会的一个中介,它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送带,也是这个“无情世界中的一个避难所”。家庭中的父性形象是儿子们仿效和将来替代的独立的象征,而哺育的母性职能则把一种乌托邦的批判能力灌输给后代。但是在现代这个管理化世界中,家庭消亡了。统治集团的压制、大众文化及垄断资本主义对家庭中父性经济独立性的侵蚀,这一切使得家庭中的父性形象丧失了。儿子们只能对这个无情的世界唯命是从,他们无法向独立自主的自我迈进,而是退化到自恋的自我,甚至再由自恋的自我堕落成受虐狂式的满足,这样,家庭就仅仅成为了产生“极权主义人格”的温床。
既然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和人都已堕落了,那么说社会中的阶级的状况怎样呢?阿道尔诺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唯一最关注社会阶级分析的思想家。尽管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理论变得不太现实了,尽管无产阶级已产生了极大的分化,但他一直坚持阶级的存在,坚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只不过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的侵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迭合成了一个概念,即现代“工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阶级对立转化为纯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社会的个人日益原子化,而不是阶级分化。整个社会变得浑浑噩噩,人们被治成了像尼采所说的“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在从心理学到社会学所经历的从人到家庭到阶级及社会的普遍考察中,阿道尔诺所看到的都是绝望,那么,是否也有希望之所在呢?是否也有什么东西来拯救这个全面崩溃了的世界呢?如果这样提问,阿道尔诺也许会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说:“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外就毫无希望了。”也许会以微弱的声息回答:救赎它的因素是美和艺术。当然,这是他的一种“乌托邦”的希望。
阿道尔诺卓有成效的领域是对现代文化所作的全面的批判。作为一个彻底否定的辩证文化批评家,他并不赞成把文化分为高级文化(诸如艺术、哲学、学问等)与低级文化(诸如惯例、习俗等社会生活方式),而用前者来救助后者,因为在一个被工具理性全面意识形态化了的工业社会,只可能存在一种文化,这就是所谓“文化工业”。无论是精英意义上的高级文化,还是世俗意义上的低级文化都被同化而腐化掉了。现代文化不折不扣地成为了谎言。“文化创造了并不存在的与人相称的社会幻想”。文化工业实质上充当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撑物,“它不断地从它的消费者那里骗取它没完没了地许诺过的东西。它玩花招、弄手脚,无休止地延期支取快乐的约定的支票;这种允诺是虚幻的,实际上永远也无法实现”。
在犀利的现代文化批判中,阿道尔诺大大深化了马克思早就论述过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利于艺术发展的观点。在这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典分析仍是阿道尔诺文化批判的重要支柱。因为在囊括一切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由于交换中抽象的等价物——货币的介入,各种商品对不同消费者的实际使用价值被掩盖了,商品中所蕴含的生产者的创造性劳动也被掩盖了,全社会变得了一种尺度,交换的尺度,金钱的尺度,商品拜物教吞噬了一切。艺术生产变成了纯粹的商品生产。艺术与广告技术之间的差别湮没了。艺术之所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满足任何真正的需要,艺术创作中作家的才能与个性被商品生产这只罪恶之手,消除得一干二净。
阿道尔诺更有特色的是他对现代音乐所作的社会批评。《启蒙的辩证法》中的否定的历史主义观点更全面地体现在他的音乐批评之中。启蒙辩证法所造成的文化困境在音乐上最初始于巴赫的作品。巴赫第一个把“展开式变奏技巧”引入了音乐。这种音乐创作技巧的突破实际上标志着:音乐由手工艺生产向批量生产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生产过程通过被分解为更小的要素实现了合理化。巴赫是“把合乎理性地制作、即对自然加以审美控制这一思想具体化的第一人”。
由巴赫开创的音乐控制自然的过程在二十世纪达到高潮,但展开式变奏技巧的高峰则是比他早得多的贝多芬的创作。阿多尔诺把贝多芬与高级资产阶级文化的英雄时代联结在一起。这一时代在哲学上和文学上产生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奥林匹斯山的两位宙神的黑格尔和歌德,而在音乐上能与他们比肩的人物就是贝多芬。贝多芬代表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高阶段,代表了实践理性在感性关系中的最清楚的体现,代表了积极的主观性在客观音乐素材中的最伟大的实现。
但是,贝多芬以后,随着资产阶级主体神话的破灭,这种“能动展开的主体”的音乐高峰就无人企及了,甚至连贝多芬本人的后期的作品也是这样。阿道尔诺认为,最能代表这种衰落的是瓦格纳,他把瓦格纳看着是与贝多芬正相反对的人物。贝多芬的交响乐是连贯的总体化作品的范例,而瓦格纳的歌剧却缺少任何真实的发展原则或真正的主观性,因而他只能借复活某种神秘的共同体来追求所谓德意志民族的新生,而这正好暗示了后来的那种法西斯精神。他对无限旋律的依赖,就像是黑格尔的“恶的无限性”,无休止地无目的地延续着,它展示了晚期资产阶级人士对无法控制的现实的妥协。
能拯救现代音乐的这种发展颓势,并寄托着阿道尔诺“乌托邦”希望的是勋伯格的“新音乐”。阿道尔诺给勋伯格誉以“辩证的作曲家”的称号,勋伯格明确地推翻了贝多芬及整个西方音乐的总体性原则。在阿道尔诺称之为现代音乐“英雄十年”这一期间,勋伯格把音乐从占优势的有调和弦和声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他使不谐和音(没有节奏的音乐)作为一个整体的诸片断而非偶然地出现。勋伯格的无调音乐最具表现主义的特质。
从阿道尔诺对现代音乐历史的简要勾勒之中,从他所推崇的勋伯格这里,我们仍然丝毫也看不出有任何肯定或有希望的痕象,一切都在否定之中进行。即便是勋伯格本人,后来也违背了他无调音乐作曲的初衷,皈依到十二调连续曲之上去了。勋伯格的无调音乐革命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主体“沉沦后余留下来的绝望的信息”,是其死亡前痛苦的流露。在这一点上,这位无调音乐家倒是与无调哲学家——阿道尔诺同声相应,他们所奉行的都只是“否定”。阿道尔诺从马克思那里出发,但他不像马克思,于批判中预言了一位未来的掘墓人,因为这位掘墓人似乎已被同化而不复存在了,因而他限入了绝望。他的全部理论就正像那只被扔进了大海的瓶子,是否能遇到未来的收信人呢?
(《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美]马丁·杰著,胡湘译,2.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