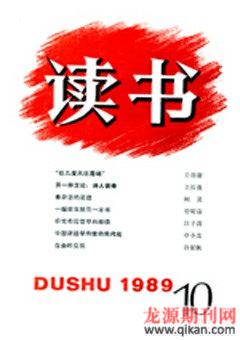一幢建筑就是一本书
曾昭奋 柴裴义
一九八九年,中国建筑界出了两件前无古人的盛事:由《世界建筑》杂志社发起的“八十年代世界名建筑”评选活动和由中国建筑文化沙龙、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八十年代中国建筑艺术优秀作品”评选活动,使中国建筑艺术的园地里很热闹了一阵子。这两起主要由中青年建筑师发起和组织的民间活动,得到了建筑界和文化艺术界老一辈专家和有关领导的关心和支持,都有了圆满的结果。
在八十年代里中外万千个建筑新作中,被拉到排头来的,只有寥寥二十个。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约略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下的足迹和信息,看到在这个年代里,中外建筑艺术思潮和创作实践的倾向和进展。本文将论及其中的四个外国实例和两个中国实例。
一
许多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和变化,促进建筑艺术在过去十年中到达一个新的阶段。广大公众不再仅仅满足于建筑的使用功能,不再欣赏建筑的简单几何形体,也不再赞同建筑师对传统样式的重复和抄袭。建筑师们的思维模式和艺术趣味,则带着更多的哲学思考。他们在创造新的建筑形式并赋与它们以浓浓的人情味儿时,在技术上已经没有多少障碍,在经济上也不再那么吝啬和精打细算了。
建筑中的现代主义被建筑理论家J·詹克斯宣布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三十二分死去。(詹克斯《后现代建筑语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美国的P·约翰逊声称:现代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它的“尽端”,不再是我们“时代的进步形式”。(戈德伯格《后现代时期的建筑设计》)他们的这些观点,得到了中青年一代建筑师和建筑学生的响应和拥护。发端于六十年代初期、企图取现代主义而代之的后现代主义,终于在八十年代里建立了自己的第一批引人瞩目的纪念碑。其中初期的、最著名的实例之一,就是约翰逊设计的、一九八四年落成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总部大厦(纽约)。这位曾因设计玻璃盒子摩天楼、大力宣传“国际式”建筑而驰名于世的现代派大师,在自己的这一新作中,大胆使用了古典手法和词汇并对它们进行改造和夸张,表现了对现代主义的背离和对历史的回顾与联想。在这座高六百六十英尺的大厦顶上,突出着一个三十英尺高的巨大山花,带着圆形缺口,像老式木座钟或十八世纪的英国衣柜的顶饰。这个设计方案引起了美国国内外建筑界和一般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从方案公诸报端到建成开业,六年内,美国的许多全国性报刊(不限于建筑专业的),共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长篇大论,对它进行攻击,或为它进行辩解。对它所表现的形式,所宣扬的建筑理想,不可能有一致的评价。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它是“时代的标志”,“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纪念碑”。《纽约时报》建筑评论员P·戈德伯格说,这个建筑形象“有着令人尊敬的含意。许多战后出现的平屋顶建筑无疑是一场美学上的灾难,使城市天际线出现混乱,令人厌烦”,是它“给(城市)天际线带来了一点浪漫性。”
有人认为,约翰逊甘心选用和模仿古典建筑词汇,太过缺乏大师风度,是他在建筑艺术创作道路上的倒退和悲剧。然而,还好,举起后现代旗子以及集合在这面旗子下面的建筑师们,并没有都拥挤在约翰逊“倒退”着走的这条窄道上,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进发”。(詹克斯《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在许多后现代建筑师的笔下,现代主义的清规戒律都被抛弃,建筑的形式和语言,不再那么纯净,那么单一。古典的/创新的,西方的/东方的,本土的/外来的,高技术的/高感情的,真实的或虚幻的,完美的或残缺的,高贵的或庸俗的,美的或丑的,都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作品中。它们既向着建筑师,也向着普通公众,既向着生活的现实,也向着心灵的幻想,表演和诉说。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州立新美术馆和日本筑波新城的市民中心,就以其多元的、折衷的、雅俗共赏的形象和性格为各国建筑界和艺术界所广泛传诵。
这两个后现代建筑,一个在东方,一九八三年建成,日本一代中年建筑师的杰出代表矶崎新所作;一个在西方,一九八四年揭幕,由英国当代最有成就的三位建筑师之一,J·斯特林设计。它们身处异地,却不约而同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当代建筑艺术形式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包容性和群众性。建筑艺术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享受、才能够理解的艺术,也不再是僵硬、无情的材料和技术的堆砌。一个在二次大战的废墟上新建的美术馆,被塑造成文化休息活动公共中心;一个新城中的市民广场,被安排成充满文化气息和感情色彩的活动园地。这两个地方,人们都可以在漫步中、在闲散中随意进入或穿行,轻松自如地去鉴赏和领略当代艺术和建筑艺术的成就和风采。它们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参差不齐的艺术爱好和感情需求,使建筑艺术重新展现其最古老的,同时又最具现代特性的本质:一种真正通俗性群众性的艺术产品。
今年世界建筑节(七月一日)这一天,我正好整日在筑波中心度过。在这里,西方古典的石头建筑与东方的汩汩流泉相映成趣,米开朗基罗的优美图案和日本的古代神话构成了椭圆形公共广场的主旋律。灰色的下沉式广场和在它周遭升起的色彩艳丽的铺地任你上下徜徉,悠闲漫步。生生不息的树木和用钢铁雕成的萋萋水草令你真伪难分。既有精心的雕琢和排比,也有随意的构图和拼凑。设计者显然同意詹克斯的理论主张,把这种种手法和做作叫做“分裂—折衷主义”,叫做艺术创造过程中的“精神分裂症”。但是,上述种种因素种种手法,在建筑师的调遣之下,却都显得那样相异而又相亲,那样对立而又那样和谐,那样雅致而又那样随和。矛盾、雅俗、文野、新旧,一时难以辨别,难以清理,但却是一个可以理解、可以对话、可以投入的崭新的建筑环境。
许多评论家认为,斯特林在斯图加特美术馆的所作所为,较之矶崎新在筑波中心所作的更为随意,更为大胆。它是那样夹生、混杂,又是那样撩动人心。这里有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圆形雕塑展览庭院和埃及神庙的凹曲的房檐,又有构成派的钢和玻璃组成的雨罩和蓬皮杜中心式的暴露的管道。既有阿·阿尔托晚期风格的扭曲的玻璃外墙,也有勒·柯布西埃早期风格的平面设计。高技派的鲜红色钢管(作为栏杆扶手)与厚重的大理石墙碰撞在一起,精美的雕像和着意摆布的废墟在互相倾诉。新、旧、正、反,各种符号杂然并陈,不同信息同时袭来,各种片断和情节的蒙太奇拼接,俨若一部意识流小说,展现着半实现、半梦幻的既古老又现代的意境。人们兴奋地接受它,也愿意慢慢来理解它。
然而,在传统中,在学院派那里,建筑艺术却不是普通人的事儿,它“不能俯就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的趣味,不能与‘非精美艺术混在一起”。(N·佩夫斯纳《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现代派造了这传统的反,造了学院派的反。建筑不再有神秘的高贵的光环,但是,仍然被看成智者(现代建筑师自己)对普通老百姓的怜悯和赐与。后现代派造了现代派的反,也造了学院派的反。美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R·文丘里,在一九六六年说的一段话,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纲领和宣言。他说:“建筑师们再也不要被清教徒式的、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的说教吓唬住了。我喜欢建筑的‘混杂而不要‘纯种,要调和折衷而不是干净单纯,宁要曲折迂回而不要一往直前,宁要模棱两可而不要关连清晰,既反常又无个性,既恼人而又有趣,……。我爱‘两者兼顾,不爱‘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是黑白都要,或者是灰的。”(文丘里《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但是,当许多后现代建筑师果真如此这般动作,极力推崇这种非理性的、不和谐的建筑形式美的时候,却把建筑创作过程和创作成果当成个性的发泄和随心所欲的形式游戏。他们造了别人的反,却没有能够约束自己,变得放肆和玩世不恭,有的已陆续推出了怪诞的、故弄玄虚的甚至是形象龌龊淫秽的“作品”。例如,在楼上的卧室的地板上,故意留下一条几十厘米宽的挖透了的槽沟,在公众出入的门厅里,煞费苦心安排了假门窗和伪楼梯,甚至把整幢建筑塑成男子生殖器的形状,等等。他们虽然因此出了名,但理所当然地没有被中国的评选者选进“名建筑”之列。
二
在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面前,现代建筑不是简单固守自己原有的阵地和原则。它在自己的近百年的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从后现代派的实践中得到启示。自六十年代以降,现代派建筑继续显示其在不同场合、不同设计对象面前的认真、严肃和深思熟虑,又开始注意到建筑的地域性、民族性,把过去抛弃、否定过的装饰、历史联想和人情味等,组织到自己的作品中。看来,现代主义并未死亡,也还没有走到自己的“尽端”。
蜚声世界的华裔美国建筑师贝聿铭为巴黎罗浮宫博物馆所作的扩建设计,就是现代派在八十年代中的杰出成果。
人们把巴黎视为西方文化的中心。罗浮宫是这个中心的中心。如今,要在这中心的中庭添建一座新建筑——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房建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的封建宫廷的院落中——矛盾集中到这个焦点上,全法国甚至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建筑师们将如何动作。一九八三年年底,密特朗总统亲自点将,把设计任务交给了贝聿铭先生。面对这座反映着封建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之间尖锐对立的、凛然不可亲近的,却又是法国古典建筑杰出代表的罗浮宫,贝谨慎而又沉着,给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要自己的新设计“不触动”这座宫殿,“既充满生气,有吸引力,又要尊重历史。”
一九八四年二月,贝公布了罗浮宫地下宫设计方案。在拿破仑庭院中,露出一个底边长各三十二米、高二十米的玻璃金字塔。它是地下宫的入口大厅的顶子。简洁的几何形体与罗浮宫的丰富轮廓和精美雕饰形成了强烈对比。它引起了法国公众的纷纷议论。人们认为,贝聿铭可以“创新”,但不该采用这种众所周知的属于古埃及的金字塔的形式。《费加罗报》在它的一批读者中征询意见,据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持上述态度。但是,跟一百年前落成的埃菲尔铁塔的命运相比,贝
贝认为,这个作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设计。事实证明,正是它的简洁和透明,充分表达了建筑师的创作意图:既尊重历史,又充满生气,洋溢着时代精神。人们在广场上可以欣赏金字塔的轻盈,欣赏现代建筑材料建筑技术的神奇表述;在金字塔里透过那玻璃的纱幕,却仍可一睹罗浮宫的丰姿,然而它变得温存和朦胧了。一位现代大师在古老的宫殿面前出奇制胜,并为爱挑剔的巴黎人所赞赏,正好证明现代建筑还没有丧失它前进的勇气和活力。
现代建筑在二次大战之后发展到自己的顶峰。之后,它不断地修正和充实自己,并从千篇一律的方盒子、“国际式”中摆脱出来。跟现代建筑相比,后现代还只有短短三十年的历史。在这三十年中,它们之间,互相奚落挖苦,又相互激励竞争。随着时日的流逝,它们终于发现:你我还都在同一条船上,同处于一段连续急转弯的波浪湍激的河流中,面对着同样的任务和同样的观众。不少现代建筑师在一夜之间就奉献出来后现代主义作品,而那些由现代派训练培养出来的后现代建筑师,也仍然保留着“现代”意识。在他们面前,一个更激进、更加脱离常轨的流派,已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
八十年代西方建筑界的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解构主义(一译解解构主义)建筑的兴起。它已经推出了第一批作品。前面提到的约翰逊——曾是现代派的干将,又转变为后现代派的“父亲”——去年八月在纽约举办的一次“解构建筑展览”,就展出了七位知名建筑师的作品。法国/瑞士血统的、一九四四年出生的建筑师B.屈米规划设计的巴黎拉·维莱特公园,被公认为第一批解构建筑中的代表作。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J·德里达,也直接加入到建筑艺术发展的论争中来。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开始的。他的理论在建筑界引起了反响。去年七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为了讨论解构主义建筑艺术,就专门亮出了德里达的观点。德里达认为,在当代建筑中,“‘疯狂把普遍的混乱和无序付诸实施,……一切事物已经使建筑放弃含义”,“它们(‘疯狂)维护、更新和重写建筑。”(英国《建筑设计》一九八八年三/四期)从这种观点出发,德里达以哲学家的眼光审视并肯定了屈米的公园设计。
维莱特公园位于巴黎东北角,占地五十五公顷。屈米的设计方案是在一次国际设计竞赛中中选的。去年,公园一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它是城市通向郊区的门户,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公园——一个旅游和国际交往的中心,一个科学、技术、工业、音乐和其它文化艺术的综合体。当我们头几回看屈米的规划设计方案时,真是不知所云。正像德里达所说,它给人一种“不稳定化,解构,裂变,并且首先是分离、间断、瓦解、分延(德里达自造的新词)”和“异质建筑,互相干扰,非一致的”的感觉。面对着这个离经叛道的设计,人们很少能一下子用好或坏、有劲或无聊等来表明自己的判断。
至于屈米本人,他对自己的作品是这样描述(只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在解构建筑师看来,建筑师对自己的建筑作品进行解释,全属多余)的。他认为,今天,“公园”这个词已失去了它通用的含义,它不再涉及一个固定的绝对,也不涉及理想。他反对历史上把建筑定义为经济、结构、用途和形式的“和谐组合”,而提倡不和谐的“疯狂”:冲突胜过合成,片断胜过统一,疯狂的游戏胜过谨慎的安排。他还描述道,他的“公园”是无始无终的,它不是今天的文化环境对人们作出的提示。他在设计中运用了重复、变形、碎裂、叠置等手法,以点、线、面的解构、组合和重叠“叠印”成公园的总平面,一条数公里长的形式和结构都十分奇特的蛇形游廊(“拉开的电影胶片”)把被他称为“疯狂”物的三十多幢“建筑”(浴室、咖啡室、餐室等,有的则无明确用途)连接起来,极力渲染一种“反”建筑、“非”建筑、“非功能”、“非理性”、“反记忆”的环境气氛。
解构建筑还常常被做成没有建成的样子,“随时都有新事物发生”。美国一位解构主义建筑师,F·盖里,就对着自己的设计说:我喜欢建筑的“正在进行(施工)的样子,而不是它的大功告成。”“如果你想在秩序、结构完整和美的形式的定义上来理解我的作品,你就完全错了。”建筑变成了对正常生活、对普通公众的嘲笑和愚弄。这种情绪,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和思想的支离破碎现象,但社会财富的丰裕却为这种“疯狂”、浪费和变态心理,为这些“玩建筑”的花花公子们,提供了物质的可能性。
四
对上述几个不同主义的建筑作品及其所显示的西方建筑艺术的色彩斑驳的世界有所了解之后,回头看看我们国内建筑界,的确会感到平静和单纯得多。它仍处于一种自我满足、自我完善的状态中。
八十年代,我国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建筑师在过去十年中所作的努力所取得的进展,为我国历史上所仅见。坚持创造中国现代建筑和坚持继承、发扬传统形式的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设计实践,虽然似乎不打算分成两派,但已表现了极为不同的创作态度和艺术追求。近年来,他们都推出了同样被政府、被群众所接受的作品。
在这次被选出的十个“八十年代中国建筑艺术优秀作品”中,一个是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一个是曲阜阙里宾舍。是否都称之为“优秀作品”?似乎称为“名建筑”更为妥当。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一种巧合:上述两个建筑在一九八六年官方评奖中,同被评为优秀建筑创作一等奖。这两个艺术形象和艺术趣味大相径庭的作品,各占各的理,却同样为政府和民众所赏识。真如民谚所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社会对建筑艺术的宽容,人们艺术爱好的多样性及对建筑师辛勤劳动的尊重。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设计者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创新意识。它是在我国出现的还不多的,相当“纯正”的一个现代派/国际式的作品。它的成功表明了当代中国建筑师在运用现代原则和手法时的信心、才能和技巧。
展览中心由四个方盒子组成。作者着墨之处有二,全是现代笔法。第一,在每两个方盒子之间插入连接体,把四个方盒子组成一个整体。连接体处安排了展馆的入口和门厅。入口处有突出的拱门门廊。拱门上空飞架圆弧圆额枋。圆滑的曲线和浓重的阴影在建筑群体上反复出现,产生了强烈的整体感和韵律感。第二,每个方盒子的四角都被削去一部分,安排了简单划一的玻璃角窗。大墙上部稍为外突的一溜高窗和下部内凹的一组低窗,使大墙上出现了明显的虚实和光影变化。这样做之后,就大大冲淡了一般混凝土方盒子的呆板僵直、平淡乏味之感。总之,整个建筑群体构图干净利索,表现了一种欢快、清新、朝气勃勃的气氛。展览中心的创作过程和建筑形象告诉我们,我国现代建筑远远未走到自己的“尽端”,而是尚在它的“开端”徘徊。但是,它的成功,它在全国、全北京的各种评比、评选中,所曾获得的十一次奖赏和荣誉称号,确实为我国公众补上了现代主义这一课,为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争到了一个好名声。
曲阜阙里宾舍,却有着一副古老和沉闷的表情。它是一位老建筑师的精心之作。与某些矫揉造作、粗制滥造的,同样是所谓“传统形式”的建筑相比,阙里宾舍是一个认真、严肃、完整的作品。其最大特色,是与孔庙、孔府两个古建筑群近似和协调。它的主体的十字脊重檐瓦顶,是照着孔庙杏坛的玻璃瓦顶的形状复制的,现代钢筋混凝土壳体上,以手工作业方式铺设了瓦面。檐下的密集的椽子,是用混凝土塑造的。用烦琐手工作业来掩盖先进的结构形式,用木匠的做木头椽子的手艺来对付混凝土,当然不会是什么“革新”。在这里,新的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等充当了复古主义的奴仆,因材制宜、材尽其用的“优秀传统”,倒是被遗忘殆尽。然而,按照设计者的原意,这种行状却被称为“以优秀传统为出发点,进行革新”,并将它作为一种创作指导思想在一九八五年冬天的建筑创作座谈会(广州)上提出,继而又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拒绝了别人对它的异议和批评。
五
但是,对展览中心还只是赞扬现代意识和创新意识,对阙里宾舍还只是评析其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已经很不够,很不够了。因为,当我们接下来作进一步的考察和思索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两个建筑艺术上属于不同时代、却同是当代中国第一流的建筑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却表露着某些相似的思想素质和相似的弱点、缺陷。
了解它们的创作过程的人们都清楚,无论是中年建筑师柴裴义先生或是著名老建筑师戴念慈先生,他们在各自的客观条件和时机分别设计自己的作品时,都享有相当充分的“创作自由”,能够不受干扰地完成自己的艺术构思,采用自己所喜爱的艺术形式。可是,他们却都选择了“模仿”而不是“创造”,平坦而不是艰辛的道路。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建筑的“模仿”,还来不及溶进自己的创造和中国老百姓的希望和憧憬。一个是对中国古典建筑的“抄袭”,把“优秀传统”局限在僵化的形式之中。样板是现成的,手法也是现成的。——我们的建筑师们,仍然是在较低的水平上,各自重复着洋人的或古人的动作。没有形式上的探索,没有理论上的突破,没有属于建筑师“自己”的新的建树。这种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建筑创作,存在着一种惯性和惰性,还没有形成自我超越的能力;我们的建筑思想和理论,仍然是那样干枯和沉寂,还没有可能为我们的创作,提供必要的源泉和养料。因此,在我们这个战线上,还只有建设工作的热闹、兴旺,而没有创作上的真正的持久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