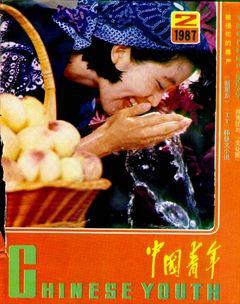田野(小说)
一
六月的中午,湘北农村奇热。天空瞥不着飞鸟,草丛里听不见虫叫。山上的树叶都挽成了小卷,稻田里的水也被蒸得发出“吸——吸”声。
我佝着纤瘦的身子,两条麻杆似的腿埋在发烫的稻田里。左手分着秧,右手急急地往下栽着,按照四六尺寸,横竖对巷的规定,不一会就栽掉了一行。然后坐在田坎上一边休息一边等着后面的伙伴。无意间瞥了一眼被汗水浸湿而又紧粘在胸前的衬衫,使我大吃一惊,一排排肋骨,似乎要把胸脯一层腊黄的皮帘顶破,弹出来找找我这个虐待了它们的“仇人”算算帐。吃惊之余,心下也觉得几分安慰;想,到大队卫生所找找卫生员,递上两支“经济”烟。再凭着这些“条条杠杠”搞一张病退回城的证明。心中打着小九九,不免还有几分坦然。
“喂,发什么愣?”
有人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一时反应过来,心中好生恼怒。你凭什么资格打我?都是一同下乡的,在学校我还是班长呢!不过我没有发怒,细细斟酌,觉得自身好笑,大白天坐在田边做梦了。我双手撑地,稍一用劲,几十斤重的身架就跷了起来。
“壮伢子——”
顺着声音望去,老队长肩着锄头扑扑踏踏向我跑来。心想,什么事?昨晚哥仨偷黄瓜发现了?我尽往最坏处想。等着老队长开口。老队长远远扔过来一支烟,我没接住,掉到田里马上湿了。老队长又扔过来一支,再给我把火点上,说:“太阳好毒!”我望着他点点头。老队长又说:“南面修堤,听说你有点文化,叫你去管管伙食。”
“管伙食?当司务长?”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对对,当司务长,是这个词儿。”老队长擤擤鼻涕,随手递过一张纸来。上面都明明白白写着,下面还有一个大红印章,不是假的。
二
她不高,很结实,我的被褥、脸盆、书,还有一些零碎用品,少说有五十斤,她轻轻松松就拎了起来。我跟着她进了房间,眼睛四下打量着。“你困这个铺。”她指指那个早已铺好了的床铺旁边的空铺。
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四壁没有窗子,黑乎乎的,弥漫着很浓重的泥土气味。地板很潮,溜溜的立不住脚。“还愣着干吗?”我听到她一声断喝,马上反过身来,一看,床铺好了。我说:“你真快。”“还快哩——”她斜睨了我一眼“今天你休息,明天帮我。这么远的路,一定累了!”我点点头,表示服从她,问道:“算盘有吗?”她愣愣地看着我:“要算盘干啥?”“算伙食帐呀,这你不懂?”我双手做着拨拉算盘的样子,心中陡然升起一种自高自大的念头。她还愣愣看着我,我也不解地望着她,双手还不停地玩着——拨算盘。“喝——!”她象是反应过来,随即又一阵好笑:“傻蛋傻蛋,你想当司务长,哼!早呐,乖乖帮老娘煮饭吧!”
“……煮饭?”我瞪大着眼睛,胸口憋了一下。她马上收敛笑容,不无嘲弄着说:“想当司务长?容易,买几条香烟去拍拍大队长。”
“什么?送香烟?放你娘的狗屁!”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别人的玩弄、亵渎,全身象火燎一样燥热。几步冲到铺前,胡乱收拢刚刚铺得整齐的草席,急急地把被子塞了进去,拽过一根草绳,猛猛地捆紧,大着嗓门对她喊:“我不干!”“你敢!”她叉开两条肥腿,双手紧贴在腰际上,大半片身子挡在门口。我上下打量着她的身坯,估估自己的身架,觉得敌不过她,当即改变态度说:“我不是冲你。”她瞪着眼,放大嗓门:“你们都是豆腐做的?都是龙身玉体呀?派来几个溜几个。算什么人?孬种。”
“谁是孬种?”“你,你们都是。”她手指戳到我鼻尖上,眼睛血红血红,俨然一头发怒的母老虎。
“你敢骂我?好,看谁是孬种?”我把背包重重掼在地下,横下心来,心想豁出去了。急急从身上拔出水果刀摆好架子。她双眼紧紧盯着刀尖,脸上没流露出半点胆怯。我跟着她转着圈儿,俨然擂台比武。“你来了。”她朝我背后打了一个手势,我慌忙转过身子,原来她卖了一个破绽。当我明白过来上了当时,早已被她紧紧箍住了。这会儿我的进攻能力全部崩溃了,一个十足的孬种。
三
我翻翻身子,床铺摇得咯咯响。闭上眼,想着心事。舐舐嘴唇,觉得有点干燥,使劲吞了一口唾沫,肚子又拖起长音来。连连紧紧裤带,尽量把肚皮捆紧。心想睡觉了就不会晓得饿了。
这时,房间里传来了她轻轻的脚步声:“把这碗面条吃完,填填肚。”
我没有动,尽量抑制着自己的馋涎。她以为我睡觉了,把碗轻轻放在靠我床铺边的桌面上,又拿着自己的扇子盖好,我又把裤带缩了一个孔,心想,等她出去了再吃不迟。等了一会,房间没有了声音,也觉得实在受不了,才爬了起来。探出头一看,惊呆了。她上身脱得精光,下面只穿一条花短裤。我吱唔着说:““你……你……”
“好看么!死鬼!”她撩开蚊帐钻了进去。
我赶忙缩进脑袋,心中直打鼓,脸上火燎燎的。全身血液滚烫烫的想往外溢。“你……你怎么会睡在这里。”我忘记了肚皮“官司”
“我怎么不能睡这里?”她轻悠悠地抛过来一句。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里是一个临时中转饭站。只认烧饭,一天三餐,直到开饭前一小时,自有汽车来收。饭站是没有别的地方睡的。也就是说,我和她睡在一个房间是必然的,无可非议的。
当晚想了很多,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妈妈那天送我上车时的情景:那一天,下着毛毛雨。我估计妈妈又会当着好多人哭。那时真怕,万一我也哭起来,怎么分手呢?然而,恰恰相反,妈妈没有哭,眼角也没潮,只是双眼有点枯竭、一种无穷饥饿的枯竭。她望着我,不动声色,那双老是挂着泪水的眼睛变得更深邃了,眼帘网了一层疲倦过度的人才有的黑圈。
车起动了,妈妈也跟上来了,她并没有加快脚步,而是估着车轮的速度不紧不慢地走过来的。末了,还是那几句不厌其烦的话:常写信回,常晒被子,好好干,多听老乡的……
朦朦胧胧听到几声喇叭叫。一觉醒来,已是日爬丈八时分。我吓了一跳,草草穿好衣服,趿着鞋子往外走,一下瞥见她背着我,坐在门槛上,慢悠悠地把书本翻得“哧哧”响。看看厨房,焦糊色的锅盖挂在墙上,大锅里冒着取掉饭后的热气,灶台抹得干干净净,石灰板照见人影。
“不洗脸?”她转过身来,手中拿着一张书中的插页。我仔细一看,糟糕,明明是我书本中的。“嘻嘻,怪好看的。”她扬着手中的图片给我看。如果说她发怒时是一只母老虎,那么此刻她更象一个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我苦笑了一下,觉得也无所谓,反正再也用不着了。农夫田为本么!顺手提来一桶凉水,冲刷了一番,好象清醒了许多,觉得比在稻田里舒服多了。自然有些兴奋,但不知该干什么,就坐下来吸烟。猛吸一口,劣烟厉害,加之我功夫甚浅,实实呛了一口,自然连眼泪鼻涕都带了下来,“伟”相确实狼狈,顾不了许多,撩袖便擦。她看着我咯咯笑了一阵,又问我:“老娘烧了面条,吃不?”我翻了她一眼,捻灭烟蒂,把剩余的放进口袋说:“你不要这么粗野。”她“哼”了一声,拍着胸脯说:“老娘这么粗,关你屁事。”我“咂咂嘴又说:“我可听不惯。”
“听不惯不听,谁叫你眼气。”她倏地站了起来,我连忙作好准备。
“啪”,她把一大碗面条重重搁在我面前,扭动着丰满的屁股到床铺上去了。
我望着干干的、凸凸的一大海碗面条,喜懵了,真想一口把它吞下去,放到胃里慢慢去消化。对于我这个吃野菜搅饭的男人来说,竟然连着要吃两餐面条,这将意味着什么呢?啊!上邪!我的“条条杠杠”的部位马上就会膨胀,纤巧的身材将会变得何等的威武,腊黄的皮帘也会是红白相间的呀!
吃完面条(我愿把吃改成吞)。觉得还不过瘾,双手捂着肚皮,慢慢揉着,直到稳稳地打了两个饱嗝,重又翻上来一点面条气味,又不失时机地吞了几口唾沫,相信喉节上下缩了几次后,才觉得惬意极了。
五
“你叫啥?”她问我,双手却急急地在我的书堆里面找画页。我移了移身子说:“别人都叫我壮伢子。”她连忙停下,呼地溜下床铺,双眼灼灼地看了我一会,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顺势推我一把,使我重重地摔倒在床上。她又一阵笑,说:“还壮伢子哩,真没屁用。”我想发气,可量量自己的手脚,觉得惭愧,只好自认倒霉。她毫不费力地把我拉了起来,挨着我坐下,双手轻轻地在印有图案的草编席子上摸着说:“你这个真好,不怕磨破衣服。”我看着她有滋有味地摸着,想起她晚上睡觉脱光衣服的情景。我说:“和你换?”“俺不换,不换,就是不换。”她连连摇头,好象是我想占她的便宜。我又说:“下一次回城,给你带一床好的。”她把食指含在嘴里,思索了一会说:“俺乡里人不配困洋货。”我连忙解释说:“不是洋货,是我们自己编的,上面的图案是艺术品。”她看着我,露出不大相信的目光。我仔细打量着她,觉得她每一处地方,每一个动作象是能独立生活的人,又更象需要在别人的保护下生活着。我指指她手中各种插页图案问:“这好看吗?”她“吧”了一下嘴巴,把手中的画页清做两起,然后指着那起有莲花、小鸟等图样的说:“这好看,我最喜欢。”我也觉得那种标语图案比不过,就说:“这都送给你,书本里面还有好多,只要你认真找。”她眨眨眼说:“我要找的,尽找好的。”我越发觉得她可爱了,又问她:“你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娇妹。”她回答了我,又倒到书本里去了,我拍了她身子一下,说:“怎么写的?你会写吗?写给我看看。”她停了下来,望了我一会说:“要我写?我不会呢?”我说:“没关系,不会我可以教你,你别看我瘦巴拉叽,肚里面‘糖多着呢!”炫耀地拍拍自己的肚皮,她把我的手拿过来,放在她的大腿上,翻过手掌,食指轻轻在我手心来回着,觉得痒酥酥的怪有味。我说:“我知道了,娇字是女乔娇,对吗?”她点点头。我又说:“娇字的解释是美好、可爱。”她看着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小巧的嘴唇嗫嚅了一阵,没有说出一句话,脸蛋尴尬得红红的,彤彤的,真娇!
作者简介姜立煌,男,1965年生于湘北农村,现为浙江某航空部队仓库保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