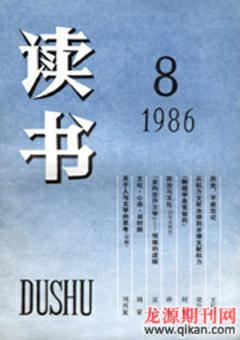诗的宏观与微观
李万庆
骆寒超是一位很有创造性思维的诗歌评论家,他的新著《中国现代诗歌论》尤其给我这种印象。这部书虽是由各自独立的诗人、流派和诗论共计九篇文章组成,但却在新诗发展的几个关节点上,概括了新诗的宏观规律并以意象为基本构成,以抒情方式为审美特征,对新诗作了微观的透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摈弃了诗歌评论对诗人、流派作孤立、静态分析的方法,而具有一种系统、整体和动态交叉比较的宏阔视野,但又力避脱离诗人和流派的具体意象构成及抒情方式,流入粗疏和虚玄之弊,达到诗的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在诗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结合中,使我最感新颖的独创是,作者在处于同一时期不同诗派相互排斥与渗透中,阐发出一种“平衡互补”的规律,而这种规律的发掘又是同对这个时期诗歌本体的微观的美感分析紧密相联的。在分析左联十年的诗歌创作时,作者认为以郭沫若、蒋光慈、殷夫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派诗歌强调了诗的革命现实内容,却把诗歌艺术的形象忽视了”;相反,以徐志摩、戴望舒为代表的“唯美派却规避了诗歌的革命现实内容,把诗歌艺术的形象奉若神明,当作追求的唯一目标”。这样,就发生了两个对立的诗派在革命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的各自侧重的追求与倾斜。由于这两派诗人世界观与审美理想的大相异趣,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排斥是明显不过的”;但是,“革命诗派和唯美诗派并不总相互排斥,而也在不断相互渗透,这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规律。”左联十年的诗歌就是这样在相互倾斜中既互相排斥与斗争着,又互相渗透与影响着;它们在倾斜中走向平衡,在互补中走向融合,构成本期诗歌的有机整体并汇流和迎来了抗战时期现实主义诗歌主潮的形成。然而作为现实主义诗歌主潮的三位代表诗人臧克家、艾青、田间,正是对上一时期这两个诗派不同片面性的扬弃。“他们都继承着革命诗派那种表现革命现实内容的精神;但在艺术风格上,又各自吸收了唯美诗派的抒情艺术:臧克家出自新月派,艾青出自象征派,而田间又颇受未来派的影响。”这一积极结果说明,革命诗派和唯美诗派由倾斜到平衡,由互斥到互补是推进本期新诗发展的内驱力。
新诗的发展不仅显出内容与形式之间趋于平衡和互补的倾向,而且也出现处于同时期不同诗派在诗美上的平衡和互补关系,《论晋察冀、七月、九叶三诗派及其交错关系》这一长达十万字的论文就是作者在这方面的力作。它不仅第一次将长期被有意忽视的我国四十年代三个主要诗派——晋察冀、七月、九叶放在一起分别勾勒了它们各自的形成和演变,在相互交叉的影响和比较中阐明了它们各自的创作内容及创作风格,而且采用了动态结构的方法对构成当时现实主义诗歌主潮鼎足而立的三派,从不同的诗美系统上作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从局部看,九叶诗派初期对诗的见解和追求与晋察冀、七月二诗派不同,“但是从四十年代诗坛整体出发来看,它们却处在一种互为补充的平衡关系中。”九叶诗派主张的“自觉超越”、“客观主义”,平衡和补充了晋察冀、七月二诗派在诗美追求上缺乏现实的深度、历史的广度以及纯主观抒情所造成的不节制不含蓄之弊;而晋察冀、七月二诗派的诗人们对时代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与强烈的激情又平衡补充了九叶诗派初期对暴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淡漠以及对现实斗争生活的游离等不良倾向。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根据自己对意象、形象和自由诗的理论建构,深入而细微地分析了这三个诗派各自不同的“感情素质”即审美特点,“这包括从抒情方式到形象结构,从形象结构到意象表现,从意象表现到自由体形式。”在感情类型上晋察冀、七月、九叶依次是:具体的客观型、抽象的主观型、抽象的客观型,与此相对应的抒情方式和意象构成则依次为直观型抒情方式明示型意象、综合型抒情方式拟喻型意象、隐喻型抒情方式隐喻型或拟喻型意象。作者还企图通过对各诗派的审美特征从美感诸因素的不同比配,由对诗美的直觉把握进而作出定量分析,这无疑也是一种可贵尝试。通过作者的研究,可以看到以现实主义自由诗为主体的我国四十年代的诗歌,是由“晋察冀诗人质实而明朗的写实风格,七月诗人郁勃而奔放的主情风格,九叶诗人婉约而朦胧的沉思风格”这三个诗美系统所构成,他们共处于一种互相倾斜的动态结构之中,在平衡与互补中使当时现实主义的诗美呈繁富多姿之态。作者的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作者对诗美的宏观和微观的综合把握,因而具有独到之处,值得人们注意。
(《中国现代诗歌论》,骆寒超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