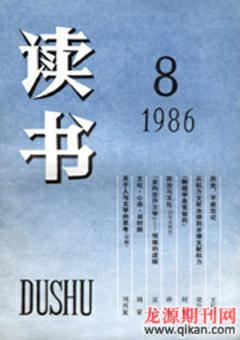历史,不能忘记
王依民
正是清明时节。悲壮的“四五”运动已过去整整十年了。在这样的时候,我读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年恶梦般的内乱,紧接着近十年步履维艰而又步伐坚定的前进,中华民族经过了一段奇特的历史。但是,十年内乱并不是虚幻的梦,奇特的历史自有它内在的规律。金春明的十六篇论文以深刻的反思和信实的史料说明着这一点。这部论文集比较深入地论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着重批判了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赞颂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未曾间断并且越来越坚决的正义斗争,即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顽强的抗争,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构成全书主要内容的这四点,阐释了这场恶梦的实质,也回答了我们何以能从梦魇中挣脱出来,并逐渐迈开我们沉重而坚实的前进步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一九八三年出版过林韦等人编著的《“四人帮”批判》,可以和这部书配合起来读。这部书是从党史的角度出发展开论析的,《“四人帮”批判》则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批判的,两书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在我有限的视野内,这两部书是近年来研究“文化大革命”较有分量的专著。
当然,从理论深度上看,这两部书还存在诸多不足,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也决不是几本书能够完成的。本书引述过胡耀邦同志的话,十年动乱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遭到多么大的灾难,受到多么大的损失,好好体会一下,是可以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来的(29页)。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特别是其中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更有责任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反省。“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几年中,我们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进行了批判,对拨乱反正,统一思想,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由于历史距离的过近,也由于我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这种批判还是不够彻底的。近年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批判逐渐深入,特别是把“文化大革命”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放到中国这一具体社会背景中研究,使思想界逐渐转到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国民心理的研究,并且很自然地进一步考察它与整个世界的冲突、整合,与现代文明的撞击、适应,从而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远源近流,更清醒地认识我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现实条件,更明智地制订和执行我们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我以为当前正在展开的中西文化大讨论的实质就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和现代化问题则是这场讨论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动机,而这正是不同于三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的深刻之处。几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破除传统中的封建主义因素。“五四”反封建斗争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这一历史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后来我们又在相当程度上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主义在新形势下的一次大爆发。这里谈到的两本专著还不能说对此作了充分的探讨。我们希望有人能吸收理论界的最新成果,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封建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影响;它与极左思想的联系;它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以及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怎样使“文化大革命”能够蔓延得如此之广、持续得如此之长;它是怎样被林彪、“四人帮”吸收、发展,并且利用它来促进愚昧、迷信,制造浩劫,等等。这不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及其远因的探讨,也是关系到改革、建设两个文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
胡耀邦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受“左”的思想毒害的问题(本书23页引述)。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我们经常听到或读到很多人谈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迫害、冲击,却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我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承担哪些政治或道德上的责任,至少很少有人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我们中的不少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的人民(包括在“文革”中曾经受到过冲击的人)——有的对“文革”前“左”的思潮的蔓延无动于衷或推波助澜,有的为“文化大革命”热血沸腾、奔走呼号过,我们曾经积极地或者消极地或者糊里糊涂地或者被迫地参加过“文化大革命”,游行,批判,揭发,“亮相”,甚至整人,抄家,武斗……至少,我们长时间的沉默过。我们当中固然产生了“四五”英雄,但也有出卖灵魂的人。不要忘记,在天安门广场执行对“四五”运动的镇压的人,也有很多是我们这种普通人。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更应该想想这一点,并时时引为鉴戒。当然就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但“文化大革命”和任何历史进程一样,决不是个别人的作品(参看本书12页)。我们承担这一份历史责任,丝毫不会减轻林彪、“四人帮”的罪责,面正是看到他们不仅把我们人民推到了灾难的痛苦之中,而且更严重的是毒害了我们的灵魂;我们承担这一份责任,正是对历史的进一步剖析,正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入把握与恰当估价,正是承担起使悲剧不再重演的崇高义务。过去,鲁迅先生曾经写出了一系列“看客”典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深刻地解剖了我们的民族劣根性;后来,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除了描写抗争和堕落以外,还以主要的笔墨描写了论陷区人民在日寇侵略时的忍耐、麻木、顺从,无可奈何甚至几乎习惯似地接受做亡国奴的命运,表达了老舍先生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以及构成这种民族性的历史、传统、文化、风俗等因素的深刻分析,着力解剖了其中的弱点。可惜的是,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以为这些仅仅属于旧时代的东西再也不会在中华民族文化一心理结构中存在了。包括老舍先生自己在内,我们以过于单纯的真诚和惊人的忍耐力,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批彭德怀”……等等运动,以致极左思想的狂潮日益膨胀而没有得到及时的、有力的遏止,终于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步,老舍先生也成了最早的牺牲品之一,鲁迅先生则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如果不重视、不彻底荡涤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当中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历史的代价也许会白白付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的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里反复地为自己当年的软弱而自责,在这位可敬的文学老人面前,我们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来正视自己的良心。刘宾雁在访问联邦德国后写了一篇题为《他们不愿忘记》的报告文学,其中写到六十年代的年青人向他们的父辈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纳粹统治时期,你们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应该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做了些什么?这个问题会使我们记住这段沉痛的历史,会使我们去探究悲剧的原因,会使我们为了不再出现悲剧而斗争、建设,会使我们毫无愧色地面对后代的子孙。
近几年来,有一些人曾多次提出对“文革”不要怨恨,无私心宽,要原谅错打儿子的母亲。在我看来,这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样做,会把一场有深刻历史原因的浩劫理解成一种偶然的失误;把党、国家和人民仅仅看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承受者,而造成十年内乱的原因自然就仅仅来自那么几个人;作为灾难承受者的一分子,以一种高尚的姿态来宣布宽恕,从而把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化为个人的恩怨,一笑了之。这种宽恕不但是无益的,而且是危险的。我们当然要严格区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与党、国家、人民的失误之间的本质区别,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不反省自己的失误。党中央已经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坦率承认并深入分析了党的工作失误,我们更有必要在党的领导下研究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并对那些至今还存在于党内、社会上、我们自身中的极左思想、封建思想和不正之风作不懈的斗争。这种批判、斗争决不是对党、国家、人民的“怨恨”,而是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封建主义的怨恨,对这一切我们决不宽恕。所以,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宽恕,是我们不能赞同的。至于象小说《绿化树》中那样庆幸能有机会经历苦难的历程,从具有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我个人以为这样的从肉体到灵魂的改造是有典型性的,但很不幸,主人公不是被改造成唯物主义者,而是被改造成一个愚昧的、教条的、顺从的、麻木的、有“耐力和刻苦精神”的愚民,是极左思想毒害的产物。文学是生活的写照。仅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肃清我们每个人灵魂中“左”的思想的毒害,是如何必要,又是如何艰巨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早已结束了。但它既然是历史之链的一个环节,就必将对现在和将来发生某些影响。我之所以要写下读了《“文化大革命”论析》以后产生的这些感想,就是想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忘掉它了事,而是要深入地剖析它的前因后果,研究它对现实的影响,把握它对未来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恩格斯所说的,以历史的进步补偿历史的灾难。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
(《“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