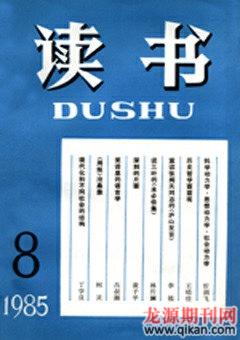访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韩南
骁 马
和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约好上午九点钟在社会科学院的小客厅谈一次。我准点到达时已见一位高个子,黄头发,背部微躬的外国客人站在门口和一位青年用中文交谈,讲话虽然慢一些,发音吐字却极标准。不用问,这一定是我要见的客人了。
坐下来之后,话题自然先落到韩南教授的专业上。美国较重要的大学都开设有东方或中国文化专业,其中总有四五个教授是专攻中国文学的。例如在哈佛,目前就有四位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其中两位研究古代文言文学,一位研究通俗方言文学,一位研究近现代文学。他们带的研究生并不多,因为学这个专业的不大好找工作,不少在中国文学方面取得博士学位的人也只能改行,到对中国有兴趣的公司里去谋职。为此,他们把研究生的人数限制到很低,每年大约只收三两个学生。与此同时,为本科学生开设的中国文化或文学课程却盛况空前,选课的人数总在二三百人。这里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大学的本科阶段注意了要避免学生过早地“单打一”,要求学文的学生一定要选几门自然科学课程,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一定要选几门文科的课。中国文化和文学课对各科的学生都表现出极大的吸引力。
韩南教授在哈佛大学是专攻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著有《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一九七三)和《中国的话本》(一九八一)和《鲁迅小说的技巧》(一九八一,已收入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
这几部书不论从体系还是论点上都是独具特色的。特别是《中国的话本》这一部书,到目前为止还是国外唯一的系统研究话本文学的专著,读后深为一位外国学者能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如此精到而折服。目前,上海和杭州的翻译工作者正在将这两部书译为中文。
谈到怎样搞起这个专业的,韩南教授竟是“半路出家”。做学生时,他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专修英国文学,获硕士学位。当时,他通过翻译读到了大量的中国古代诗歌,对中国文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重打旗鼓另开张,到伦敦大学专攻中国文学,从学士的本科课程一直读到获博士学位。从此他便开始了在中国通俗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造诣之高似可从下面这件事上看出一二。一九六二年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席位出缺,引起世界各国不少著名学者的关注,应聘者很多。结果是新西兰籍学者韩南得到了这个荣誉,受聘至今。而且,这次从中国回去后,他就要出任哈佛大学东方文化系的主任了。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韩南教授来中国的次数并不多,这次来只是他的第三次中国之行。每次到中国来,他都是泡在故纸堆里的时间多,很少能挤出时间观光游览。至今,他居然还没能偷闲到西安去看看呢!
韩南教授第一次来中国是一九五七年,由当时的对外文化联络会接待,住在北京船板胡同的一个小旅馆里。联络会为他联系和中国学者、教授会面,并为他在图书馆里搞研究创造条件。他住了八个月,写出一篇关于《金瓶梅》的论文,考证了《金瓶梅》书中各部分的真伪和材料的来源等问题。由《金瓶梅》我们自然就谈到了小说中的色情问题。韩南教授认为中国小说中色情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而且这里面往往有一个很有趣的模式:故事的开始是对色情的渲染,结果是因此受到的惩罚,似乎意在规劝,可是惩罚的部分往往绝不足以抵销渲染部分对人的吸引。结尾反映的是社会的传统和习俗,是为了把小说或故事装潢得更体面一些。不仅包含色情因素的小说是这样,其它小说也有类似的模式,即放纵——控制。例如《水浒》中反叛的部分造就了那么多活灵活现的人物,最后的招安部分似乎只是给全书安上了一条毫无生气的尾巴。《西游记》当然也是放纵的部分最引人入胜。韩南教授说,许多小说从模式上讲都可以做为道德教训来读,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个角度,那就大大地降低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关键的问题还是要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欣赏书的主体部分。当然,各类文学作品的质量很不一样,鱼龙混杂,也不可一概而论。
韩南教授第二次来华是一九八○年随一个代表团进行为时三周的访问。那时他刚刚写好《中国的话本》这部专著,有不少材料需要进行核对。于是他公私兼顾,挤时间干了不少自己的事情。查材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在文学资料的保存方面,并不是很理想的。遗憾的是,不少今天在中国找不到的资料,却可以在日本查找到。十七世纪时,中国有大批书籍出口到日本,藏在贵族的图书馆里。书籍登陆时日本的海关都有记录,从这里就可以查出书籍的去处。例如清朝文学家李渔的第一个故事集《无声戏》现在就只有在日本才能找到。李渔还有一部包括十八个故事的集子《连城壁》也只在日本才有全本,中国只是最近才在大连找到这个集子不完全的手抄本。
韩南教授这次到中国来是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客人,计划在四个月的逗留期间完成并充实一部有关李渔的专著。他说他之所以选择了李渔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李渔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难得的可以进行总体研究的作家,各方面的论述和作品都具有一致性,形成一套独特的理论和见解。他不打算把这部书仅仅写成传记性的著作,而是要在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基础上使著作具有更多的文学理论价值。不过,李渔的生平是很有特色的,因此这部书还是专辟一章集中探讨他的生平。例如,在西方人们常把李渔和莫里哀相比,因为他们都是剧作家,又都是自建剧团演戏,有第一手的经验。李渔自蓄家妓为文友和达官献艺是人尽皆知的。而且,在李渔的身上还有两个突出的侧面。一方面他有文人的清高,憎恶社会的不公;另一方面他又要穿梭走动于达官贵人之间,求得赞助。这部专著的主体是分别研究李渔的小说、戏曲和文章的章节。韩南教授认为这些文学体裁在李渔手下都有相互呼应的地方。比如说,不论在小说、戏曲还是文章中,作者的声音都要比其他作家明显。李渔是一个不甘于使自己的声音仅仅处于背景之中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往往有一个人物,戏剧中则是角色,文章中便是插话者,反映的正是李渔的声音,机智幽默,充满活力和喜剧色彩。越是喜剧性浓厚的作品,这个声音就越明显。在这一点上,李渔常常能使熟悉英美文学的人想起王尔德和肖伯纳。他们都是以机智著称,以戏剧见长。特别是李渔和王尔德,他们都很注意戏剧的美学效果,较少顾忌社会习俗的羁绊。
由李渔以及通俗文学在文学中的地位问题,我们谈起了今天常讲的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脱节的现象。韩南教授说古代的通俗文学当以话本或小说的书面形式出现时,已经成为一种沟通雅俗的中间形式。李渔的作品就有雅俗共赏的特点。这种文学上的中间潮流对整个社会文学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社会力图创造一统文学的倾向总是很强,对通俗文学或植根于通俗文学的中间文学总取或是不屑一顾,或要将其纳入高雅文学的模式之中的态度。其实,这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今天中国文学的中间潮流给人的感觉的确是不很丰富,大有发展的天地。古代通俗文学中的养料还多有可以汲取的地方。
最后,韩南教授对中国目前古典文学方面的学术情况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他觉得目前出版方面的情况是很喜人的,大批的书籍得以整理出版,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准备工作。五十年代郑振铎主持编辑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就是出版提高学术水平的一个例子。现在的情况使人感到是和中国三十年代以及五十年代书籍出版的好时光相同甚至更好的阶段。第二,比五十年代范围更广泛的考证研究有了长足的长进。大批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第三,与前两个方面相比较,文学评论工作则显得落后。原因之一可能是过多地要使文学成为政治和道德的工具,评《水浒》说《红楼》都曾走过极端。再有就是文艺理论的单薄。现代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浪潮接一个浪潮,让人目不暇接。虽然各个浪潮都有偏颇,却也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各个方面的认识。文学艺术本身是极其丰富的,总是要给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理论出难题。一个现代社会的文艺批评家应该有丰富的理论修养,根据不同的作家和作品,选择不同的评论角度。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就可以作为象征来读,因为作者就是把他作为象征来写的。但是如果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也作为象征来看,说她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之类,就有些牵强了。
韩南教授的意见自然使我想到他的治学态度。他关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著述,绝没有空口妄论的感觉。书中既有翔实的材料,又有变换自如的考察角度,读来很有兴味。而且,韩南教授从来不追逐“时髦”,又了解各种“时髦”,在扎扎实实的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难怪钱锺书先生要说,韩南教授是“老派学者,现在越来越稀罕了。”从这样一位外国学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方法和态度中,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些启示。
一九八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