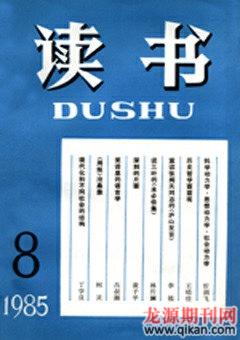科学动力学·思想动力学·社会动力学
忻剑飞
1
哲学与科学——人类智慧的产儿,常常象《旧约全书》中以撒和列伯加的孪生子:以扫和雅各,为争夺长子权而兄弟阋墙。当近代科学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哲学就以君临一切的姿态,裹挟了科学;而当科学开始以精密的态度审视以往种种哲学猜想时,它一方面正确地摒弃了旧的自然哲学,另一方面却又开始拒斥哲学……,这种现象时起时伏,绵延至今,并未绝迹,不少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在这里留下了令人遗憾的败绩,如黑格尔,如牛顿。
但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潮流,客观上却证实着恩格斯的论断:“各门科学在十八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形式,因此它从此便一方面和哲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马恩全集》第三卷第666—667页)而科学哲学的兴盛则为哲学与科学的联盟搭起了现实的桥。不管这座桥还有多少不尽完美之处,但它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等方面体现出的社会功能却愈益显著,越来越惹人注目。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出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在理论上把生产力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直接形态,即直接生产力;一种是一般形态,即一般生产力,科学就在一般生产力的意义上被包括在生产力之内。而科学又可以分为两种知识形态:一种是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知识,无疑它的物化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生产力;另一种是作为科学知识的结晶的科学方法,它涉及到科学成就的评价和选择,科学发现或发明的结构,因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更为深远。研究科学方法必须把重点放在科学知识的动态发展上,这就是科学动力学。所谓科学动力学,无非是以科学史和科学思维为对象,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哲学思考。当然,这种哲学思考不仅在研究内容和对象上,而且在思维形式和特征上,都离不开科学。科学与哲学的这种互相交融、紧密结合,产生了一门主要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纪的学科——科学哲学。
如此看来,说科学哲学不仅是科学动力学,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动力学,并不虚妄。正是在寻求社会发展动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科学动力学与社会动力学共有着一个出发点和归宿。
研究科学动力学,努力使之转化为社会动力学,这个任务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更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人们都说,中国政治化伦理化的哲学传统曾经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达,然而,一旦门户打开,这种哲学特性却也鼓舞了人们从新近输入的近代科学思想中寻找社会动力学的热情。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曾被人们认作最新的社会动力学。但事实很快证明,问题远非那么简单,于是而有了中国哲学界六十多年以前的那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情况复杂,以往总习惯于把它简单地视为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之间的内部争斗,近来又有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的作用,于是又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我倒觉得,不如把它主要地看作当时人们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一场大讨论,是人们寻求科学的社会动力学的一种表现,不过,那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开始大规模传播,这场讨论却置此不顾,加之中国并无发达的科学,世界上也还并无发达的科学哲学,所以就难免不了了之。半个世纪以后,由于教条地或者是歪曲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造成的恶果,由于新的事实和理论大量涌现,更由于人们寻求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现代化历程的需要和热情,许多中国人又重新思考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希望在理论和实践的活动中构建新的科学的社会动力学,除了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现象进行再研究(如:重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讨论,重建社会学等等),在理论上,人们大体上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审核我们以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发掘马克思思想中更富有预见力、生命力的东西,在新的阐释学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还原”;二是借鉴现代历史哲学,汤因比、克罗齐、结构主义等都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三是再一次与自然科学结盟,这次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结合,又引进了当代科学哲学,自然今非昔比。
所以,今天当我们听到有人尖锐地发问:“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并知道这个问题引起震动和反响的时候,我们无疑感受到了时代的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读到邱仁宗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一书,首先便在脑际浮现出“社会动力学”这个词,引出了上面关于哲学与科学分分合合的历史的感想。以下则试图从该书对科学哲学的阐述中获得对社会动力学的新的启示。
也许这并非出于主观臆想,因为作者在书的“序”中已明白地说明了科学哲学对于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意义,批评了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尚存在的重大弊病:“我们毕竟与外界隔离太久,对他们的了解很差。更重要的是现在哲学界有些人仍然喜欢作‘语录式批判。人家说些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甚至人家的主要著作都没有看,就根据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中摘出的几句话来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地加以‘批判。而有的杂志也乐意刊登这种未经研究的‘哲学研究文章。”开放地汲取外来文化,科学地开展学术研究,大胆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本身也属于社会动力学的问题。
当然,任何重大的社会现象总是世界性的。自从逻辑经验主义在新的科学水准上开始了科学与哲学的联姻(尽管,其中有些杰出人物主观上还在笼统地拒斥哲学,如赖欣巴哈),几十年来,科学哲学中一些最著名的代表,如Popper(波普尔),Kuhn(库恩),Lakatos(拉卡托斯)和Feyerabend(费耶阿本德)等无不喜欢同时谈谈哲学认识论,方法论,谈谈社会学、历史学甚至马克恩主义,表现出强烈地参与社会动力学的倾向。以致,一九七九年在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上,A·帕里加洛夫(Polikarov)专文阐述“支持哲学与科学相关联的十个论证”,并对未来作了这样的展望:“科学的现状将在数十年或更长时期内加以概括总结。在历史的归纳或重建的基础上(显然,这还是较不重视科学与社会相联系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提法——引者注),许多现在遮盖着这个基本过程的东西将作为细节或之字形的东西而得以减少,基本的观念、倾向、方法和结果将会出现,他们的方法论的和哲学的特点将会更为清楚地突出出来。”(《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论文集》第355页)
看来,科学与哲学的联盟还会加强,科学动力学的社会功能也还会加强。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其表现和特色是不同的罢了。
2
我认为,科学哲学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启示是最值得重视的,尤其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在提倡科学与民主,建设现代化的时代。
试择其要者,略述一二:
“人可以比大自然喊得更响”——切勿拘泥于经验没有一门科学可以完全脱离经验,然而,也没有一门科学是拘泥于经验事实的。拉卡托斯关于人比大自然强的口号,既是对科学家们创造性思维的礼赞也表现了科学哲学家们的共性。对哥白尼革命的纷纭众说,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归纳主义者认为哥白尼革命就在于发现了新事实并从事实中作出了正确概括;概率主义者则把它解释为相对于当时全部可得到的证据而言的结论;否证主义又用否证和判决性实验的观点看待它;约定论则认为哥白尼理论比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第159—160页)。所有这些解释,都有其局限性,但人类正是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推进了对事实的了解,增长了知识,甚至创造了新的理论、新的学科。当然,这不是提倡“唯我论”,“唯意志论”,而恰恰是基于对作为认识对象的经验事实的深刻了解。如所周知,现代量子物理学已告诉我们“对任何系统的状态的观察,都必须考虑到对这个系统的扰动”(《无数学的物理》),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证据受污染”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要想使认识有所前进,除了尽可能多地掌握客观材料之外,更关键的恐怕还在于发挥能动性,提出更有前途的假说来。这个问题颇有现实意义,尽管在前些年里,我们较多地看到了唯意志主义、教条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大施淫威的恶果,但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历史表象背后的东西,正是几千年封建主义禁锢下,小生产的狭隘经验论的思维方式衬托了某些“超人”的权力意志。另外,从社会科学研究上来看,忽视理论必须要有材料之外的结论,并用这种结论去组织材料,从新角度去分析材料,正是当前社会科学落后的症结之一,因为,照杜恒(Duhem)的说法,一些最深刻的科学理论具有“纠正事实”的作用(第128页)。所以,波普尔的口号应当时时记取:“大胆假说,严格检验”(第61页)。
“反对科学沙文主义”——追求多样化思维费耶阿本德的这一意见也与其他科学哲学家基本一致。如果说,强调创造性思维是对人作为认识主体的讴歌,那么强调多样化思维则是把人的主体性认识特点贯彻到底——谁都有权发挥思想的主体性,但谁也不能垄断它。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沙文主义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一部科学哲学史大体上却是愈来愈坚决地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的。从“现代历史学派的鼻祖”惠威尔(Whewell)的关于科学发展的支流—江河模式,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归化论的累积主义,都反对了科学沙文主义的理论永恒性。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库恩的常态和革命的双相观,都否定了科学沙文主义的权威的绝对性。而拉卡托斯关于各种理论竞争和并存(包括对已退化的理论的宽容)的研究纲领,和费耶阿本德的无固定模式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则连科学沙文主义暂时的栖息之地也剥夺了。当然,他们(主要是历史主义一派)的科学发展观多少有些相对主义的缺陷,然而,近年新起的夏皮尔(P.Shapere)和萨普(F.Suppe)的科学实在论(这一派邱著未曾涉及,不免是一个缺憾),尽管在积极纠正历史主义一派的相对主义,但同样与科学沙文主义格格不入(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多样化思维在今天中国社会的极端必要性,似乎无须多加论证了。值得一提的倒是这样一个令人汗颜的事实:费耶阿本德在讽刺只允许一种模式的传统的科学教育时,竟以中国女人的小脚为喻。“三寸金莲”早成了历史陈迹,但大一统的僵硬性会不会再成为新的历史笑柄呢?
“逆规则”——来一点反向思维所谓“逆规则”,即要求我们采用和阐发与已被充分确证的理论和充分证实的事实相矛盾的假说,也就是要我们按反归纳法行事。这合理吗?费耶阿本德对此作了回答(第178—179页)。逆规则包括两条:关于提出与公认的、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致的假说的逆规则,是建筑于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之上的——只有借助于另一个不相容的理论,才能发掘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这是否有点象我们今天所说的“先立后破”呢?)。另一条是关于提出与观察、事实和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假说的逆规则,其根据是:没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是与在它周围内的所有已知事实一致的(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证据受污染相似)。很明显,就思维方式而言,“逆规则”启示我们要来一点反向思维,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要有一点怀疑常识(包括理论和事实)的勇气,二是要懂得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常识往往蒙蔽人,如最近看到《新民晚报》一篇短文,说世界上本无狐狸,只有分别叫狐和狸的动物,可见我们的许多常识是大可怀疑的。而中国画与西洋画截然相反的透视法也只不过是无数相反相成事物之一例。尽管如此,种种惰性和惯性毕竟太强大,以致我们必得常常提醒自己和别人:来一下“反弹琵琶”,如何?
“格式塔转换”——调整思维的目标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充满了调整思维目标的事例。人们今天对休谟和康德的重视,从某种角度讲,也在于他们俩人一个从消极的意义上(怀疑主义,提出归纳问题),另一个从积极的意义上(反躬自问,提出人的认识能力问题),转换了传统哲学和科学思维的问题。科学哲学史表明,这种转换常常是革命性的,开拓性的。如果说,休谟的怀疑主义对弗·培根(F.Bacon)以来的证明主义是一个格式塔式转换的预兆,那么波普尔的否证主义,把对理论的证明问题转向理论的发现问题,则是科学哲学史中的重要一举。显然,它比卡尔纳普(Carnap)等的新证明主义更高明些,因为它拓宽了思维空间,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尽管也有可观的成就,如对概率问题的研究,但由于走的是原来的思维道路,因而路子变窄了。意味深长的是库恩把科学发展与格式塔心理学与皮亚杰(J.Piaget)发生认识论联系起来,从而增加了这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我们今天不也常常面临这种状况吗?一些或者只具有常识意义的命题,或者毫无现实感的命题充斥于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对于这种学术研究,谁都有正当理由去怀疑它的信息量和意义,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过多地去理会和指责为好,库恩认为对旧范型、旧的心理定势的执拗是科学革命中的正常现象,关键是对于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尤其是青年理论工作者,应当鞭策和激励他们:“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与问题有关的真理才与科学有关”——正确引入价值观价值论在科学哲学中占有相当地位,科学哲学中讨论的分界问题、意义问题,研究科学成就的评价和选择问题,都与价值论有关。波普尔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而摒弃“所有的桌子都是桌子”、“1+1=2”这样的真理(我想,也包括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些象牙之塔中的理论),这种价值观是积极的。更为难得的是这种价值观还体现了思维方法中的宽容原则,即对一些看来属于片面的、极端的但毕竟是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宽容。被称为“科学哲学界的怪杰”的费耶阿本德就是一个善于独辟蹊径,启迪思路的人,但他又的的确确是有不少片面性和极端性的。如果没有宽容,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把提出问题看作是一种极大的价值的观念,费耶阿本德就一定会陷入劈头盖脑的“大批判”之中。问题的现实性还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提倡了几千年“中庸”之道的国度,宣传波普关于理论的可否证度与逻辑概率的反比关系的见解,并使之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将有极大的意义。否则,可以想象,面对着“明天这里天下雨”与“明天这里天下雨或不下雨”这样两个陈述(第50页),中庸思想熏陶下的人们一定会选择后者,尽管这种模棱两可的“预言”,信息量只等于零(可否证度也等于零),而逻辑概率却等于1(因而是百分之百地正确的)。襄王枕上原无梦,莫看阳台一片云!
3
爱因斯坦十分推崇新方法,但他更重视人类精神的作用,他说过,在一切方法背后,如果没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它们到头来不过是笨拙的工具而已。
所以,这里还想谈谈科学动力学及其创造者们的精神。主要是:批判和开拓精神;追求科学知识一体化的精神。因为,这两种精神对我们今天探求科学的社会动力学关系甚大。
批判和开拓同属于人类最本质的精神的系列。波普有一个著名的论题:“从阿米巴到Einstein只是一步。”说它是一个论题,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句表明人类根本特性的格言式的话,而且是以新的生物进化理论为依据,又以人类的伟大实践为证明的。波普认为,作为单细胞原生动物的阿米巴和爱因斯坦所差的一步在于:虽然两者都在进行排除错误的“自然选择”,但阿米巴不是理性的,“不喜欢犯错误,不喜欢承认错误,结果它与错误一起死亡”(第61页)。而爱因斯坦则不然,他提出相对论时,就声明了在什么条件下他的理论就可被证明是错误的,并准备放弃它。所以,波普所认为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既批判别人,也批判自己,又接受别人批判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又必然导致开拓精神,开拓精神也与新的生物进化论相联系,同样为人类实践所验证。波普认为,宇宙或宇宙的进化是有创造性的,而随着人的出现,宇宙的创造性变得明显了,最有力的证据是人类已创造出一个新的客观世界——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波普名之曰“世界3”。
对于批判精神和开拓精神的提法,我们并不陌生。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科学动力学的帮助,以便将这种精神与科学,也与哲学联系起来,并付诸实践。在此,波普的理论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说明。问题还在于人类并没有都达到了爱因斯坦的境界,一个大活人却只拥有阿米巴的进化能力的情况还并不罕见。所以,波普声明,他所引证的都是在“英雄意义”上的科学史的创造者,“他们的生活是由大胆的思想组成的”(第67页)。
追求科学知识一体化的精神乃是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时下,人们很喜欢谈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统一的问题,并尝试着做一些互相介绍和引进的工作,或者客串另一领域遨游一番,留下一些新鲜的足迹。科学哲学家们也不乏这样的兴趣。波普兼有历史哲学家的身份,他用他的“猜测一试错”法否定了历史规律陈述的可验证性;库恩将他的“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作比较,得出两者大体相同的结论;拉卡托斯用他的“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来解释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费耶阿本德甚至直接引用列宁在《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关于实践比理论、方法更丰富的话来证明他的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当然,这些尝试性的工作总不免带有局限性,甚至明显的荒谬性。所以,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倒是科学哲学为知识一体化的基础所提供的独特的证明。说它独特,是因为科学动力学中关于知识一体化的倾向,常常是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影响这一面体现出来的,这恰好弥补了当前人们往往只从另一相反方向来谈论知识一体化问题的不足。比如:波普关于科学始于神话的观点,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始于非理性的“激情”或“爱好”的观点,可以看作知识发生学意义上的证明。库恩关于社会的某种需要引起常规科学的危机,关于世界观决定对范型的选择的观点,则是知识发展观意义上的证明。而科学哲学中的主流派——历史主义,显然在方法论上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具有共通性。此外,科学哲学注重讨论认识论,引入价值观,都可以从知识一体化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确,知识一体化是一种双向的趋势,列宁就呼吁过,不要让幻想为诗人们独占了。
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一书中,作者专辟两节,叙述了“理论动力学”和“思想社会学”(第88页,第94页)对于库恩科学哲学观的影响,随之,作者又说明库恩的理论又着着实实地构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诸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冲击波”。可见,在科学动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之间,思想动力学是极重要的媒介。本文旨在发掘科学动力学对社会动力学的影响,然却把主要笔墨化在科学动力学对哲学、对人类的思维方法,对人类精神等思想动力学的影响上,其源盖出于此。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邱仁宗编著,知识出版社(沪)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版,0.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