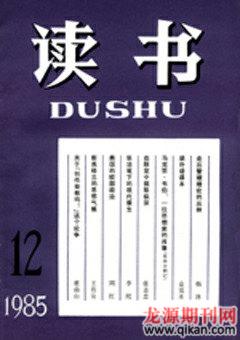《三位苏联女诗人诗集》
徐海昕
美国最近出版了三位苏联女诗人的诗集,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苏联一个时期内诗歌的一些情况,也看到海外对苏联现代诗歌的兴趣所在。这三位女诗人是:安娜·阿赫玛托娃(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玛丽娜·兹魏塔耶娃(一八九二——一九四一)和伊莎白·阿卡杜丽娜(一九三七—— )。她们的生涯由于苏联历史上的特定原因,都带有悲剧色彩。
阿赫玛托娃是和马雅可夫斯基同辈的诗人。如一位评论家所说:“阿赫玛托娃笼在寂静中,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倾诉;马雅可夫斯基则如同千声齐唤的广场。”她不同于受象征主义或受未来主义影响的俄国诗人,善于细致地写具有形体和质感的事物。但是,阿赫玛托娃的诗一度被斥为是狭小的个人天地,是“堕落并且有害青年的”。在一九五八年恢复名誉之前,她一直处于一种精神上遭到软禁的状况:作品不能发表,信件和电话被检查,就连她丈夫也要把她的诗烧掉。从诗集中所收的十几首诗中,不难看出诗人的孤寂。她和外界相通的窗户不是被遮挡,就是看不到生气。“我为窗外射来的光祈祷。/苍白瘦弱的直射。/我从早晨起就无话可说,我的心/裂成了两半。”“枕头的两面都热了。/第二根蜡烛/又燃尽。乌鸦的叫声/漫长。/一整夜没有入睡。想做梦/已经太晚……/难忍的是看/白窗户上遮着白窗帘!/“喂!”
当然,孤寂已超越了阿赫玛托娃的个人遭遇,成了她的诗的风格和主题。她的情感总是那么静悄悄的:“银色的垂柳点触/九月的清水。/我的影子从逝去中浮起/无声地走来。”而且,她以为人和人之间可以很亲密,但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秘密的地方/任何感情也无法穿透,/即便嘴唇在可怕的沉寂中相触,/任凭爱把心象纸一样撕碎。”她的孤寂和人际交流的困难连在了一起。
兹魏塔耶娃也是上述那个时代的人,但似乎并不介入任何诗派。她有象马雅可夫斯基的地方,如辞令;也有不象的地方,如动词的省略和口语化的程度(这一点又和阿赫玛托娃近似)。她长于用极富有感情的口语写催人泪下的经历,也可以用优雅流畅的风格写民间传说和童话题材。兹魏塔耶娃的诗才是多方面的,从一九一○年就开始出版诗集。但是,在一九二八年出版了《苏联身后》这本诗集以后,她便在诗坛上销声匿迹了。一直到六十年代苏联读者才重又读到她的诗集,读到这位已不在人世的女诗人的悲惨遭遇。
兹魏塔耶娃一九二二年随丈夫,一个白军军官,迁居国外,先住布拉格,后又到巴黎。在国外,由于俄国移民纷纷传说她丈夫是苏维埃政权安插来的人,她一直生活在一种遭冷遇的隔绝之中。她思念故土:“思乡!那样的疲惫/我已饱尝!/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孤独!”“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一所房子,/并不觉得是自己的,就象进工棚、医院。”一九三九年她回到祖国,却发现丈夫已被作为反革命处决了,女儿也关进了集中营。因为是从国外回来的,过去的朋友谁也不敢和她来往。她本人最终也被送到偏远的农村,一度找到工作又很快被辞退。在绝望中她于一九四一年上吊自杀了。
兹魏塔耶娃的诗却流传了下来。原因大致是倾注了心血的诗,总要结出果实。请读读她这首题为《我打开我的血管》的诗:“我打开我的血管:止不住,/无法修复,生命喷射出来——/赶快用盆碗接住!/每个碗都太浅,/每个盆都太平。//从地上渗进/黑色的土养育丛生的芦苇,/无可救药,止不住,/莫说修复——芦笛喷出诗。”这支用血养育的芦笛,还在读者的心田中喷射着诗。
阿卡杜丽娜是晚辈诗人,身上却带着前两位诗人的影子:象阿赫玛托娃,她善于用有趣而新颖的手法写实实在在的物;象兹魏塔耶娃,她的诗句常使人感到是拢在韵律里的歇斯底里。她的诗句中也有受压抑的影子。毕竟她曾因为脱离政治而被开除出高尔基文学院厂她因此只能以翻译家的身份加入作协;她一九六二年发表的第一本诗集《弦》被指斥为太接近阿赫玛托娃颓废的诗歌。她并没有被禁止写诗,却常常有欲歌不能的感觉:“唱啊!——雪花、绝壁/和树丛中的无数张嘴在求我。/我大喊却没有声音,/只有一团雾离开我的嘴,缭绕唇边。”
尽管如此,她还是唱了。她喜欢写冬天:“冬天对我的姿式,/经久的寒气刺骨。/冬天的气候中却有/治病的药。//不然为什么/我毫无戒心的病/会从黑暗和病痛中/倏地向它伸出双手?”她在溪边的歌也很代表她的风格:“在乡间人们叫它黑溪。/真不知是谁想起了这个名字。/象所有的溪,它是淘气的机灵鬼,/清彻得透明。//罗圈腿的鸭子哼哼着/把羽毛丢在水里。/溅了一身水的勿忘我花簇在溪边,/要比水流抛起的蓝色浪花。//这溪水对我一定别有意味,/因为它映出挂了灰的牛蒡,/一棵笔直的白桦,一座黄色的小山/——我故土的面貌。//这溪水熟练地冲过明亮的卵石,/汇进奥卡河。/我将怀念黑溪,/当它变成宽阔的黑海。”
(Three Russian Women Poets,trns.&ed.by Mary Maddock,The Cros-sing Press,NY,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