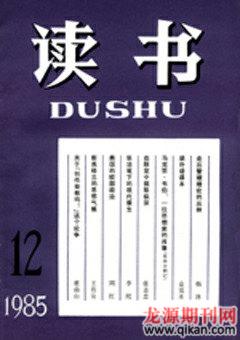罗淑和她的《生人妻》
沙 汀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在读到《生人妻》时,作者朴素简炼的风格,就把我吸引住了。仿佛自己在文学创作道路上遇见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同伴。当然,主要是因为她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使我感到亲切。虽然我是川西北人,罗淑生长于川南沱江流域,语言风习却有不少共同地方。而且,她不象我,很少使用冷僻的方言俚语。
最近,罗淑的故乡简阳各界人士,愈益感觉他们县里有这样一位曾经用她的笔描绘过本地自然风物,人情世态,而且对劳动人民倾注了深厚同情的出众的作家,是值得自豪的,决定在县文化宫内创立一个罗淑纪念室。这个信息给我带来很多感想,因为我曾经赞赏过她的作品,痛惜过她厄于短年。
尽管我和罗淑是同时代人,又是大同乡,“八·一三”事件前后且都住在上海,但是,由于当日彼此都生活在中外反动派统治下,行动不便,见面不多,对她本人印象不深,更不确切知道她的经历。最近,读了两三篇悼念她和追述她的身世的文章,对她在创作上起步之高和所取得的成就,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同时更加痛惜她走得太早了。
“文如其人”,她的文风也正同她的品格一样,“不露锋芒,热情蕴藏在温厚的外表下”,“思绪十分周到,话语简单而有力量。”一位和她两夫妇私交深厚的老作家还就其所知告诉我们,“许多人说她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却少有人知道她是社会革命的斗士。”接着还举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实例。而我这里只想借这些论断来说明罗淑在创作上的成就绝非偶然。
我是三十年代初开始搞创作的。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在一位前辈提示下,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这才转而反映我比较熟悉的川西北小城镇和农村的现实生活。而和《生人妻》一类作品相比,我却不免感到自己在题材上略逊一筹,因为我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龚老法团和丁跛公一类角色身上了。当然,就社会效果说,这也未可厚非,同时我也写过《一个秋天晚上》和《呼嚎》一类作品。这种差别也和各人的气质、修养、经历有关,实在难于一致。也不必强求一致。
一位同志前几年在一次通信中告诉我,在读到我有的作品时,对于其中人物的遭遇感到颤栗,而我却写得那么冷静!其实,在我重读《生人妻》时,也有同样感觉。虽然回味并不怎么一样。而在风格的特点上,罗淑并不依靠自己出头露面呐喊、呼吁和大发议论来鼓动读者,主要是用人物本身的言行和内心活动获致高度艺术效果。就拿胡大家派人来接“人”那天夜里,两位即将分离的夫妇的一两个场景来说吧,我相信,即便在今天,读来也不能不感到十分压抑。
那位妇女忍不住痛骂把自己嫁掉的丈夫:“你狼心狗肺,全不要良心的呀!”而丈夫在沉默一阵后爆炸似地吼道:“我,我未必不是娘养的!我犯了什么王法?我该受这活罪?”这已经足够教人感觉得难受了!而接着,在银发簪问题上更进一步表现了彼此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深情厚意,同时互相理解所有一切极不正常的变化,不是出于本意,而是来自穷困。特别叫人感动的是,妻子在忍痛离家时,走不多远,猛地又回过头喊道:“当家的呀!你那件汗衣洗了晾在桑树上,莫忘记收进来!”这喊声叫人久久不能平静。
出现在罗淑笔下那些被损害、被盘剥和被侮辱的农民还有盐工,都是“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皮里!”“借了发财人的帐,卖儿,卖女,卖骨头都得还”的穷光蛋。他们善良、纯朴,有时对于自己的遭际也深感不平,十分恼怒。当我读到《橘子》中阿全叔在收买水果的张贩子敲诈下,贱价卖掉自己几十棵橘树上的果实,而却不能让孙儿丁丁尝尝新时,深感他的内心多么痛苦!面对那个满脸奸笑的商人,他真想退还定钱:“那是我的!……我的东西!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然而,这些合情合理的愤激之言,只能在心里七拱八翘,最后,却不能不冲到笑嘻嘻捧着橘子的孙儿跟前,“颤声地说:放下!不许要,”因为他当时最需要的是钱。
由于贫困及其随之而来的被损害与被侮辱,以致在亲属之间出现极不正常、也就是背于常情事理的纠葛,在罗淑的作品中,可以说大都如此。《橘子》中祖孙、母子间的情节正是这样,而更叫人震撼的,却是《阿牛》这篇小说中阿牛母子间的关系。阿牛的父亲是熬盐工人,十多年前劳动时跌在盐锅里,被沸腾的盐水把生命吞食了。他是靠母亲开烟馆和做暗娼养活大的。故事开始时,阿牛已经二十岁了,而且恰好由赶车的升级为筒工,穿着一身新衣,准备前去接班。
按照常理,他应该很高兴,而他却忽然敏感到他的提升太不光彩。因为他联想起那个常到他家烧烟,同他娘关系暖昧,如今把他提升为筒工的何管事,于是不由得十分恼怒:“老狗……有一天要碰到我的手上!”一天深夜,他终于在家里碰上那个“老狗”了,正由娘陪伴着躺在床上抽烟。他大叫:“你给我滚出去!”……
我这样写,似乎是想介绍这篇小说的全部情节。不!我没有这种打算。只是因为这篇一气呵成,近万言的作品,太紧凑,太动人了,一想到它,三个主要人物就那么生动地浮现眼前,真有点情不自己。其实,其他短篇比如《刘嫂》、《贼》,又何尝不同样吸引人呢?我之赞同罗淑是一位社会革命斗士的论断,主要在于这次阅读她的作品,感觉它们全都燃烧着对于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对于剥削制度的憎恨。从她的经历看,有一点最值得注意。初到法国时,她的兄长曾经领她观光法国的城市,而她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的繁荣所眩惑,倒是认为法国“一样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见得比简阳好。”
“九·一八”事变后,尽管留在法国有利于继续钻研法国文学,但她终于不顾她的亲友的劝阻,毅然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因为怀孕,“八·一三”后又在敌军狂轰滥炸下随其亲属回转四川。当朋友们在炮火声中去车站送行,谈到几天来人民遭受的灾难时,她不是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不会死,也不该死”吗?!而她在分娩前写的两个短篇,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我想,我们不会死的,也不该死!”这两天,这简单朴素的语言一直在我耳边缭绕,她是多么想活下去,多么相信自己应该活下去呵!而刚到成都不久,产褥热却一下夺去了她的生命!
罗淑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几十年了,但她的作品并没有被人遗忘,希望能有人对这位有才华而又早逝的女作家进行更深入的生平和创作研究。
一九八五年二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