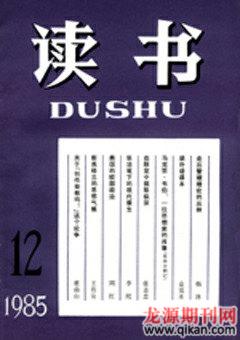民族意识
陈平原 黄子平 钱理群
正如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的那样,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现代民族的形成和崛起在世界范围内由西而东,这独具特色的一环曾分别体现为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德国古典哲学,十九世纪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则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激烈讨论和实践。文学始终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而展开的。就其基本特质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
钱理群:我们这一次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黄子平:好。上一次讲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汇入“世界文学”的大系统,这是一个横向座标;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有一个纵向座标,就是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历史位置。
陈平原:关于这个“历史位置”问题,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把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分成三大块,一块是“古代中国文学”,所谓“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落后的小生产经济与政治专制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宗法社会,与这样的政治、经济形态相适应,产生了古代中国文学。另一大块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文学”,所谓“现代中国”,是一个以经济高度现代化与政治高度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必然会产生一种崭新的现代中国文学。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文学,它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的文学进程。
黄子平:我很欣赏你用的“进程”这个概念,“进程”就是一种运动……
钱理群:对,应该用“动态”的观点来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陈平原:应该明确地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由古老的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时期,在历史的转折中,逐渐地建立起现代民族政治,现代民族经济,现代民族文化,实现整个民族的现代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逐渐形成中的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
钱理群:这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必然包含两个侧面:既是现代化的,又是民族化的。
黄子平:我想,更确切地说,是既是“世界文学化”的,又是“民族化”的,两者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在矛盾统一的运动过程中,实现文学的“现代化”。
钱理群:这样考察,就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横向座标与纵向座标联系起来了。
陈平原:你们刚才讲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世界化”(“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对立统一,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世界文学一体化与各民族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对立统一。一方面,每个民族不可能单独发展,热切地要求与世界文学取得共同语言,趋向共同的人类文化;一方面,每个民族为了自身的精神发展,又必然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既要追赶世界潮流,又要发扬民族特色,这几乎是二十世纪各国文学发展的共同课题。
黄子平:这个矛盾,反映在文化继承、吸收问题上,就是如何对待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问题。
钱理群:这可是一个困惑了整个世纪,不断引起争论,恐怕至今尚未结束的“古老”而“年轻”的文学课题……
陈平原:对,从本世纪初的夷夏之辨,到五四时代欧化与国粹之争,二十年代东西文化比较,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本位论,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五、六十年代以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为本论,七、八十年代“开放”与“封闭”之争以及当前的“寻根”运动……
钱理群:争论接连不断、欲罢不能,恐怕恰好说明:如何对待传统化与外来文化,如何处理世界文学一体化与各民族文学多样化(或者说文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矛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
黄子平:这是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座标(横向座标与纵向座标)所决定的基本矛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基本矛盾,这就是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具有世界性的。
钱理群:我还要补充一点,也正是这个矛盾推动着文学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似乎每一次论争都是以往论争的重复,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古老”的文学课题;实际上,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部分重现,反映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运动……
黄子平:如果以这些论争作为一条线索,结合创作实践,来考察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何在两种发展要求、倾向的对立统一中曲折前进的,这是很有意思的。陈平原:这个问题放到以后再去作“专论”吧。我们还是把讨论的题目集中在今天的中心:现代民族文学的形成与特征。
钱理群:(笑)平原,你不要着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个历史座标是互相联系的;即使我们讨论现代民族文学的形成、特征,也不能离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融这个总的文化背景。
黄子平:对,作为现代民族文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第一个辉煌高潮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多次文学变革运动最大的不同,就是五四所要实现的文学变革,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封闭体系内部实现的,而恰恰是以冲破这种封闭体系,击碎“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为其前提的,这样,它就必然要主要借助于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以西方文化为武器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陈平原:我最近正在研究从戊戌政变到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戊戌政变前后,梁启超他们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发动了文学改良运动,但却以失败告终,并没有、也不可能催生出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而五四文学革命却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梁启超们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模式。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封闭体系内部进行局部的调整,而反对根本的变革。
钱理群:你所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许正是许多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觉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不仅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洋务派与改良派所坚持(当然,洋务派与改良派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这里不作具体讨论),而且恐怕会成为贯串整个二十世纪的不容忽视的一种思潮。事实上,从五四以来就不断有人或直言不讳、或隐晦曲折地宣扬这种思想,也有的在五四时期曾经激烈地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又成为其积极吹鼓手的。我最近写了一篇论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文章,其中就谈到周作人在敌伪时期提出了以“儒家人文主义”为“大东亚文化”中心思想的口号;在他看来,在“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原始的儒家思想”里,就包含了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思想与民主思想,只是后来(汉以后,特别是宋以后),加进了法家成分,接受了佛、道影响,变成了酷儒与玄儒;因此,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改革只需要在传统文化封闭体系内部实行调整:恢复原始的儒家“人文主义”传统。
陈平原:按照周作人他们的逻辑,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周作人自己也在内)运用西方现代思想武器对以孔孟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至少也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与“偏颇”。
黄子平:这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唱的是“外国有的,中国古已有之”的“老调”,看样子,“老调”还是“唱不完”!
陈平原:张之洞当年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时,就特意点明:其作用是“不使偏废”,仿佛不偏不倚,很“全面”,很“辩证”。
钱理群:岂只张之洞!五四时期的“国粹派”不也是这样?学衡派诸公高唱“融贯中西”,就“全面”得很,“辩证”得很……
陈平原:相反,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倒显得十分的偏激,十分的绝对。鲁迅就宣布:“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甚至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钱理群:这种决绝态度、战斗风姿实在是令人神往的。老实说,如果没有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们那种“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就根本不可能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不可能击碎“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带来整个民族的觉醒,思想的解放,更谈不上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现代民族文学的诞生……
陈平原:至于说立论的“片面性”,恩格斯有一句话,“片面性是历史发展的必要形式。”子平,你不是在《读书》今年第八期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深刻的片面”?
黄子平:(笑而不言)……
钱理群:其实,五四文学革命对于传统文学在否定中也是有肯定的,并非一味的“全盘否定”。包括先驱者的发难文章,无论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寄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在高举批判、否定的旗帜时,也包含了对传统小说价值再发现的肯定性内容。
陈平原:五四以来,在整理和研究传统文化遗产取得最卓越成绩的,恰恰是运用西方思想文化武器,猛烈批判封建文化传统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参加者,而不是那些主张在传统文化体系内进行调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这个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黄子平: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再发现,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这样,它就提供了另外一个参照系;传统的东方文化体系正是在西方文化体系的比较、映照中,更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价值,而在单一的封闭体系中反而容易被忽略,以至否定。这就是说,两个系统的碰撞,常常获得新的价值。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更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个意义绝不能低估。而我们常常估计不足,比如对五四时期所输入的逻辑实证的思维方式、方法对推动我们民族理论思维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至今仍缺乏足够估计。
钱理群:应该说,在五四时期,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化的汲取是自觉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就比较复杂。今年《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期有一篇伍晓明论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文章,谈到五四时期传统文化的体系被打碎了,但传统思想因素“仍然深埋在现代作家的潜意识之中”,遇到西方文化的撞击,就会发生“原有潜能的激活和解放”,并在与西方文化的化合作用中逐渐形成“新的意识结构”,他举例说,郭沫若从小喜欢老庄思想,但并不理解,仅作为一种潜在意识存在,正是“西方泛神论和康德、叔本华的影响”,使郭沫若对老庄思想作出新的解释,并成为他“泛神论”思想和艺术无目的论的一个基础。我想,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有一定典型性的。
陈平原:大概在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才比较明确地提出来,成为现代作家自觉努力的方向。这以后的发展、变化,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还是不谈了罢?
黄子平:也好。我对你在开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过渡性质,以及它是一种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这两个论断很有兴趣,似乎有展开的必要。
钱理群: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对二十世纪民族的中心任务、时代精神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与把握。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从本世纪初,孙中山预言中国的大跃进,五四时期李大钊歌颂“青春”的中国,郭沫若描绘民族的“涅
黄子平:这在今天似乎已经是无须论证的“常识”,可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却偏偏在这个常识问题上认识不清,为此我们不得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陈平原:只有抓住这个时代中心,我们才能正确地说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只能是、并且必然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这个文学始终与民族的命运、与民族解放、振兴事业保持着天然的、血肉般的联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基本历史品格,无以摆脱的民族危机感产生于中国现代作家特有的忧患意识,并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
钱理群:这里还有一个中心环节,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性质。文学自觉地担负起了“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
黄子平:也许是过于沉重的责任……
钱理群:对,由于落后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极不发达,启蒙工具、渠道都过于缺乏,文学艺术常常成为唯一的启蒙手段,许多农民甚至连基本的历史知识都是从戏曲中获得的。这种情况既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优点,也带了一些历史的缺憾,而不论优点还是缺憾,都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特色与民族特色。
陈平原:在现代中国,很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都在关心着“国民性的改造”,试图用文学的武器唤起民族的觉醒,通过“干预灵魂”来“干预生活”,这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文学观念。
钱理群:当然,在不同倾向特别是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之间区别是存在的。分歧点主要集中在:用什么思想来启蒙?思想启蒙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的关系,前者是否能取代后者?等等。而在重视与强调文学“洗刷人心”、“再造民族灵魂”的启蒙作用这一基本点上,却有着相通之处。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强调作家在政治倾向上的分歧,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类最能显示作家政治倾向的文艺观念上的分歧,这是一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有它的必要性,而且在今后我们也不必有意地掩盖这种分歧。但是,应该承认,文艺观点也是多侧面、多层次的,作家们可以在一些文艺观点上存在分歧,在另一些文艺问题上又有共同之处,而且即使在“同”中也有“异”。而我们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重视与强调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启蒙作用这一基本点的一致性,恐怕是必要的。
陈平原:这与传统文学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有什么区别呢?
黄子平:中国现代作家强调文学的启蒙作用,是渗透着一种十分强烈的现代意识的,这包括重视人民的历史作用的现代民主思想,强调“人”的自我价值、自我觉醒的个性解放思想等等。这些在传统的文学教化作用里都不可能有的,有的恐怕倒是相反的封建专制思想、愚民政策等等。
钱理群:这就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民族的主体——人民大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突出优点。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贯串着一个中心主题:“改造民族灵魂”。形成了两大题材:知识分子题材——他们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农民题材——他们是民族的大多数,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这都是由文学的启蒙性质所决定,同时也最能显示文学与人民及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
黄子平:文学形式也受着文学启蒙性质的制约,并且产生了一些基本矛盾……
陈平原:这个问题留到以后再谈吧,我们还有专讲文学形式的题目呢。
黄子平:好吧,暂时不谈。不过,我还想谈一点——问题的另一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地承担起了对于它自身来说也许是过于沉重的思想启蒙任务,这就使它不能不加入了许多非文学的成份,不能不处处“照顾”我们民族过于低下的平均文化水平——这种情况,越是在历史转折时期越是严重,以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多次向一般的“宣传”工具方面摆动(例如,抗战初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等),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文学自身审美品格的发展……
陈平原: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整体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价值是高于审美价值的。
黄子平:大概如此吧。这与其说是一个弱点,不如说是一种特色。一切特色,都是一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都是历史老人的“产儿”,我们的责任只是面对历史,正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