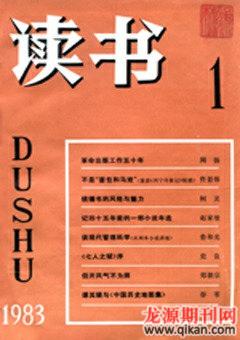两点感受
王同策
《读书》一九八二年第七期上发表的吕叔湘同志的《由苏东坡作<黠鼠赋>的年龄问题引起的》,读后颇觉高兴。
其原因之一是讲理。文章实事求是地批评了文风不正的现象。多少年来,虽然“摆事实,讲道理”的话不少人都知道,一个时期甚至喊得十分响亮,但与说话人的行动似乎毫不沾边。毛泽东同志有一段对“三个凡是”都要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的很有名的语录,那后面还有几句很重要的话却很少为人了解和重视:“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旧小说写公堂断案,常用一句描述语叫“不由分说”,幼年读书并未在意,只是在经历了多年来“左”的思想影响下的运动的“分析批判”之后,才逐渐体味到这四个字的真正内涵。俗语云:“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因为“不由分说”,更不用想说“清”,“有理”又可奈何?那时的所谓批判文章,也大都是深文周纳,锻炼人罪的恶霸腔调,打手架势。吕文的好,就好在讲理。,
原因之二是厚道。街头巷尾的妇姑勃溪,往往有所谓“得理不让人”的。这“得理”当然是好的,而因“得理”就气势咄咄地“不让人”,也是有伤厚道。“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自己写文章或编审他人的文章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确乎可以用出版物序跋中常用的那句话,是“在所难免”的。吕文对作者、编者的要求,只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避免他能够避免的错误”、“改正他能够改正的错误”。不苛求于人。当然,何者为能够,何者为不能够,其间标准是不象度量衡那样精确。不过,只要拿来具体问题,是可以加以判别的。即以这一期《读书》上《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面镜子》一文中的一段话为例:
在鲁迅的日记、书信中,还有一些有关《肖伯纳在上海》的史料线索足值钩沉,如《鲁迅日记》三月一日致台静农笺云:“我们集了上海各种议(疑衍一“论”字——笔者),以为一书,名之曰《肖伯纳在上海》,已付印,成后亦当寄上。”因鲁迅《序言》写于“二月二十八日灯下”,而此日即云:“已付印”,我估计即于今日(三月一日)发稿付排。
这段文字虽然不长,其中却至少有三处是错了而应予改正的:一、《鲁迅日记》显系《鲁迅书信》之误;二、“笔者”加注中的“衍”字显系“夺”字之误,校勘学术语中“衍”指多出的,“夺”才指脱漏;三、现在写文章指说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称为“今日”的,须将“今日(三月一日)”改为“三月一日当天”才对。
上述三点,对作者来说,应该是“能够避免”的,而对编者来说,更应该说是“能够改正”的,这恐怕不至有何歧义。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吕文中所说的“认真负责”、“认真阅读”这两个“认真”上。
对厚道的期望,理宜严肃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