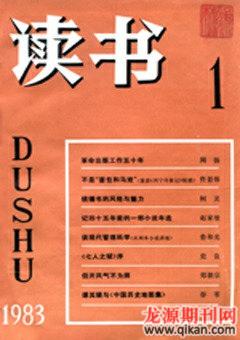不是“面包和马戏”
瑙姆·嘉博 等
重读《列宁印象记》随感
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再版的《列宁印象记》,是杰出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克拉拉·蔡特金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写的一本回忆录。书中生动细致地叙述了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间列宁同蔡特金的几次会见和谈话,为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初期列宁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其中列宁谈到艺术和文化建设问题的部分,已经收入《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书,成为马列主义美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在同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针对当时在苏联出现的一些盲目仿效西方艺术“时髦形式”的做法,发表了他对现代派的那个著名评价:“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当作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而加以赞赏。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愉快。”也正是在批评了当时苏联艺术界中的一些混乱现象之后,列宁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这个经典性的表述,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艺术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必须团结他们、提高他们,并唤起和发展他们的艺术才能。接着列宁又进一步指出,为了使艺术可以接近人民,人民可以接近艺术,必须首先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平;我们的工人和农民进行了革命,以空前的牺牲和鲜血保卫了自己的事业,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人民是文化的土壤,在这个土壤上将成长起一种内容和形式都好的、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一种共产主义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家只有理解并完成这些极其重要的崇高的任务,才算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尽了责任,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也向他们敞开了通向自由的大门,即摆脱《共产党宣言》所精辟地指明的那种悲惨处境。
列宁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为我们描绘的这幅光辉的艺术发展图景,在党的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提到战略的高度,确定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理论观点和行动方针之后,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格外地亲切和备受鼓舞。特别是正当我国艺术界力求克服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后果,开阔眼界,大胆创新,同时在对待西方现代派的问题上也出现了某些糊涂观念之际,重温列宁的这些教导,很有助于我们澄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新美学、新艺术层出不穷,艺术中的“现代热”此起彼伏,其花样之多,变化之快,实为既往任何时代所罕见。但是,在二十世纪,究竟哪一种美学和艺术才是代表时代和社会进步的真正新的美学和艺术呢?
在西欧和美国,几十年来出了不知道多少精致考究的现代艺术和美学著作。人们长篇大套地建立和鼓吹着一个比一个新奇的学说和体系。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在一九二八年出了第六版,他要用“直觉”来排除掉艺术的“杂质”,因为“艺术与真理和道德无关”,用另一个意大利评论家——塔里亚布埃的话说,他“确立了艺术的独立性和纯洁性”;英国的“克罗齐专家”埃德加·卡里特并且据此发挥说,看一幅油画如果还要了解它的名称或主题,那只是“证明着审美上的无能”。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决心紧跟三十年代的新型诗歌和绘画,他说,读者如欲了解艺术是什么,只要读一下艾略特的《荒原》就明白了,它反映了现代文明给人所留下的最后一种感情:恐惧。桑塔亚那以他的“唯物主义”与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相抗衡,一九三九年他在《总忏悔》中重申了早年写的《美感》和《艺术中的理性》的人道主义:知识、宗教和艺术所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都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美的享受的根源是包括性本能在内的各种人性。他认为艺术家创造艺术是利用侥幸的偶然性,而艺术理论家的任务则是要揭示出这些偶然原因和各种不同美的类型的肉体本源。
在七嘴八舌、各执一词的争论之中,唯有精神病科医生弗洛伊德和他的学派得天独厚、经久不衰。正如美学史家凯瑟琳·吉尔伯特所说,精神分析学对模糊不清的、下意识的象征所作的解释,以其为一切神奇玄妙事物所固有的诱惑力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并因此而成为各个对立的流派共同讨论和解释的对象。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中的“神秘的微笑”,几乎成了美术史家们的一个神秘的专题,而弗洛伊德运用他那万能的“性本能”、“潜意识”和“恋母情意综”,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一语道破。他说,这女主人公的微笑,可能是反映了过分敏感的私生子同遭到遗弃的单身母亲之间的一种特别强烈的相互眷恋之情,也可能是由一个充满童年回忆的某种幻觉所唤起的。这只是弗洛伊德学说在美学上的一个小小的妙用!正因为它如此神通,所以先前以及后起的各种符号和象征美学、实证主义美学和语义学美学等等,都竞相把精神分析学当成一大法宝接了过去,各种现代派文学、诗歌和绘画,也无不含有它的种子,或拖着它的影
是的,所有这些美学和艺术流派,除了蓄意否定一切传统和标新立异的因素之外,在一些具体的美学问题上,在艺术的形式和风格手法方面,各自也都有所发明和发现,其中并且不乏可资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尤其从了解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来说,许多作品还具有不小的认识价值。因此,对待属于这些流派的艺术家和作品,我们都要具体分析,决不能笼统地一概排斥和否定。根据列宁的教导,我们从中也可以“吸取人类所积累起来而为我们所必需的一切”。
现代派艺术伴随了资本主义各国自本世纪初迄今的整个发展过程,这本身就说明它是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和必然的阶段,我们必须认真了解、研究而决不可以忽略。问题只是,我们是否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如列宁所批评的那样,只是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或者如列宁的另一个说法那样,在这方面保持一种“艺术伪善”,对西方艺术时髦抱着“不自觉的尊敬”?而现在确实存在这一类情况。
无论现代派艺术有多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代表二十世纪时代和进步的新美学和新艺术决不能是强调本能和寻求刺激、鼓吹荒谬和脱离生活的艺术,决不能是徒具虚名的新形式!二十世纪的新美学和新艺术,必须能够掌握千百万人的心灵,成为他们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武器。它们既不能笼统地排旧,也不能盲目地崇新,而应象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它们应象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论述无产阶级文化时所说的那样:“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已指出,工业革命是人的创造力的完全解放的必要前提,未来的共产主义联合体必将使每个人都有充分可能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从这个伟大的社会理想的提出,到列宁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问世之初,就把艺术接近人民、人民接近艺术的任务提上苏维埃政权的议事日程,一直到在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我们党又再一次明确规定了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这是世界美学和艺术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变革,它把一向被排斥在美的王国之外的千千万万人民尊为艺术和文化的主人。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一次必然的变革,而不是在书斋、学院和画室中杜撰出来的。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工业革命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得好:“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象我国这样以千百万人计的人口,艺术对其中几百人或几千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在资本主义国家,艺术为少数社会“精华”服务,在我们这里,艺术和社会理想、文化和新人的成长,美和真理与道德,是分不开的,一切新的形式也都是按照社会主义的艺术即“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的内容规定的。
在列宁当时的现代派画家之中,有一个瓦西里·康定斯基。《现代绘画简史》的作者赫伯特·里德说,康定斯基和其他现代派画家对现代艺术运动发展所作的贡献,比任何其他艺术家的贡献都要大。他本来是一个俄国人,一九○○年在慕尼黑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法国、突尼斯、意大利和德国各地“漫游从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他先后被任命为重新建立的莫斯科美术学院教授、教育委员会委员、绘画文化博物馆馆长(负责全国画廊的组织工作)、莫斯科大学教授和新建的艺术科学院副院长。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时曾说:“我们已经设立了宏伟的学院并采取了真正良好的步骤,使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青年能够学习、研究、获取文化。”康定斯基任职的这些机构,毫无疑问都正在革命政府所采取的那些真正良好的步骤之列。早在一九一○年,康定斯基就写了一篇“有历史意义的论文”,陈述了这样一个信念:人类正在走向艺术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这篇论文被赫伯特·里德称为“第一部新的艺术信念的启示录”。那么,这个“新艺术”的预言家,在革命为真正新兴的艺术和艺术家们敞开了通向自由的大门之后,在那么多重要而崇高的岗位上,又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列宁谈话的那些年间,康定斯基正继续创作着他那些“不拘形式的”即兴之作,又叫做表现主义的抽象。这所谓“不拘形式”,就是指从“母题”(如风景和人物)中解放出来,使绘画“非客观化”。据研究家考证,这是康定斯基从笔触和斑点的苦心经营中获得的“一个骤然的突破”。据康定斯基本人自述,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他一次回家打开工作室的门,远远看见自己一幅斜立着的油画,只有明亮的色块,“惊得他手足无措”,于是明白了一件事:绘画上不需要有什么客观的东西和客观物体的描绘,这些东西实际上对绘画是有害的。当时在莫斯科,还有一个马列维奇,自称“至上主义者”,主张艺术既不必再现对象,也不应要“有意识的观念”,而是唯以颜色和形状对感情的刺激作用为决定性的因素,他要以此而使艺术达到非客观的表现,即一种“至上的境界”,又叫做纯粹主义。此外还有塔特林、罗德钦柯、嘉博和佩尔斯奈尔等一批画家、雕塑家,搞所谓构成主义,即把艺术创作归结为各种材料的三度空间结构和生产主义,即主张以制造实物取代艺术,因为艺术是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东西。所有这些“新艺术”的大师们,如赫伯特·里德所说,“在大战和内战的旋风之中,在极端的物质困难和政治倾轧(!)之中”,在学院和画室里,从理论上和具体试验上,不断进行着自己的“创新”,把从西欧搬来的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东西,加上一些有如上述的那种革命词句,在定期的公开讨论会上讨论,消除着互相之间的分歧,并因此受到“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喝彩。
所以,毫不足怪,列宁不仅对旧政权使大多数人受不到教育和没有文化无比愤慨,对革命后已经做的大量文化工作毫不满足,对一时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都受到教育和培养深感苦恼,而尤其对当时艺术和文化生活中的无视人民的各种表现,更是表现了那样不可容忍的严厉态度。他向蔡特金说的下面这段话,今天听来仍然是发人深省的:“我知道!许多人真地相信,当前的困难和危险是能用‘面包和马戏来克服的。面包——当然!马戏——没意见!但我们不可忘记,马戏决不是一种伟大的、真正的艺术,而不过是一种比较有趣的游艺罢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决不是罗马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不是受国家供养的,而是以自己的工作支持着国家……”
“面包和马戏”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诗人优维纳利斯的著名警句,它讽刺了贵族用免费的粮食和流行的娱乐(斗兽场的演出)来安抚和拉拢平民即自由无产者的政策,同时也寓有针砭平民胸无大志、安于充当食客和低级娱乐,亦即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公民变成庶民”之意。有人曾对列宁的这段话发生误解,以为列宁似乎对马戏或杂技这种艺术的意义估价过于不足。这段话的意思当然不在于此。马戏和任何艺术形式一样有高有低。列宁引用这个典故的含义,我认为是非常深刻和多方面的。整个说来,它指的是对待艺术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的一种错误的态度。具体地说,它还包括有对于艺术家热衷于时髦,向人民提供低级趣味的东西,或者不顾人民利益和需要另搞一套等等做法的批评,以及革命和人民对艺术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等等思想。
蔡特金听了列宁的谈话后不禁感叹,有些人居然会把一个如此热爱人民的人看成是一架冷酷的思考机器。说共产党人不懂得人和文化的价值,自《共产党宣言》时起就屡见不鲜。可是读一读《列宁印象记》,仅仅这一本小册子就充满着对文化、对人、对千千万万人民的何等关心和热爱啊!有人似乎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学方面没什么贡献。别的统统不说,单是《列宁印象记》的第六篇即最后一篇,就比不少美学论著高明。《列宁印象记》这本书值得文学艺术工作者一读。
《列宁印象记》,〔德〕蔡特金著,马清槐译,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二版,0.21元)
佟景韩/康定斯基/马列维奇/瑙姆·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