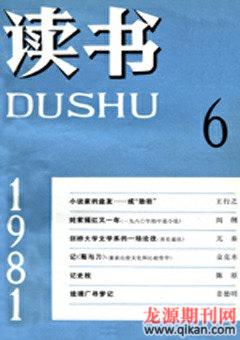对《金薯传习录》的再认识
吴德铎
《金薯传习录》影印本前言
一
一九六一年第八期《文物》月刊同时发表了两篇讨论甘薯历史的文章。拙作《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主要是介绍这一有关甘薯的重要古籍,夏鼐同志的《略谈番薯和薯蓣》,在结束时,有这样一段话:
“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关系更大。……由这一角度来看,考证番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是有它的重要意义的。”
《文物》月刊上进行这一问题的讨论时,我国农史学界的局面,相当生动、活泼。成绩也斐然可观。但,那时,只有夏鼐同志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农史研究,一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和必要。至少我个人是如此。
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我们才了解,国外已有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作过这方面的研究。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一人,对“美洲作物传华的问题”,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便三次(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九年)“用英文发表了研究的结果”①。一九七八年,何炳棣教授为纪念《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而撰写的《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①一文,便是专门讨论落花生、甘薯、玉蜀黍、马铃薯这四种作物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
何炳棣教授认为:“四百余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①何炳棣教授说,他“在研究的较早阶段已经发现,近千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长期的‘革命。第一个革命开始于北宋真宗一○一二年后,较耐旱、较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逐步传播。”“我国第二个长期粮食生产的革命,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美洲作物传华四百年来,对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确实引起了一个长期的革命。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是互为因果的……无疑义地,新中国科技、组织、计划、执行的水准与嘉(庆)道(光)之际的水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今日人口的压力……较道光末年却也加了一倍以上。因此,本文所提供的大量历史资料(何先生此文,长达三万余字),多少还应有些‘古为今鉴的用处。”②
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外国作物的引入和推广,便赋予作物栽培史以巨大的现实意义。
何炳棣教授指出:“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②。这个数目字再也具体不过地说明我国的甘薯在世界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我国引进甘薯的历史经验,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许也“多少还应有些‘古为今鉴的用处”。
研究甘薯的种植和推广,并把它作为解决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不足的补充手段之一,是当前全世界农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均对这一措施寄以厚望。栽种甘薯较早、生产甘薯最多、深受甘薯之惠的中国人民,自应在这方面竭尽绵薄。我们中国农学史工作者所应做的,当然是将我们的引入历史和栽种经验(包括教训),无保留地公之于众。
一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在学术思想界,确实存在着一个悠久的重农传统。有人甚至以为,欧洲十八世纪的重农学派是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衍生物③(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有“欧洲的孔子”之称)。《农政全书》共六十卷,汇录前人的重农学说的资料(《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国朝重农考》),就有三卷之多。诚如陈子龙在《凡例》中开宗明义声称的:“古之圣人,畴不重农政哉?”贾宝玉非常厌恶的“文章经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章,以“重农”为题目的,多得难以数计。不过,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尽管“民以食为天”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玩忽民食”也是封建社会中地方官吏的极大罪名,但,千百年来,真正研究农业生产的著作,却少得可怜。吴汝纶在给《天演论》写的序中不胜感慨地写道:“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④,在这些士大夫心目中,农业生产技术,不仅属于严复所指陈的“象数形下之末”⑤,而且,在“末”中,恐怕又是倒数第一!
在号称有数千年重农传统的我国古代思想学术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怪现象:一方面是理论上,众口一词,无不推崇农业生产的重要;而另一方面,象贾思勰、陈
农家类著作少的原因当然也很多。它们是研究生产、讲究实效的,与科举仕进无关(至少关系不大),应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来,又带来了另一个消极作用:本来数量就不多的农书,普遍不为人们所重视。现在影印在本书中的《金薯传习录》问世年代,距今不过二百余年,并且印过三次。与它同时的公私撰述,保留到现在的,不知凡几,而《金薯传习录》则只福建省图书馆藏有一全本(即本书据以影印的底本)。这书现在如此稀见,倘理解为当年印数少,也不是事实。本书的编撰人陈世元的《续刻布词》说得很清楚:“两朝诸绅士,赋颂诗词,薯疏笔记,汇订成卷,但取印刷微费,散置东西南北各省书坊,俾就近得以购览。较之昔人所著《齐民要术》、《食物本草》、《致富》诸书,尤见简切,而利赖无穷焉。”可见当年流传的范围,并不太狭隘,但,这书不仅《四库》未收(这书刻印之日,正《四库》撰修之期),连一般的书目,均未著录,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珍贵史料的命运,有的甚至还不如《金薯传习录》(连一本都没有传下来),甚或连书名也不为后人所知。造成这情况的原因,固属多多,但它们不登大雅之堂,属于“象数形下之末”,与仕进无关,应该是、也始终是主要原因。
从浅表看来,《金薯传习录》这书似乎没有什么大道理——它不过是明季陈振龙将薯种传来、他的后裔积极加以推广的资料汇录。又因为他们人微言轻(有的还是利用外出经商的机会来推广),所以要假借官府的力量,到处呈请大老爷批示、支持。为了说明种植甘薯是可能的、方便的,他们还在许多地方种给当地人看,用事实来证明言之非谬。又印了许多招贴,四出张贴。内容既猥杂琐屑,又仅仅是一家门中的事,而这些人的社会地位都很平常。从这样的角度看来,这书确实无多大价值。不仅没有什么价值,且反有为自己人评功摆好,过分吹捧先人之嫌。以这种尺度来度量,《金薯传习录》不受重视,理所当然。
何炳棣教授,大概是从有关的书籍中,知道《金薯传习录》,未尝获睹原书,所以他在上述那篇长文中,谈到乾隆年间推广甘薯时,征引的文献,是陈宏谋的《培远堂偶存稿》,在谈到“直隶、山东等省又推广甘薯的种植”时,也没有提到对这事有详细记载的《金薯传习录》。如果我们象何炳棣教授对《培远堂偶存稿》所采取的态度那样,突出推广甘薯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金薯传习录》,作为一部甘薯引种、推广史料汇编,是最宝贵的科学史文献。它为我们提供的,是第一手材料,是经过实践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当时人的亲身见闻。这种当事人亲自写下的推广甘薯的专著,不要说在我国,即使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金薯传习录》的史料价值,世罕其匹——朝鲜徐有榘的《种薯谱》、我国陆
象《金薯传习录》这样的有关甘薯的史籍,在目前还没有第二部。
三
我个人了解、接触这书,开始于五十年代末,但不是一开始对这书便有这样的认识,为了说明个人认识的过程,不妨在这里提一些往事。
人们都知道,解放前上海的“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早期留美学生组织的、旨在推进祖国科学事业的学术团体。它所创办的事业,如“明复图书馆”以及两种刊物:《科学》和《科学画报》,数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彰明较著的。上海解放之初,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任鸿隽等诸先生,一度决定将《科学》停刊(《科学画报》移交给国家出版机构继续出版)。据了解,上海市长陈毅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后,亲自进行了干预,责成上海有关出版机构负责印行,《科学》本为月刊,改为季刊,继续出版。
五十年代末,由于写(译)稿的缘故,我和《科学》编辑部联系较多,因而任鸿隽老先生要我也分任一些工作。根据当时的条件,任老先生等决定,中国科学社的工作应以征集、整理科学史料、发表科学史的论著为主。当时曾出版过一两种中国科学社主编的科学史专著。《科学》(季刊)的内容也积极转向这一方面。任老不只一次地耳提面命,要我多做些有关科学史的工作。在一次下乡劳动的过程中,我才知道甘薯这作物有那么多的用途、它和农民经济生活的关系是那样密切。我便决定对我国种植甘薯的历史,进行一些探讨。
当时,以收藏方志出名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开放未几。前去看书的人很少,有时整整一个下午,只有两人:我因查考甘薯传播史,借阅各种地方志;另一便是曾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苏继
我查遍了所有有关甘薯的方志,写出了一篇万余字的《甘薯的故事》,发表于一九六○年四月出版的第三十六卷第二期《科学》,它是拥有四十余年历史的《科学》的最后一期上的最末了一篇文章。
从方志中我知道福建有过《金薯传习录》这样的专书。通过它才确切地知道,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蕃衍,其传遂广。”这是有关甘薯传来最明确、具体的记载。当时,农业出版社正开办,我一方面建议他们重印这书,一方面向福建省图书馆求援。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农业出版社采纳了我的建议,福建省图书馆慷慨地把这一珍本(即本书的底本)借给我用了半年。我抄了个副本,不少单位、朋友又根据我的抄本传抄。同样也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这个抄本,居然跟着我安然地度过了“十年浩劫”。
当年我建议农业出版社出版的,是一个排印(标点)本。为了这件事,我曾向史学耆宿陈垣老先生求教。援老很快便寄来我求他写的书名,回信中谦逊地说,甘薯问题,素无研究,不敢说话。但他热情地以一大包他自己的著作见赠(包括几种很珍贵的励耘书屋刻本),援老的著作,是从事史学撰述的楷模,是后学的榜样。
回想起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初的往事,真有说不出的愉快。老一辈对素昧平生的末学后生的扶持、提掖,身受者固然铭感,这种风气也是值得发扬的。
我既目睹了《金薯传习录》原书,又手抄了一份。一九六一年二月,在给《新民晚报》写的介绍版本学知识专栏《书林一叶》中,又专文介绍了一次,并刊出了书影。同年八月,《文物》又发表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从此以后,介绍、谈论《金薯传习录》的文章,经常可以在报刊上读到。邓拓同志在《燕山夜话》中也谈过这本书。一九六二年冬,郭沫若院长在福建时,曾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并要求有关同志,设法查考下卷中《金薯歌》和《金薯颂》的作者。福建的同志,终于查考出,《金薯歌》的作者是叶向高、《金薯颂》的作者是何乔远。后者的《闽书》,在史乘中,是颇负盛名的(实际上,《金薯传习录》中的《金薯颂》就是《闽书》中的《甘薯颂》)⑧。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兴旺、活泼的局面,不久便完全改观。古农书的研究、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探讨都在禁忌之列。重印《金薯传习录》自然更不可能。陈援老的亲笔题签,也在动荡中失落。有关这书的设想,完全成了泡影。
不过,世界上的事,很难逆料。当年只想出一个排印本,遭到了扼杀。今天,我们将它全文影印,并且还打算另出校注整理本。“从一粒砂可以看出一个世界”,这一微不足道的变化,也可以说明许许多多问题,其中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是在一天天的好起来!
上文说过,我个人对《金薯传习录》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头便象今天这样。在发表于《文物》的拙作中,我说过这书“类似民间流通的‘劝世文。”把它看成不过“是一本在农村中流传的通俗书”。是的,它的确“是一本在农村中流传的通俗书”,但这些年来,随着人口问题的突出,便不免常常想到甘薯在解决世界性粮食供应不足这问题上所能起的作用。由此进而想到我国甘薯的来历和当年有识之士为了推广这作物所付出的劳动。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再来回顾《金薯传习录》,这书的价值和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便越来越显得重要。这书在学术上的意义,决不如我过去所设想的那样,仅仅“类似民间流通的‘劝世文”而已。
四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与外界接触频繁,外来作物传入的渠道很多,我们承认陈振龙传来了甘薯,但恐不能因此便断言,所有的甘薯都源出于唯一的这条“根”(拙作《甘薯的故事》对此有较详尽的说明)。许多外来作物的来源,我都倾向于多元说,不大赞成简单的“一元化”。如果将所有甘薯的传来,全记在陈振龙的功劳簿上,恐怕既不符合当年的客观事实,也不适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当然,在甘薯传来及推广等历史问题上,陈振龙及其后人,成绩卓著。但在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科学遗产的我国,陈振龙决不是我国唯一的甘薯“拓荒者”。
二十年前拙作《甘薯的故事》曾指出:
“自古以来是我国领土的台湾的材料,也是我们所应该重视的。清·黄叔
这便说明了,台湾的甘薯,有的由福建传往,有的得自文莱,它的来历,也是多元的。和祖国大陆上的情况一模一样。
据报道,近来,台湾学术界人士中出现了一个寻根热。他们经过多方面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台湾所有一切的“根”,都在祖国大陆。⑨本是同根生的甘薯,当然更不例外。
(《金薯传习录》与朝鲜古农书中的珍本《种薯谱》(汉文),即将由农业出版社影印、合刊出版)
①《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卷,页673—731。
②《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卷,673页—731。
③参阅Reichwein:《China andEurope》,页104。
④吴汝纶:《天演论序》。
⑤严复:《译天演论自序》。
⑥参看拙作《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
⑦苏继
⑧何乔远的《金薯颂》,即《闽书》中的《甘薯颂》。关于何乔远、《闽书》与甘薯的关系,请参阅拙作《甘薯的故事》。
⑨张仕英:《台湾的‘根源于中国大陆》,载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日《台湾新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