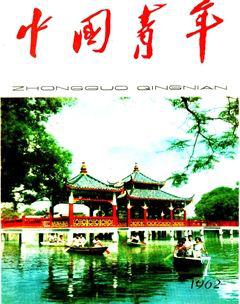拜年
浩然
农历正月初一早晨,乡亲们仍是按照老习惯互相拜年。从第一声爆竹响起,村子里就热闹了;贴着春联彩画的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上,都活动着穿戴整洁、满脸喜气的人群;空气里震荡着欢笑声,混和着煮饺子、炖猪肉的香味儿。
宋三爷在吉素村辈数最大,人缘也最好,往常拜年,大伙几总是先从他家开始;今年谁也没有跟谁商量,就都自动地改变了路线。听说宋三爷没结婚的三女婿来拜年,这是一件新鲜事儿,众人要最后归到宋家,多坐个时辰,凑凑热闹。
宋家三口最高兴,也最忙;三个人三个心眼儿,忙得也不一样。
宋三爷是个好体面的人。他是队里有名儿的老积极,去年劳动一年,接连着受表扬,干活儿争强夺胜,爱社不甘下风;就在生活里的一些细小事情上,也总要比别人高出一格。没结婚的女婿第一次登门,他觉得十分光彩;人家又是农具厂的工人,工农本来就是两亲家嘛,加上这段姻缘,更是亲上加亲;这是他在众人跟前显头露脸的机会,决不可放过,更不能在客人面前丢丑。
天不亮宋三爷就起来了,把院子打扫得象场板似的,建一块石子儿、一片柴草叶都给他拣走了。他还把棚里肥滚滚的山羊,故意拴在猪圈前边最显眼的地方。房檐下挂着的两大嘟噜玉米,本来用草遮着,宋三爷把草拿掉,叉把上边的坐土打扫净,旁边配上两串鲜红的干辣椒,把它衬托得特别金黄耀眼。厢房是他这个老保管的仓库,他除了用春联上的字句表示了此地重要之外,还学着镇上粮站的样子,裁了一张长方的红纸,写了“仓库重地,谢绝参观”八个大字,贴在门上。
这一切都是可以让那位工人一进门就感到,这个生产队生产搞得很出色,社员的生活安排得也满好;这是个丰衣足食、日子昌盛的家。
院子收拾完了,宋三爷又开始布置屋子,屋子里更进了一层。平时舍不得用的一只雕花红漆桌,摆在炕上了,桌子旁边铺着一条北京清河呢厂出产的花毛毯,这是女儿进京开会的时候买来的。宋三爷最热心显示的是北墙壁。那边,毛主席画象两旁挂的是他和闺女玉娟的模范社员奖状。那是去年抗旱播种和消灭虫害两次战斗中得的。两次战斗,使老人家深深地懂得了“人定胜天”这旬话的意义,也让他受了一场锻炼。两张售卖超额余粮的收条,本来无须保存,他却从柜子里找出来,小心翼翼地贴在奖状的下边。挂在偏右方的那一面红缎子奖旗尤其引人注目,上边绣着“战胜灾害夺丰收”七个金黄的美术字儿。这旗子是他昨晚上从会计那里要来的,他借口保管员要保管生产队所有的财富,实际上却是为了给自己装装门面。有了它,给这个小屋子增加了无限的光彩呵!
这一切都可以无声地向工人贵客表示:这个生产队的生产之所以搞得好,是社员的干劲高,两张奖状能够显示这一点;搞好生产,不是凭那一个人的本事,得靠大家伙几一条心,一股劲儿,那面红旗可以说话;社员积极生产,并不是光为自己,是为国家建设,为支援工人老大哥,那两张出售余粮的收条,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宋三爷手忙脚乱地收拾完毕,又里里外外地自我欣赏一遍,这才心满意足地在那只铺着新毡垫的春凳上坐下来,悠然自得地抽烟,等候贵客。
三奶奶是个“内热”的人,她想得实际,做得也实际。作娘的都有一付永不满足的心肠,玉娟是她的三闺女,是她填补心愿的柜子。大闺女才满七岁,斗红高粱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妇,上头①那年闹旱灾,大年初一女婿照例该来丈人家拜年,可是那边买不起二斤粗点心的礼物,这边也做不起一顿有粮食的饭招待;一切从简,女婿空着手来,扶扶水缸就走,三爷又嫌丢脸,两头老人暗地里一商量,免了这个礼儿;年轻人不明白老人的难处,女婿一气,十年没登过丈人家的门槛。三奶奶觉着欠了债,对不起闺女,每逢年关佳节,别人家迎送女婿,她就痛心地流泪。二闺女攀了个高枝儿,找下阔婆家。老俩口要填补心愿,从秋天起就一点一滴地节省、积蓄,到了年根下又借了一笔吸血债,割了肉,磨了面,建细盘子、花瓷碗都借下了。她也象今天这样高高兴兴的准备迎接贵客;可是那边嫌弃宋家日子贫困、门户不对,女婿根本没有理他这个茬儿,面也没有见。三奶奶无端无由地埋怨着自己,觉得对不起闺女,每逢年关佳节,谁若是提起女婿拜年,就气得浑身发抖,牙根儿疼。
三闺女玉娟可赶上如今这个好时光了。日子过得昌盛,谁不知道吉素是全公社的丰产队?家庭是体面的,谁不知宋家三口出了两个有名儿的模范?没结婚的女婿上门来拜年,已经使老人家高兴了,而女婿的身份更增加了一个丈母娘的荣誉感。人家是农具厂的技术员兼副厂长,还是盘山里有名气的老铁匠“锄头李”的后代;据社员们说,队里使的锄、镰、锨、镐,还有双铧犁、播种机,都是女婿那个工厂造出来的。春天,正是播种的季节,滴雨不落,墒情又不好,社员决心要抗旱点种,种着种着到了山根下,离着井水远,渠里的水也引不上去了,就在这个当口,跟天兵下降一般,农具厂送来了车拉水箱。没见那水箱哪,一箱能装四十多挑子水,顶四十个棒小伙子;下边安着滚珠轴承胶皮轮,走起来风快,棒小伙子也撵不上,这一车就把一亩地种上了,多救急!六月里起虫害,大片大片地超,庄稼棵里打疙疽,站在地头上,就听得刷刷响,让人心焦!社员要在虫子嘴里夺粮食,药粉成车往地头上拉,满地的喷雾器吱吱晌,把筒子打得烫手热,消灭一片又一片,可恨的虫子在后边又跟着起来了。比及时雨还要及时,农具厂又把马拉的喷药车送到地里。没见那车哪,十个头安在尾巴上,走起来象下雨,一喷一大片,走多快,喷多快,一个来回就是二亩地,看虫子还能不能!都传说,这两种新东西都是三奶奶的女婿跟他爷爷“锄头李”发明创造的。对于女婿,她从来没有见过,就凭他不辞辛苦,处处为农民打算的热心肠,就实在讨她欢心了!
有这样一个女婿,怎么会不让老丈母娘称心呢!她比老头子起得更早,切菜、剁肉、合面,天不亮,她就包完了两大盖lian小饺子。那饺子是纯肉丸的,白菜、葱花只是当作料;那面是头罗白,雪花一般。她精心致意,施展了老手艺,把饺子捏成花边儿、鼓肚子,一般大小,一个模样;一圈一圈地摆在盖lian上,一眼看去,就如同在北京城里玉石刻的浮雕。接着,她从房背后草堆里翻出个大冻柿子,这是傍年根前队里分给社员的;她用凉水把柿子洗净、擦干,摆在花瓷盘子里化着,活象一座红琉璃的小塔。她又从罐子里拣出一些山里红、大枣儿,分别放在两只大海碗里,活象两碗珍珠、玛瑙。另外还炒了一盘向日葵籽儿;女婿要是不吸烟,就一边说话,一边嗑着吃。
现在,三奶奶总算坐下来了,她坐在离灶火不远的水缸旁边的蒲墩上,一边慢慢地摘豆芽儿,一边想着心事,打谱炒几道菜下酒,她想得多,做得多,却显不出半点激动和忙乱,一如平时,有板有眼,平平静静。
最慌乱,最激动的要算三闺女玉娟了。她处处都随她爸爸,就好象是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纸糊的灯笼里外亮,肚子里的话儿挂脸上。她数了一夜窗户格子,早晨起来,她帮过爸爸,也帮过妈妈,什么活儿她都搁过手,什么活儿她也没有做出来。点着柴禾,她忘了添水;舀水的时候,却抓过一把铁丝儿笊篱。烧一锅开水的工夫,她偷偷地跑到大门口张望了三次,中间还溜进自己房里照了两次镜子。
她希望自己那个人今天打扮得非常标致、漂亮,第一眼就给村里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就讨得爸爸妈妈的欢心;虽说,很多人都认识这位工人,可是人们对于最熟悉的人,一旦要当新女婿了,也总是另眼看待,仔细观察,总要留神平时不留神的地方。等他拜了年,离开吉素村,她就可以红着脸,噘着嘴几,扭过头去,却是张着耳朵去听取别人的夸奖、赞美,她应当,而且能够享受到这一切的。今天她自己的打扮,就苦费了一番心思。别看她平时干起活来是个横冲直闯的庄稼姑娘,美,却总是她生活里缺少不了的内容,就连下地挑大粪去,临出工之前也要穿戴得整整洁洁。今天在一个初恋的姑娘来说,是个万分宝贵的时光,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更美!
镜子摆在代替梳妆台的方桌上。镜子擦得亮光光,她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镜子里立刻照出另一个俊姑娘。她又象玉娟,又有点儿不象;那生来就曲卷的头发,那略有几颗小小雀斑的圆脸,是她自然健康美的象征;那个紧闭着的、带着挑皮神气的红薄嘴唇,是她对新生活充满着信心和神往的内心流露,如今,又好象憋着多少秘密要对别人说,又不肯讲出来。她看着看着,眼神渐渐模糊不清,镜子里忽然间变成一张男子的脸。那张四方的,微黑透红的脸,虽然依旧不失铁匠固有的严肃和坚强神气,却掩不住地带着一种甜蜜的,迷人的微笑;他笑的时候,黑眉毛
总是往上挑起,大眼睛却细成一条缝儿,让人感到他质朴又天真。工人帽斜扣在后脑勺上,分不清是兰是青的工人服上,除了油烟子,就是被火星烧得大大小小的窟窿眼儿——老天爷,他怎么这个样子就来了!你是来抡锤,你是来拉风匣,你还是来收废铁?
这正是玉娟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样子呀!
那是前年秋天的事情。
盘山前的谷子熟了,玉娟领着社员开始收割,还跟别的队挑战比赛。可是不到半天的工夫,就有十几个社员找她换镰刀,这个说镰刀钝得不能使,那个说镰刀卷了刃;开头玉娟还是大嚷大叫地让大伙儿对付一下,没多久,她自己的镰刀也变成了秃菜刀。她火了。
“这是那个倒霉的地方出的?”
“邦均农具厂呗!”
“我找他们算账去!”
于是,她把所有的坏镰刀装在筐子里边,背到镇上,一进车间大门,就哗啦一声,把镰刀倒在地下,两手插腰,怒眉立目地喊:“喂,这是谁的手艺?”
正干活儿的工人们都给这个愣姑娘闹懵了,一个黄白头发的工人瞟她一眼,问道:“同志,别这的大气,怎么回事呀?”
“我问你这是谁的手艺?”玉娟用脚尖指指地下的镰刀说。
“这是大伙打的。”
“我看你们都不用吃饭了,鸭子也能打出来呀!”
“有话尽管说,别骂人呀!”
“骂人,这还是好听的呐!”玉娟满肚子火气顶嗓子,朝那工人眼前凑了一步说:“你们耽误了我们多少活计,谷子烂在地下收不上来,你们负责任吗?退吧!”
“这镰刀农具供应站包售,你在那儿买的那儿退去。”
“我不管那儿买的,是你们打的,你们就得给退!”
“这人真厉害……”
“厉害,咬你了?”玉娟翻了翻眼珠子说:“你不懂人话,你们头呢?”
就在这个不可开交的时候,从里边走出一个高个子工人。他方脸浓眉,斜戴着工人帽,身穿着窟窿的衣服,围着说灰不灰,说白不白的围裙。他一面朝这边走,一面拿被煤屑沾黑的毛巾擦汗,和气地对玉娟说:“别着急,别着急,有话儿慢慢讲。”说着,搬过一只凳子放在玉娟身边:“同志,请坐,请坐。”又端过一杯白开水。“同志,喝水,您有意见对我说吧。”
真怪,玉娟朝那工人的脸上扫一眼,心里的怒火,立刻消去一半。她看到那张严肃的脸上,洋溢着热情和诚恳的神态,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声调也自然低了,说:“照你这样,话还好说。你们这镰刀简直象木头片子,一使就卷刃!”
工人从地下拾起一把镰刀,看了看又问:“这是麦收时候买的吧?”
玉娟说:“割麦子倒对付,麦子跟谷子不一样呵!麦子一碰就折,割谷子可得使大劲儿!”
工人闻听,惊奇地看了姑娘一眼,醒悟地低声说:“这一层我们可真没有想到。”就用大拇指试试刃,放在耳朵下边敲敲听听响,又说:“火候软。我们一定包修、包换。您先回去……”
“马上就退吧!”
“退了你们使什么,那不耽误生产嘱?”
“你说怎么办?”
“一起晌我就把新镰刀给您送地里去,行吧?”
玉娟回到家,火气一消,又觉着自己太莽撞了,实在对不起人家工人;这么热的天头,何必劳累人家给送来呢!她没有吃饭,就又往回折,半路上,正巧碰见那个年轻的工人骑着车子送新镰刀来了。
工人跳下车子,从后架子上解下一捆镰刀,对玉娟说:“这些镰刀又都加了一遍火,您使使看,不行的话,再找我们,反复搞几次,慢慢地就可以摸出经验来了。”
玉娟一再道谢,又不好意思地说:“刚才我太火性了,说话不大好听……”
工人说:“谷子要紧着收割,这事情放在谁身上也要着急的。”
看人家多会体贴人,玉娟心里很感激,就问:“同志,您贵姓呀?”
“我叫李贵庭,您叫宋玉娟,对吧?”工人微笑地说着,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本子:“您这次到厂里去,把我们提醒了:办工厂不能关着门儿——我们过去不就是关着门儿吗?关着门儿开会、研究,关着门儿制造,制出来就出售;满心是想支援农业,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合用不合用,农业还缺什么,我们可就捂着耳朵不听了。这回我们要坚决改。您就当我们的义务参谋吧,这本子您收下,队里对我们生产的工具有什么意见,另外还有什么要求,您就记在这本子上,您赶集时顺便就跟我们说一声,没工夫去,求别人把本子捎去也行。”
……
这一天,玉娟从工人那里换回来镰刀,换回了信任和鼓舞,也换回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那个高个子、斜戴工人帽的身影,那张严肃、坚毅的面孔,常常在她眼前出现。那个白报纸本成了她的日记,她在上面写下了许许多多的话,也写进一个农村姑娘的热烈的,心情。这本子在工厂和农村之间传递着,它象一片肥沃的田地,在这个农民和工人的汗水和心血灌溉下,结出硕果。春天抗旱播种的时候,姑娘在生产队的灯下,把希望的种子埋在本子里;传到工厂之后,在工厂的洪炉旁边,一辆辆大水箱和喷药车就诞生了……爱情,也跟着一切果实丰收来临了。姑娘的心,渐渐地给工厂里那颗心吸住了。玉娟每次到邦均赶集,总是把牲口拴在农具厂的大院子里;有些东西临时弄不回来,也存在那儿;她还带着一群姑娘在工厂里看过两次电影;八月中秋到镇上看戏,社员们坐的凳子,都是玉娟从农具厂搬来的,农具厂食堂还专门招待他们喝茶水。这样一来二去。风言风语就就在村里传开了。姐妹们另眼看她了,小伙子们跟她开起玩笑,爸爸妈妈耳闻目见,也是无声的赞许:这一切都如同金皇后②吐线、壮浆时候的一场甘露雨,催促了这颗爱情果实的速快成熟……
姑娘变得更神气了。幸福的时代,人人都是幸福的,她却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幸福;她不错过一切机会,要向村里的每一个人显示她的未婚夫。眼下是新春佳节,人齐全,又闲暇;只要他一来,全村的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看不到,以后,会有多少人议论他,该给她增添多少光彩!
三奶奶在外屋喊叫起业:“玉娟,你这猴丫头,钻到屋里干什么去了?火都烧到灶膛外边了!”
玉娟被吓了一跳,立刻从梦一般的甜蜜回忆里惊醒了。她象一只小山羊似的从屋里跳出来,红着脸,把木柴踢进灶内,又使劲跺跺脚,抖下跳到花鞋上的灰烬。
三奶奶又说:“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不来,说不定不来了……”
玉娟实在不爱听这句话,把小嘴一噘说:“人家可不是那种人,说到那儿,就办到那儿;象您说话不算数!”
“哟,疯子,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贵庭信上说不让咱们破费铺张,随便做些吃的就行了,昨晚上您满口答应,可是……”
“过年过节嘛,他不来,我们也是照样吃喝;妈要是舍不得给他吃,把什么都藏起来,你该又生气了!”
玉娟捂着嘴,嘻嘻地笑了起来。
宋三爷被母女俩的说笑声惊动,磕打了烟袋灰,从屋里走出来,站在门口,看看东升的太阳,听听街上的鞭炮声、嘻笑声,又转过头来问闺女:“玉娟,你们把日子订妥了没有?才八里地,不要说骑车子,就是步行也该早到了,说不定忘了吧?”
玉娟又噘起嘴,说:“人家脑筋可好呐,那么复杂的机器都装的下,这点小事情就忘了,照您记性不好?”?“嚯,我记性怎么不好了?”
“人家从保管股借筷子那么长一节儿拴口袋绳,您还要记账呐!”
“那不是记性好不好的事情,那是规矩。”
这工夫,拜年的乡亲们把全村都转完了,继续行行的地朝宋家奔来,欢笑的声浪,从街口泛进宋三爷的小院子里。
“三爷,贵客还没到哇?”
“恭禧,恭禧。玉娟,新女婿的架子不少吧!”
玉娟自己也奇怪,为什么忽然间忸怩起来了?她脸上一热,蹭地一步跳进自己的屋子里。堂屋和爸爸屋里那么沸腾欢乐的声音,一点儿也进不到她的耳朵里去,她极力地注意着院子里的动静。院子里只有肥猪撞击着圈门的光当声和山羊的咩咩地叫唤。她心里十分焦灼,不由得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团,小心地抖落开,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是李贵庭前天求赶集的人捎来的,上边明明写着,今天早起来拜年,吃了饭走,这怎么会错呢?就算临时有了事情不能来,也会再捎个信来。喔,说不定他走错路了。这边好几个村都叫吉素,西边大吉素顺道又出名,说不定他撞到那里去了。想到这几,她悄悄地把门帘扒开一道小缝朝外看看,只见西屋的人们让烟让水,说说闹闹,谁也没留神,她就来个闪电式,几步跨到院子里,撒腿就跑。
过了一道沟就是大吉素村。鞭炮声、广播喇叭唱,和那满街鲜红的春联、穿着花衣服的孩子,都不能引起姑娘的注意,她被路面浮土上的两道自行车轱辘印吸住了,她熟悉这花纹似的印痕,就如同熟悉这车子主人的手纹一样。李贵庭果然是走错了路,钻到这儿来了。她顺着车轱辘印往前走,走着走着,一面通到二队的队部门口。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停在那儿,车把上的丝线把套是她织的,把套上垂着的两个穗子,是她从发绳上剪下来的;车座的套子上的花是她绣的,那上面折边花布,是她做棉袄裁剩下的;车后架搭着一个上马上③,一头装着一个用彩纸包装的点心匣子,这可真象新女婿拜年的派头了。
姑娘的心里跳了,脸上笑了,她刚要开口喊,忽听得屋里暴发起一阵哄笑和鼓掌声。
“静静,静静,让李厂长说完嘛!”有人大声地维持秩序,好久才安静下来。
“我没有好多话讲,今天就是来给农民同志们拜年,顺便跟大家要点礼物。”这正是她的李贵庭的声音。
“说吧,要什么给什么!”一个老人的声音。
“工厂支援农村,农村也要支援工厂嘛!”一个女人附合。
“别的不要,就要大伙几对农具厂的意见。”李贵庭用铁匠常有的那种高昂洪亮的嗓门说:“去年我们制造的工具,那一些好用,那一些不好用;还有,按着你们今年的生产计划,我们农具厂还应该增加什么新品种……。”
又暴起一阵笑声和鼓掌声。
“不得了,工人老大哥跑到我们门口征求意见来了!”一个人大声地赞叹说。
“对。去年我们跟几个队挂了钧,用意见本或是请农民到我们工厂里提意见,这办法的收效很好,可是太不够了。从今年开始,我们工厂领导分工包片,定期下来登门拜访。”李贵庭叉乐呵呵地说:“平常日子大伙不得闲,难得象今天这么齐全,就讲各位先提意见吧。”
“不忙,不忙,吃了饭再说。”
“对,李厂长到我家吃,还有白干酒哩!”
“不了,谢谢各位。”李贵庭客气地说:“一会儿我还要到三队,中午前赶到小吉素,到那儿看个亲戚……”
“是给老丈人拜年吧?”
“真是公私两利,这样咱们可不能强留了!”
又是一阵哄笑。
在笑声中,玉娟已经跑回家。
三奶奶惊喜地站起身:“看你这鬼丫头乐的,他进村了吧?”说着,她赶忙往灶膛里加把火,又把切好的菜和肉看了一眼。
宋三爷也迎出屋:“怎么这时候才到?是骑车子还是步行,没带别的朋友来吗?”他说着,看了看拴在院子里的山羊和仓库门上的红色的方纸块。
来拜年的乡亲们也涌到门口,挤着朝外看。
玉娟喘着气,忍住乐,对众人说:“都请屋里坐,屋里坐,还没到呐!”等大伙儿都转回屋里,重又坐定,她急忙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白报纸本子,又抽出钢笔,往雕花的小炕桌旁边一坐,说:“大家给农具厂提些意见吧!去年他们打出来的东西那些应该改进;按着我们队今年的生产计划,还需要他们制造什么新工具……”
宋三爷一楞:“怎么回事儿呀?”
三奶奶把嘴一噘:“这丫头真疯了!”
玉娟撒娇地把头一晃:“这样先下手,节省他一点时间,好多走几个村。”
“节省什么时间?”三爷问。
“走什么村呀?”三奶奶也问。
玉娟认真地说:“人家正在三队,一会儿就到咱们这里来;人家不光是为了拜年,还要征求对农具厂的意见……”
老俩口和拜年来的乡亲们这才恍然大悟。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草
①上头即正式结婚。
②玉米的一种。
③有地方称褡裢,类似布口袋,两端装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