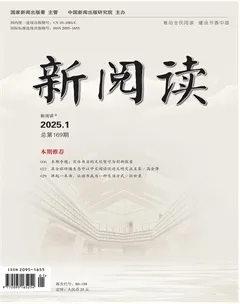从意象到意脉:《野草·希望》的虚无书写与精神图谱
摘要:《野草·希望》中的意象和意脉,是鲁迅在社会变动、家庭失和双重背景下创作动机的外化。作品中的革命、青春、暗夜意象分别代表了希望的狂飙突进、情感的细腻温柔、生命的虚无感。这些意象构建了作品的意脉,展现了鲁迅对革命的理解、对青年未老先衰的失望,以及直面黑暗的思想碎片。
关键词:创作动机" 意象" 意脉" 道路
五四运动自1920年9月进入落潮期,思想启蒙热潮逐渐减弱,新文化阵营内部因理念分歧而分化,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与斗争。1923年7月,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了一封绝交信,宣告他们40年的兄弟之情断交。在社会变动和家庭失和的双重背景下,鲁迅于1925年1月写作了《野草·希望》,故而其中有着明显的失落感和虚无感。《野草·希望》是一次面向虚无的独语。虚无的概念在存在主义和神秘主义中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沿用的是存在主义的界定:世界本身没有固有的意义或价值,人类生存在一个没有神、没有固定价值观的世界中,即“存在的无意义”。独语是一种个体自发地用言语表达内心思绪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是非对话性的,即个体并非在与他人进行交流,而是在自己的思维中进行言语表达,其可以被视为一种释放情感、整理思绪的方式。《野草·希望》通过一种直面虚无的姿态,展现出在困境中调适自身并言说的勇气,总体上接续《野草》的苦难、战斗美学精神。
意象
《野草·希望》中有着三个明显的意象,即革命、青春、暗夜。
革命意象以“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为标志,带有攻击性和生命力具有激进、爆发的一面。这不仅仅是对旧秩序的颠覆,更是对新生活的追求。这种希望是由内而外的,它源自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可以说革命意象中蕴含的是一种狂飙突进的希望。这也可以看到鲁迅对尼采“个性”思想的借鉴。尼采用非理性的生命意志取代理性,强调非理性的情绪体验,使得艺术和哲学都成了通过某种特殊情绪状态体验生命意义的活动。尼采的意象、文体特征都为鲁迅所吸纳,并渗透了他的创作,在鲁迅的革命意象当中被描绘成“血腥的歌声”,这也使得革命意象中蒙上了一层战斗的美学色彩。
青春意象指代的是情感上的奋不顾身。这种希望更多寄托于青年人之中,通过“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等形象描绘出来,是一种更为温柔、细腻的希望,是追求一种神秘又美好的事物。这种希望是关于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性。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谈到《希望》的创作动机:“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鲁迅在进行文本创作时,聚焦于他们“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很平安”,暗示着这种存在的实感正在消散,正有抛向虚无的可能性。
暗夜意象代表着生命中的虚无感。暗夜就是当革命的激情消退、青春的光芒黯淡之后对外部环境中的虚无感的认知。具体到《希望》这一篇章的开头,“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呈现出一幅黑暗静寂的图景。接着又“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并“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最后发现“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从对暗夜的存在并抵抗到对黑夜是否真正存在的质疑,有着强烈的虚无色调。当然,文章最后一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与其说是“反抗绝望”的一种实践,不如说是面对虚无的一种主张和姿态。
意脉
通过意象构建,《野草·希望》展现了一种虚无与勇气并存的复杂意蕴,并为文本铺开了其意脉。在散文中,意脉通常指的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意义等内容的贯穿线索或主线。《野草·希望》意脉主要从思想上的无意义化、情感上的张力构建及意义上的诗意化观照来呈现。
在思想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革命的理解。革命原有的审美价值特质已经模糊和丧失,只是来“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对应到对革命形势的无力感。这是对《故乡》“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的思想承接,也是在革命的潮起潮落中对希望有无的茫然与未知心态。这种态度反映了鲁迅在时代变迁中的思想困境,这实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在革命落潮期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或许在社会面前,个体的希望似乎无足轻重。革命的主力军是青年,自晚清开始就流行“青年崇拜”的心理。鲁迅也曾从进化论出发对青年人寄予厚望,认为他们肩负着创造不同时代的使命。正是因为青年是政治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也就成了各类政党竞相争夺的对象,最终清党变成国民党青年对共产党青年的大清洗,所以鲁迅痛苦地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在情感上,对于孤寂和衰老的感知与青春意象的勾连,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巨大张力。这种情感张力的构建,一方面源于鲁迅对个人境遇的感怀,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忧思。自我的衰弱和对青年的怒其不争编织在《野草·希望》的纹理之中。他认为,青年人正在失去直面困境的觉悟,开始把复杂严肃的事情轻佻化,逃避沉重的思考或躲避苦重的社会事件,过去奋不顾身的勇气和与之改变的可能性正在消散。但这也和鲁迅自身的悲哀相联系,因为他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他自身的衰老与青年人的未老先衰联系在一起,在青春消逝和追忆青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拉扯。
在意义上,叙述者呈现出一幅在暗夜中观照意象之物的场景。适应了暗夜,那么暗夜还会存在吗?在这一自我质疑的独语形式中形成诗意化的观照,它的景象便是:带着勇气和若有似无的希望直面虚无的境遇。这也是鲁迅一贯的黑暗体验。周作人认为,“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这点出了支配鲁迅一生的一个思想侧面。鲁迅的思想侧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悲观主义,他对中国社会和民族的现状深感失望、绝望。但鲁迅的悲观主义并非消极的悲观主义,而是类似于尼采的积极和富于批判精神的悲观主义。他对现实的悲观与对民族国家的忧虑和责任感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鲁迅试图以“文坛偶像”的身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结语
在散文诗中,意象和意脉密不可分,意脉通过意象得以表达,意象则为意脉提供了更好的表达方式。《野草·希望》以意象为经,将思想的彷徨、情感的纠葛、意义的探寻熔铸一炉,呈现出虚无的意蕴及“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的勇气,彰显的是鲁迅的深邃思想和卓越才情。在社会变动、家庭失和的时期,周氏兄弟都经历了一段思想彷徨期,但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周作人转向构筑自己的园地,在“向下向广”的民俗学挖掘中加深了自己对于虚无观念的认知,这也为其后续的“历史循环论”“文艺无用论”做了铺垫。而鲁迅则在“虚无”的废墟上面,插上自己“反抗绝望”的大旗,在后续的杂文创作中践行自己的思想主张。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鲁迅.野草[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2]汪卫东.“虚无”如何面对,如何抗击?——《野草》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深度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01).
[3]黄健.灵魂的独语——《野草》鲁迅的心路历程[J].名作欣赏,2010(18).
[4]薛绥之, 韩立群.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M].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