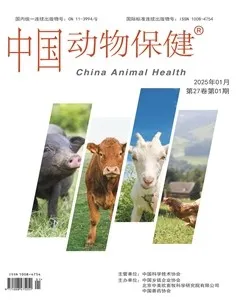非洲猪瘟防控及疫苗研发研究进展

摘要: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SFV)引起的一种高度传染性且高度致死性的动物疾病,主要影响猪类并可能影响其他与猪有经济联系的动物。本文阐述了非洲猪瘟的流行情况、病原学特点、传播途径、诊断技术、风险防控策略以及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总结了国内外在非洲猪瘟防控和疫苗研发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经验,并讨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结论强调了持续的研究对于控制非洲猪瘟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非洲猪瘟;疫苗研发;防控
2018年以来,非洲猪瘟疫情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暴发,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疫情的迅速蔓延不仅给全球猪肉供应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国际贸易、边境管理、食品安全及动物疾病管理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给疫区的农民、养殖企业以及相关的供应链参与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健康风险。鉴于非洲猪瘟的严重性和其对国际贸易及公共卫生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研究和开发有效的防控措施及疫苗成了当务之急。当前,虽然一些国家和组织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包括加强生物安全措施、提升监测和诊断能力以及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疫苗接种策略,但是非洲猪瘟的根除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疫苗的研发进展缓慢,目前还没有广泛可用的商业化疫苗来预防或治疗非洲猪瘟。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非洲猪瘟的流行状况、影响以及当前的防控措施和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并为该疫病的有效应对提供科学指导和策略建议。
1 非洲猪瘟的基本特性与传播特点
1.1 非洲猪瘟的病原学特点
非洲猪瘟病毒(ASFV)是一种大型的 DNA病毒,属于非洲猪瘟病毒科,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和生存能力,能在低温条件下保持感染性,并且通过不同的途径快速传播。早期研究表明非洲猪瘟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致命性,能够引起家猪和野猪的急性、发热性和高致死率疾病。病毒的传染性不仅体现在直接接触传播,还包括间接接触传播和气溶胶传播,其中直接接触传播是指通过与感染猪或感染组织的直接接触,而间接接触传播则涉及通过蜱虫、饲料等媒介的传播[1]。此外,非洲猪瘟病毒还能通过猪肉制品长时间存活,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2]。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非洲猪瘟病毒的基因组结构和基因组学特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病毒基因组编码多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涉及病毒的复制和免疫逃逸等关键生物学过程[3-4]。病毒的高毒力基因型可以导致高达100%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低毒力基因型虽然不会立即导致死亡,但会引起血清学改变,增加了疫情诊断的难度[1]。疫苗研发面临的挑战包括病毒的高度变异性和免疫逃逸能力,这使得疫苗的研发和应用变得复杂且充满挑战[5],但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商业疫苗可用。
1.2 流行病学特征
非洲猪瘟于1921年在肯尼亚被首次报道[6],随后该病迅速蔓延至欧洲、美洲等地区。在许多不同国家报告,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例如,为了防止全国性动物流行病,古巴在1971年杀死了超过50万头猪[7]。2011年,在俄罗斯联邦地区,超过30万头猪死于非洲猪瘟[8]。特别是自2018年8月在中国沈阳首次报告非洲猪瘟疫情后,该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涉及国家包括不限于俄罗斯、中国、越南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公共卫生风险,使ASFV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9-10]。针对非洲猪瘟的疫苗研发一直是国际上的研究热点。早期的疫苗研究表明,灭活疫苗对非洲猪瘟的免疫保护效果有限[11]。随后,基于非洲猪瘟病毒(ASFV)基因组的复杂性,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其他类型的疫苗,如基因缺失疫苗和重组亚单位疫苗[12]。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成功研制出一种基因缺失疫苗,并在实验室和田间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
果[13]。各国针对非洲猪瘟的防控措施包括加强边境检疫、提高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平、推广疫苗接种等。例如,欧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测和报告系统,能够快速检测到疫情,并向成员国发布警报[14]。中国政府也实施了生猪调运指导意见,要求生猪运输车辆必须严格消毒,并禁止在疫点区域内进行生猪交易[15-16]。
非洲猪瘟病毒主要通过病猪的血液、分泌物及排泄物直接传播,也会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饲料、水源、器具等间接传播[1]。此外,病毒在猪肉制品中的存活时间较长,增加了病毒的传播和扩散风险[12],泔水因其中可能携带大量病毒和细菌,也是传播途径之一[12]。最新的研究还提到,为了控制非洲猪瘟的传播,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严格的生猪运输规定,限制生猪跨区域的流动,并推广疫苗接种[17]。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助于减少非洲猪瘟的传播风险。
2 非洲猪瘟的诊断技术与风险防控
2.1 诊断技术的研究进展
早期关于非洲猪瘟的诊断主要依赖于传统的临床观察和流行病学调查,这些方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判断疫情的存在,但对于病毒性疾病的确切诊断存在局限性。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PCR技术的应用,大幅提升了对非洲猪瘟的诊断能力。例如,杨公立等人[18]通过流行病学研究,分析了非洲猪瘟的流行特点和风险因素,但具体的诊断技术在文中并未详细描述。进入21世纪,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诊断技术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例如,荧光定量PCR技术的应用,使得对非洲猪瘟病毒(ASFV)的检测更加快速准确。此外,LAMP技术因其操作简便、反应快速的特点,在非洲猪瘟的诊断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和间接 ELISA检测方法也在不断地优化中,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诊断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诊断方法的标准化、敏感性和特异性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等问题。此外,随着疫苗研发的进展,对诊断技术的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未来的研究也需要考虑与新技术的兼容性和整合性。
2.2 风险防控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面对非洲猪瘟的挑战,国内相关部门开始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防控策略。例如,郭莉[10]对非洲猪瘟在我国的风险防控研究中分析了国内ASF的潜在危险,并总结了国内ASF诊断的研究进展,强调了加强国内ASF诊断技术储备的重要性。随后,康亚男等人[15]进一步分析了我国非洲猪瘟的流行现状,并提供了疫苗研发进展的最新信息,同时也提出了预防ASF传入和蔓延的措施。最新的研究,如麦伟健等人[12],详细探讨了防控形势及防范措施,强调了提高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平的重要性,并指出了饲料监管在防控中的作用。尽管防控非洲猪瘟还存在许多挑战,如疫苗研发的不确定性和防控措施的执行难度,但国内的防控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保护国内生猪产业的安全与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例如,波兰和拉脱维亚在面临疫情暴发后,加强了疫情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并在边境设立了检查站以防止受感染的猪只及其产品进入国内。此外,国家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以提高对ASF的防控能力。随后的研究中,芬兰、德国等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通过设立边境关卡来控制疫情的传入。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涉及政府部门,还包括了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共同努力减少ASF的引入和传播。
3 非洲猪瘟疫苗研发的进展与挑战
3.1 疫苗研发的历程
早期的研究集中在灭活疫苗的开发上,但由于非洲猪瘟病毒(ASFV)的复杂性,这一研究方向并未取得满意的成果。随后,研究者们转向了减毒活疫苗的研发,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这种活疫苗的安全性和现场应用的挑战仍然存在。进入21世纪,亚单位疫苗的研发成了新的方向。亚单位疫苗基于ASFV的单个或小组基因或蛋白质,相比于活疫苗,这种疫苗被认为更安全。例如,有研究利用p30、p54及p72蛋白制备的亚单位疫苗,能够为猪群提供部分的免疫保护。然而,由于 ASFV基因组庞大,单一蛋白制备的疫苗抗体水平较低,提示了需要进一步开发多亚单位的联合疫苗以提高抗体水平。最近的研究还包括了基于基因工程手段制备的疫苗,如基因缺失疫苗和核酸疫苗。例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成功研制出一种基因缺失疫苗,并在实验室和田间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此外,核酸疫苗的研制正处于起步阶段,这种疫苗通过在细胞内完成特定的转换和翻译来激发机体的免疫应答。非洲猪瘟疫苗的研发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进步的过程,从灭活疫苗到减毒活疫苗,再到亚单位疫苗和核酸疫苗,每一步都反映了对安全有效疫苗的迫切需求和科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有望开发出更加有效的疫苗以防控非洲猪瘟的流行。
3.2 疫苗研发中的科学问题与挑战
随着对非洲猪瘟病毒认识的深入,科研人员开始探索疫苗研发的新途径,虽然在非洲猪瘟的防控及疫苗研发方面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如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和合成生物学技术等。但是目前还面临许多挑战,包括疫苗研发的技术瓶颈、对病毒的认识不足以及防控措施的实施难度等。要有效控制该病的传播和暴发,仍需要持续的研究和技术创新。针对非洲猪瘟的疫苗研发,邵治国等[13]分析了疫苗研发的挑战与对策,指出虽然对非洲猪瘟病毒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升,但疫苗研发的难度仍很大,面临许多技术瓶颈,包括病毒蛋白的复制和转录调控不清楚等问题。此外,麦伟健等[12]的研究强调了提高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平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推广疫苗接种的策略。这些研究表明,虽然在技术和策略上取得了进展,但要克服现有挑战,实现疫苗的商业化应用,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从徐春晓等[17]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针对非洲猪瘟防控形势及防范路径的探讨强调了基层防疫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以及监测体系的构建。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需要技术和设备的支持,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和专业人员的培训。因此,非洲猪瘟的防控及疫苗研发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过程,需要国内外的科研力量共同努力,不断优化防控策略和疫苗研发技术,以期达到有效控制疫情的目的。
早期的研究集中在灭活疫苗的开发上,但这些疫苗并未显示出有效的免疫保护效果。随后,研究者们转向了更有希望的疫苗类型,包括亚单位疫苗、核酸疫苗、基因重组疫苗等。邵治国等[13]对非洲猪瘟的防控和疫苗研发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指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亚单位疫苗的研究进展则在王涛等[5]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他们探讨了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结合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来加速疫苗研发的可能性。此外,核酸疫苗的开发正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还存在许多挑战,但已有的研究表明,通过将编码病毒抗原基因克隆到真核载体中,可以有效激活宿主的免疫应答。最近的研究则集中在寻找能够提供更安全保护的亚单位疫苗上,如华冰洁[2]的研究中提到,虽然亚单位疫苗的开发具有很大的潜力,但需要鉴定更多的ASFV保护性抗原,并开发出新的免疫佐剂以提高疫苗的效力。此外,马艳荣[16]的研究中也强调了生物安全管理在防控非洲猪瘟中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培育抗ASF病毒猪的研究进展。
尽管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包括疫苗研发的高成本、技术难度以及对病毒认识的局限性等,但研究者们正通过多学科交叉合作、利用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合成生物学方法,积极探索有效的疫苗开发策略。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关注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成本效益比,以实现广泛的应用和疾病的根除。
4 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综合了国内外在非洲猪瘟的诊断技术、风险防控以及疫苗研发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尽管存在诊断技术的局限性、防控措施的挑战以及疫苗研发的技术难题,但各国科研机构和企业已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诊断技术方面,基于核酸的检测方法,如PCR技术,已成为早期诊断的重要手段。此外,生物安全措施和生物安全柜的使用在控制疫情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在风险防控策略上,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成了有效应对跨国疫情的重要策略。疫苗研发方面,虽然目前还没有商业化的ASFV疫苗,但多个候选疫苗的研发正在进行,包括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 DNA疫苗等多种技术路径。研究成功不仅为ASFV的防控提供了新的工具,也为未来的疫苗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不仅加深了对非洲猪瘟的认识和理解,也为制定更有效的防控策略和疫苗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不仅对提升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找到更有效的防控和疫苗研发策略,以减轻甚至根除非洲猪瘟对畜牧业的
影响。■
参考文献:
[1] 周伟伟,唐伟,顾蓓蓓,陈瑞辉,陈未.基于非洲猪瘟研究现状下的风险防控研究[J].中国兽医杂志,2017,53(05):112-114.
[2] 华冰洁.非洲猪瘟的研究进展[J].中国动物保健,2024,26,300(02):7-8.
[3] 王玥宁.非洲猪瘟病毒基因组密码子偏性分析及目的蛋白密码子优化表达[D].扬州:扬州大学.2024.
[4] Jie Yang,Zhiwei Shao,Xin Zhao,et al.Structures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topoisomerase complex and their implications[J].Nature Communications.2024,15:1-10.
[5] 王涛,孙元,罗玉子,仇华吉.非洲猪瘟防控及疫苗研发:挑战与对策[J].生物工程学报,2018,34,240(12):1931-1942.
[6] Montgomery,R.E..On a form of swine fever occurring in British East Africa (Kenya Colony)[J].Comp.Pathol.1921,34:159-191.
[7] Costard,S.,Mur,L.,Lubroth,J.,Sanchez-Vizcaino,J.M.amp;Pfeiffer,D.U.Epidemiology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J].Virus Res.2013,173:191-197.
[8] Gogin,A.,Gerasimov,V.,Malogolovkin,A.amp; Kolbasov,D.African swine fever in the North Caucasus region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years 2007-2012[J].Virus Res.2013,173:198-203.
[9] Zhou,X.T.et al.Emergence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China[J].Transbound.Emerg.Dis.2018,65:1482-1484.
[10] 郭莉.非洲猪瘟在我国的风险防控研究[J].畜牧兽医科学.2019,38(02):75-76.
[11] 胡思腾.非洲猪瘟病毒的研究进展[J].中国畜牧业.2024,11:61-62.
[12] 麦伟健,龙玄,谭叁.非洲猪瘟的病理与防控措施研究[J].农村科学实验.2024,(01):165-167.
[13] 邵治国,张素荣,杨明星,杜爱英,赵晓倩,宋凯,崔菁婧.非洲猪瘟防控及疫苗研发——挑战与对策[J].中国畜禽种业.2019,15(08):64.
[14] 王鹏达.非洲猪瘟的流行病学与防控[J].养猪.2023,187(02):110-113.
[15] 康亚男,刘涛,张小波,柳珊,吴雅清,赵玉龙.我国非洲猪瘟疫情现状及防控措施[J].中国猪业.2021,168(04):57-60.
[16] 马艳荣.非洲猪瘟流行病学及防控措施现状[J].中国畜牧业.2022,600(09):119-120.
[17] 徐春晓,唐振.2021.非洲猪瘟防控形势及防范路径探讨[J].今日畜牧兽医.2021,441(06):14-16.
[18] 杨公立,张志诚,非洲猪瘟流行病学及其风险因素分析[J].猪业科学.2014,31(05):24-27.
收稿日期:2024-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