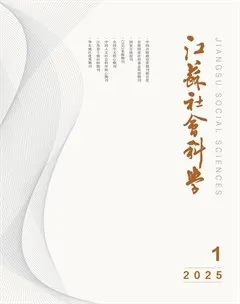宗法伦理起源新探
内容提要 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是宗法伦理的源头。在伦理维度上,殷代祭祀先公、选祭与周祭先王的宗教性活动,强化了族长(商王)的权威,凝聚了宗族共同体。西周初期,祖先崇拜发展为作为理性制度设计的宗法制,并且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而形成了宗法分封制,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随之确立,孝、友成为核心伦理规范。春秋时期,孔子继承了孝友观念,构建了以孝悌为基础规范的儒家伦理。其后,儒家学派提出了五伦、三纲、六纪等观念,宗法伦理成为儒家伦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宗法伦理与君主专制政治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另一方面,宗法伦理在儒家仁爱思想的强烈影响下,以血缘伦理为道德进阶的基础,超越了血缘之爱,不断追求“亲亲、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天地一体之仁”的道德理想。这也是儒家伦理宝贵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 宗法伦理 祖先崇拜 孝友 宗法分封制 仁爱
徐嘉,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和“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礼乐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23AZX00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人民聚族而居,伦理以家族为本位,故宗法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内容。甚至可以说,宗法伦理的起源与中国古代伦理的起源几乎是同一个问题,其孕育、形成与扩展,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伦理的形态与作用机制,而且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重要特征。随着100多年来考古发现与殷商史、西周史研究的进展,现在我们有条件循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依靠甲骨文、金文与可靠的传世文献,追索宗法伦理形成的历史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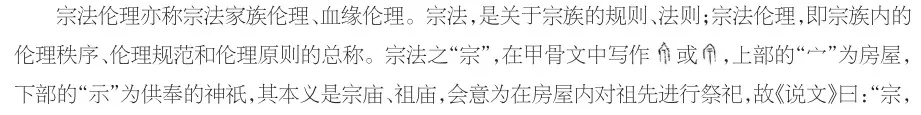

中国的宗法伦理起源于何时,又是如何起源的?宗族、宗法制、宗法伦理是密切关联的。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论断:殷商“无嫡庶之制”,周人始有“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1]。这就是说,宗法制起源于西周。而现在的研究表明,宗法制确实是周代社会的重要制度,是一种独特的“血缘-政治”制度系统,其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规定了宗族内的尊卑秩序、权力格局。具体而言,其包括大宗小宗之分、嫡庶之别、财产的归属与继承、宗庙的排列(“辨宗庙之昭穆”)等等。在西周时期,宗法制与宗法伦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在伦理学领域,一般笼统地认为宗法伦理产生于西周;但是,随着100多年来甲骨文研究的进展,殷商时期的思想文化也越来越清晰,至少在殷商武丁(第22位商王)[2]时代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祭祖活动,并产生了具有伦理意味的观念。因此,我们认为,宗法伦理的源头在殷商时期,从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到西周宗法分封制的建立,宗法制与宗法伦理相伴而生,其形成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轨迹。
一、祭祀先公的伦理意义
祖先崇拜是宗法制的先导,亦是宗法伦理的源头。殷人把祖先视为具有超自然力的神灵,认为其灵魂可以庇佑本族成员、赐福后代,并通过祭祀活动与祖先沟通与交流,表达敬畏,祈求福祐——这是一种典型的祖先崇拜。根据陈梦家先生的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记录的祭祀对象,与传世文献《周礼·大宗伯》所记载的祭祀对象是相当一致的,都包括天神、地示、人鬼三类[3]。天神中最重的是“帝”,这是殷人所信仰的至上神;地示指山、川、河、岳、四方等自然神灵;而人鬼指逝去的祖先。研究表明,在三类祭祀中,对祖先的祭祀压倒了天神崇拜[4],祖先祭祀方面的卜辞多达15000余片,超过其他任何一类卜辞的数量,这是殷末重视血缘祖先的有力证据[5]。
商人的祖先崇拜表现为种类繁多的对祖先神的祭祀活动。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将殷代的祖先分为先公与先王两类:自契始,大乙(成汤)之前的14代祖先称先公;成汤灭夏成立殷王朝后,成汤至帝辛(纣王)的30代祖先称先王。现在,司马迁列举的14位先公已不可考,而其所记载的30代先王世系则在甲骨文中得到印证[6]。最早的先公在起源处渺渺茫茫,史影、传说、神话交织在一起。盘庚(19代商王)迁殷至帝辛(末代商王)共273年,共有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12王。甲骨文作为殷末的历史记载,主要是从武丁到帝辛时期的占卜记录。在卜辞中所见对于祖先的祭祀中,武丁至文丁时期大量祭祀高祖先公,后期则祭祀先王。就祭祀本身而言,对于远祖先公的祭祀与对于近祖先王、先妣的祭祀,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后者采用了非常规律的“选祭”与“周祭”的祭祀方式。而整个殷商时期祖先崇拜的规律性发展,体现了“宗法”的形成与走向成熟,虽然还远未形成宗法伦理,但已有了伦理的功能,并蕴含了宗法伦理的萌芽。
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被频繁祭祀的最早的先公被称为“高祖夒”。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认为夒是殷祖帝喾,据称是最早的商王[1]。虽然对于夒是否是帝喾古史学家们观点不一,但其一致认为这是商人的最早的祖先。根据“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库”进行统计,在《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与《小屯南地甲骨》(以下简称《屯南》)中,祭祀“夒”的次数达到85次,略举几例:
叀高祖夒祝用,王受又(祐)。(《合集》30398)这是卜问,对高祖夒用“祝”(祈祷)“用”(杀生)的祭祀,问能否使商王得到护佑。
□戌贞,其告秋冓于高祖夒。(《合集》33227)这是贞问,问秋天是否可用“冓”这种祭祀来祭祀高祖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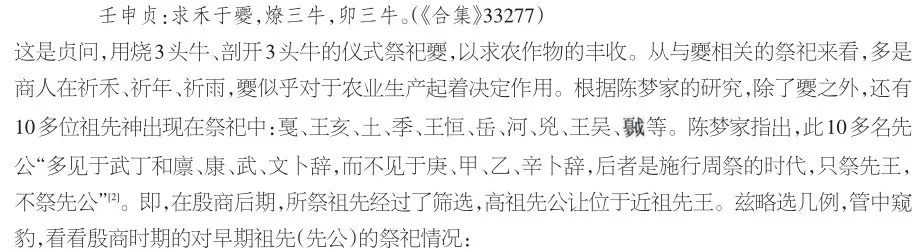
(1)庚午卜:求雨于岳。(《合集》12855.2)
(2)丁酉卜:其求年于岳,惟羊。(《屯南》689)
(3)戊寅卜,争贞:求年于河。(《合集》10084.1)

(5)辛卯卜:甲午求禾上甲,三牛,用。(《合集》32322)
以上5则卜辞都反映了商人祭祀祖先的情况。根据陈梦家、常玉芝等学者的研究,“岳”与“河”都是祖先神,而非自然神[3]。(1)是通过卜问向岳求雨。岳是商人的先公,最早的祖先之一。(2)是以献羊的方式向岳求“年”。“年”,上面是“禾”,下面是“人”,即“秊”(“年”的异体字),表示禾谷成熟,人负禾谷,故《说文》曰:“秊,谷熟也。”所以,本则卜辞是向先公岳祈求农业丰收。(3)是向先公河祈求农业丰收。(4)是卜问,问是不是先公王亥作祟不降雨。(5)是以杀3头牛的祭祀仪式向先公上甲“求禾”,“禾”为谷物丰收,“用”为杀生之祭。陈梦家先生列举的受到频繁祭祀的祖先神中并没有上甲,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甲骨学研究的深入,可以确认的商人的先公远祖越来越多,上甲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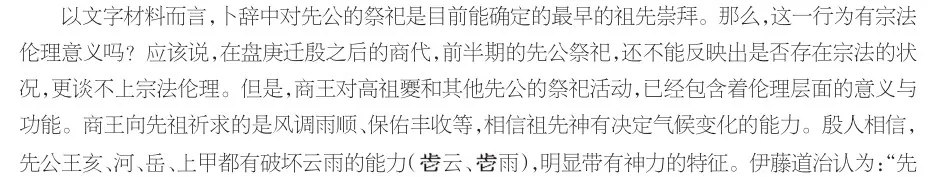

二、“选祭”“周祭”中的宗法伦理性
在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前期的祭祀主要是对远祖先公,而后期的祭祀则名目繁多,祭祀的对象包括众多先王。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我们只关注两类重要的祭祖行为——“选祭”与“周祭”。这两种祭祖活动都对宗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出现了清晰的宗法伦理的端绪。
所谓“选祭”,是指在一次合祭中选择若干祖先(直系或五世以内的先祖)进行祭祀,这样的祭祖活动,有具体的目的,每次祭祖因事而定,没有确定的时间,陈梦家先生称之为“选祭”[4]。选祭从武丁(第22代商王)时代出现,武丁、祖庚(第23代商王)时期最多,一直延续到殷亡。选祭多是为了问询吉凶、祈请、祓禳。其中,祈请之祭是为了实现某种愿望,而“祓禳之祭”,孔颖达疏“祓禳皆除凶之祭”,即祈求避免祸患。祖先神会降下灾祸,如干旱、饥馑、疾病与败仗。略举几例如下:
(1)乙丑,在八月,酒,大乙牛三,祖乙牛三,小乙牛三,父丁牛三。(《屯南》777)
(2)庚寅卜:辛卯奏舞,雨?
庚寅卜:癸巳奏舞,雨?
庚寅卜:甲午奏舞,雨?……(《合集》12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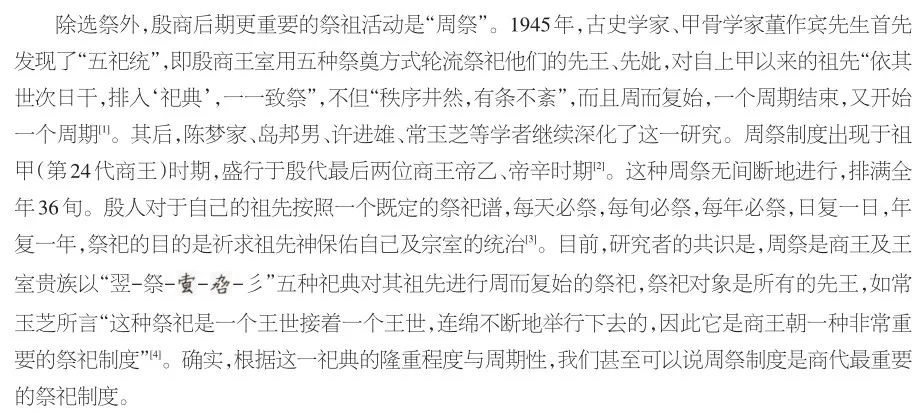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殷人祭其先(祖)无定制。”[5]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始于西周。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宗法制滥觞于商末的观点,才是更符合历史的。根据常玉芝的研究,殷人对早期先公的祭祀与《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出入较大,而先王时代的祭祀与其记载的吻合度相当高。在周祭中,对先王的祭祀次序是以他们的即位次序进行排列的。根据现在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在周祭的31位殷先王中,有27位的祭祀次序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一致,而相异之处也有可信的原因,如曾被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的,在周祭中也安排了他们的祭祀位置,而在《史记》中他们是不被排入世系的[6]。并且在周祭制度中,由周祭先王、先妣的祭祀次序可以看到,先王、先妣地位不同,“到了商代晚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已大大地低于男性。这时已有了贵贱嫡庶的宗法制了”[7]。此外,根据陈梦家先生对《殷本纪》与卜辞对照考证,商王的继统法,子继与弟及并用,传兄之子与传弟之子并用,兄弟同礼而有长幼之别,兄弟即位以长幼为序;虽无嫡庶之分,但凡子继王位者其父得为直系。虽然复杂,但有着严谨的规制。而到了殷商最后的四个商王时期,“武乙以至帝辛传子,实与周制相同”[8]。这一发现,为判断宗法伦理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在殷末,选祭与周祭并存,正好体现了不同的伦理原则都是宗法伦理的重要源头。根据常玉芝的研究,“(选祭)重近世而轻远世,亲直系而疏旁系”[9],伊藤道治也发现,在武丁(商代第22位先王)时期的卜辞中,先公、先王在祭祀中还没有什么区别,但到了祖甲时期,“上甲以前的先公被排除在这种严格的祭祀之外”[10]。高祖、先公逐渐退出被祭祀的行列,近祖先王得到重视,非直系的祖先逐渐被排除在外,这似乎更重视“亲亲”的原则。而周祭已经没有明确的目的,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周祭是对所有祖先的祭祀,体现了“尊尊”的原则[11]。所以,选祭与周祭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王权合法性的建构,亦是宗法与政治紧密关联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周祭更受重视,祈请、祓禳不再是祭祀的目的,这也意味着宗教性的祖先崇拜趋于弱化。所以,虽然从形式上看,周祭制度比其他时期对祖先神的祭祀都更隆重而复杂,但实际上,这是宗法秩序政治化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
总之,殷代后期对先王的选祭强调了直系祖先的重要地位,周祭给予所有祖先的尊重。一方面,这促进了祖先崇拜向宗法制转变。祖先崇拜与宗法制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具有宗教意味的信仰,后者是一种理性的制度设计。在祖先崇拜中,后人寄希望于祖先神的护佑。而宗法伦理是共同体的内在规范,对于祖先的恭敬是为强化当下的伦理秩序。另一方面,选祭与周祭所遵循的“亲亲”与“尊尊”,成为宗法伦理的根本原则。其在殷末的伦理功能亦十分明确,祭祖出于政治目的,但依靠的“亲亲”与“尊尊”,其既是政治的要求,亦是伦理的原则。其于商王是政治也是伦理,于宗族则是伦理意义高于政治功能。祖先神是王权合法性、政治秩序的依据。而商王通过与逝去的祖先沟通祈求祖先降福氏族,客观上起到了凝聚宗族、保持秩序、不断唤起宗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而就宗法伦理的起源而言,对于宗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是产生伦理观念的起点。
三、宗法分封制下的宗法伦理
西周初期,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标志,宗法制形成,并且宗法制与政治上的分封制相结合而形成了宗法分封制[1]。这一特殊的治国方式,不但使宗法制得到强化与推广,而且严格意义上的宗法伦理最终形成。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宗法伦理的形成,既有历史延续性,更有理性的设计与建构。
关于宗法分封制,《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的后代把本族的姒姓贵族分封到12个地区建立封国,但此说难以证实。而《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氏),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左传》《尚书》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朱凤瀚先生根据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殷代社会的宗族制已有相当发展,商王朝是通过各级宗族族长进行统治的。当时的宗族组织按宗法血缘关系区分为“宗氏”(大宗之族)和“分族”(小宗之族)等层次[2]。可以认为,殷代晚期,宗法分封制度已有雏形,殷代贵族以宗族族长身份可以世袭官职,而这些宗族与殷王具有血缘关系。至西周,《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分封。《左传》中亦多次提及宗法分封制,其记载事件去周未远,而且有大量青铜器上的铭文可以进行佐证,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参照《左传》中的记载对宗法分封制进行说明: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使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左传·隐公八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左传·定公四年》)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
在第一则文献中,姓、氏、宗、族各有所指:姓是同祖的血缘群体;氏既是姓的分族,亦是政治单位、世袭官职的称号;宗是按祖先祭祀的礼仪进行的分级序列;族初指同一旗号下的战斗单位,百家为一族,春秋时指诸侯的非嫡系后人[3]。《左传·隐公八年》载,鲁国的司空无骇(姬姓,展氏,名无骇)去世,大臣羽父为无骇请求谥号和族氏。按照周制,周天子分封诸侯,根据他原来的氏族赐以“姓”(“因生以赐姓”),又封以土地而赐以氏名(“胙之土而使之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其后人又以此作为族氏。为官世代有功,就可以官名为氏,也可以封邑为氏。鲁隐公命令以无骇的字作为族氏,就是展氏。
周武王翦商之后,即实行分封制管理天下,而成康之世成为封建亲戚的核心时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一是分封古帝王后人,即从法理上承认各氏族的合法性。这包括殷商旧部,如商纣王帝辛之子武庚封于邶。二是分封周人子弟(同姓)与贵戚(异姓)。其中,周王室的子弟为姬姓,如周公姬旦被封于鲁,而与周联姻的诸侯、功臣非姬姓,以姜姓为代表[1],如姜尚(周武王的岳父)被封于齐。在这三类分封中,虽然有怀柔殷商旧族的政策,但分封的诸侯,以姬姜二姓为主[2],也就是说,这种分封的主体部分,是根据宗法关系实行的分封,是“宗法分封制”,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臣属,本来就是血亲与姻亲的关系,而不是新产生的投靠与依附关系[3]。
具体而言,天子既是周王,亦是“天下之大宗”。天子分封诸侯(“天子建国”),诸侯既是一国之主,亦是一国之大宗。诸侯分封卿、大夫(“诸侯立家”),卿以众子为“侧室”(官名),大夫以宗室子弟为“贰宗”(官名),侧室、贰宗作为卿、大夫的支族,既是封邑的长官,亦是采邑内之大宗。卿大夫分封士,士宗于上级卿大夫,以其家族子弟为隶役。士以下不再分封,庶人、工、商亦不再分尊卑,而以血缘亲疏为若干等级之分别。当然,诸侯、卿、大夫亦有不同等级,血缘远近成为一个重要的分封原则。需要说明的是,宗法分封是就西周分封的主流而言。对古代帝王如尧、舜的后人的分封以及“元子就封”[4]等宗法分封的特殊形式的存在,并不影响宗法分封的核心地位。总之,西周分封制度是宗法制与分封制的高度融合,是以宗法秩序为原则的分封制。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天子诸侯则宗统与君统合”,“由亲之统言,则天子、诸侯之子,身为别子而其后世为大宗者,无不奉天子、诸侯以为最大之大宗”[5]。周人宗族通过逐级的宗法分封,使“宗统”与“君统”合一。“宗统”是宗族组织系统,要求宗族成员尊祖敬宗、遵守等级隶属的规则。而“君统”则是政治组织系统,要求政治上的等级隶属关系。各级宗族组织中的族长、家长、宗长,是各级政治上的各级官员[6]。各国国君之间既是同僚,又是宗亲。同姓大国国君被称为“伯父”,异姓大国国君被称为“伯舅”,同姓小邦国君被称为“叔父”,异姓小邦国君被称为“叔舅”,由此,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形成了伯、叔、舅、侄、甥的亲戚关系——血亲与姻亲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血缘-政治”共同体。故郭沫若说:“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所谓国,其实仅仅是一个大宗或小宗,所以动辄便称万国万邦。”[7]周代的宗法分封制,除《左传》《诗经》《尚书》等早期文献外,100多年来出土的大盂鼎、宜侯夨簋、史墙盘等青铜器,亦十分确实地记录了西周时期分封的情况。
那么,在宗法分封制下,“宗统”与“君统”合一时,宗法伦理的结构与形态又是如何呢?这里需要明确一点,我们现在所言之“宗法伦理”,在西周时期是核心性的“礼”,包括(刑)法、政治、伦理的重叠规范和要求。家是伦理实体,国是政治实体,而宗法伦理既是家族秩序的伦理要求,亦是国家社会的等级原则。比如孝友,于宗法家族,是伦理规范,于政治,则是国家的典章制度,而违背孝友的要求,乃是众恶之首,要受到严厉的刑罚。就现代意义上的伦理而言,宗法伦理有如下特征:
首先,宗法伦理的原则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可以说,宗法伦理的诸多规范、准则,宗法家族的伦理秩序,皆以此四项原则为指南。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有一著名论断:“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1]其中,“丧服之制”的大纲,就是以上四项原则。此四项要求,出自《礼记·丧服小记》中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现在,我们之所以把丧服之制的原则视为宗法伦理的原则,是因为丧服之制与宗法伦理秩序具有同一性。王国维先生研究认为,西周制度的首要革新是嫡长子继承制,因此才有宗法制[2],为了维护宗法制,才有了丧服之制,丧服之制本身就是巩固和强化宗法伦理秩序的规制,因此,丧服之制的原则实际上是宗法伦理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四项原则出自晚期文献《礼记》,但从《尚书》《诗经》《左传》等早期文献以及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来看,它们皆符合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
那么,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作为宗法伦理的原则,具体何指呢?根据孙希旦《礼记集解》的解释,亲亲是“下治子孙”,即厘清对子、孙的亲疏顺序;尊尊是“上治祖祢”,即尊崇祖父、父亲、亲戚长辈;长长是“旁治昆弟”,即兄弟之爱;男女有别指所娶他姓之女、已嫁他姓之女以及未嫁之女的家族地位和伦理规范。这些复杂而细致的区分,其实质是根据宗法家族内的地位、尊卑而确立相应的伦理规范,体现了宗法家族内的伦理秩序。《礼记·大传》曰:“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这段话对以“亲亲”为起点的宗法伦理具有总结性。人之道的第一要义是亲亲。以爱亲之心为心,上推而尊祖,尊祖而敬宗子,然后能聚合族人,宗庙祭祀秩序井然。卿大夫宗庙与君之社稷相为休戚,故宗庙严必重社稷。其实,“亲亲—敬宗—收族—宗庙严—重社稷”并没有严格的逻辑顺序,只能说宗法政治、宗法伦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浑然一体、相辅相成,是一个绵密的有机整体。
其次,“孝”与“友”是宗法伦理的核心规范。就传统文献而言,《诗经》《尚书》中保留有反映西周时期孝友观念的记载,最重要的是《尚书·康诰》中的记载:
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这是西周初年,周公摄政时告诫其弟康叔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以孝、友为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西周宗法伦理的特点——这是宗法分封制格局下的“政治-伦理”的要求:周王为大宗,大宗之下,非嫡庶子即昆弟。“善事父母者”为孝,“善兄弟曰友”,故而孝与友成为维系政治格局与伦理秩序的核心规范。而不孝不友必然是“元恶大憝”,最大的恶,一定要“刑兹无赦”,严加惩罚。除传统文献之外,最直接的材料来自青铜器铭文。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历方鼎,其铭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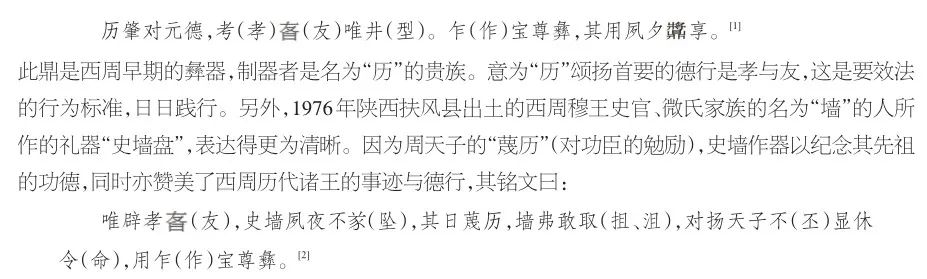
此段文字大意是,史墙之君周穆王(或者史墙之父乙公),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使得史墙不敢懈怠,勤于执事,史墙对于周王的嘉奖不敢自满,故制此盘以感恩天子。值得关注的是,此铭文前一半颂扬了西周王族的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文功武德,后一半叙述家族先祖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的功劳。历数周王宗族与本宗族的传承,从而突出了孝、友在宗法伦理中的重要性。可以说,西周时期的进步在于,商人祭祖主要是出于对祖先神会作祟于生者的畏惧以及祖先降福、保佑子孙的愿望,但西周贵族祭祖的主要原因则是认为祖先有德,此德为政治上的作为与品行。这无疑是一种更具道德理性特征的思想观念。
西周时期的孝、友不但是宗法伦理的核心规范,亦是整个社会的核心要求。以孝友治天下,与秦汉以后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差异颇大。“忠”字出现较晚,始见于战国时的中山王厝鼎[3],虽然《尚书·祭仲之命》有“惟忠惟孝”的说法,但“忠”应该不是西周时的主要的伦理规范。“忠”的初义是“尽心曰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在《论语》中,忠的基本义是尽心竭力,尤其是对上级官吏忠于职事[4]。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确实是孔子提出的伦理规范,但是,在诸侯国林立的春秋时期,此“忠”与后世对君主一人尽忠的思想有较大差别。唯忠一人之“忠”,是在宗法分封制解体、君王与各级官吏没有宗法关系之后,才从根本上受到推崇。总之,孝与友已经可以满足宗法分封制下维护国家秩序的要求,是西周到春秋时期宗法伦理的核心规范。
正因为实行宗法分封制,所以不但天子与诸侯存在宗法关系,而且诸侯、卿大夫、士与庶人普遍存在宗法关系[5]。宗法伦理所规定的伦理秩序不是平等的,或者说平等不是宗法伦理的要义。其中所蕴含的等级制,是西周礼制的本质。《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这种世卿世禄制,是国家政权机构宗法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西周春秋时期,从周王室到卿大夫的“家”,每一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不同等级的世袭贵族组成。具体来说就是:一是天子、诸侯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这是根本性的原则,决定了政治上的尊卑,并衍生出宗法上的亲疏之别、居丧期间的“五服”之制,进而成为政治上分封制的依据。二是“庙数之制”,即天子七庙,诸侯、大夫、士的庙数依次递减。这既是等级制度,又强化了宗法家族的组织结构,其依托的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原则。三是“同姓不婚之制”。王国维解释说:“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1]即以伦理的方式有机地联系各宗族,政治结构采用了凝聚家族的伦理机制,政治与血缘伦理高度融合,这就是“家国同构”。所以,以宗族结构为根据的宗法伦理,决定了王朝的传承、疆域的分封等国家大事,并且下贯至各级贵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政治秩序。因此,奠基于宗法伦理之上的国家制度,具有政治权力分配和血缘伦理约束的双重功能。可以说,西周时期,宗法制因分封制而达鼎盛,宗法伦理也因此成为西周各项制度的核心。
四、宗法伦理的血缘性与超越性
西周时期的“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决定了宗法伦理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当宗法分封制解体,宗法伦理便逐渐摆脱了对政治的绝对依附,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意义形态,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宗法伦理形成于春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学派对宗法伦理的演变、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简言之,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使宗法伦理具有了超越性的精神气质,展现了一种由家而国、普爱天下的情怀。
顾颉刚指出:“大国便是最大的家,小国便是次大的家,卿大夫便是再次一等的家;家国一体,家指人众,国指疆土,只是一事的两面,所以家可以叫做国,国也可以叫做家,又不妨拼合起来而叫做国家。”[2]因此,西周的宗法伦理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亲亲、尊尊的原则,孝友的规范,不仅是宗族内部的伦理秩序的要求,更是政治行为的准则。但是,西周时期实行的宗法分封制发展到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名存实亡。诸侯之间的纷争与吞并不断,秩序井然的礼乐制度开始崩坏,不但周天子已弱于诸侯,诸侯也发生了权力下移的情况,卿大夫专政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从历史进程来说,春秋末期,宗法分封制下的“领主制”逐渐转变为“郡县制”,“世卿制”转变为“客卿制”,甚至“陪臣执国命”现象亦大量出现。当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不再结合,宗法制逐渐成为越来越独立的社会制度,严格意义上的宗法伦理体系日趋成熟。
首先,儒门学人继承并发展了西周宗法伦理的核心规范。春秋时期,伦理规范体系已逐渐成熟。《左传·隐公三年》曰:“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与西周时相比,君臣一伦日益受到重视,与宗法伦理一起构成了伦理规范体系的主要内容。如果说,西周时期的宗法伦理的核心是孝与友,那么,在儒家学派的影响下,西周时期的宗法伦理的核心要求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论语·学而》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悌者,“善兄弟也”,即敬爱兄长。所以,孝悌与孝友同义。在这一点上,孔子似乎继承了西周以来伦理规范,没有改变。其实,就宗法伦理思想而言,孔子强调的是父子与兄弟两伦。而孟子提出了五伦:“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相较于西周与春秋时期,夫妇一伦受到了明显重视。可以说,在儒家学派的影响下,宗法伦理提高了“夫义妇顺”的重要性,并使其成为新的宗法伦理的核心规范。
其次,“三纲”的绝对地位决定了汉代以后宗法伦理以父子、夫妇两伦为核心规范。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施行后,“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阳为尊、阴为卑被提出,三纲之说已经形成。在东汉王朝的官方文件《白虎通》明确宣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后,三纲成为大一统君主专制秩序的核心伦理规范[1]。从五伦到三纲,双向互动的伦理规范变成了单向绝对的伦理要求。按贺麟先生的观点,五伦是人生中正常而永恒的伦理关系,三纲是五伦的最高要求[2]。也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人生无可回避的主要伦理关系是五伦,宗法伦理于五伦中有其三。而在父子、夫妻、兄弟三种关系中,最根本的是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汉代时,稳定、专制的大一统国家形成,宗法伦理规范日益完备,《白虎通义·三纲六纪》曰:“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可见,三纲六纪是以宗法伦理为中心,上及君臣,下涉朋友,旁及师长。君臣如父子,朋友如昆弟,师长如长辈。质言之,父子、夫妻的绝对尊卑关系是宗法伦理的内核。
最后,宗法伦理所遵循的区分亲疏远近的仁爱观念,深刻地受到儒家推己及人思想的影响,既依循爱有差等,又有超越血缘关系而博爱天下的情怀。儒家的仁爱观念,奠基于孔子。根据杨伯峻先生的研究,春秋时期,主流的制度与思想观念是“礼”。《左传》言“礼”共有462次,言“仁”不过33次。而在《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却以“仁”为核心[3]。“仁”的基本义是“爱人”,所爱之人始于孝、悌,仁或仁爱的本义是等差之爱,根据血缘关系而有亲疏远近之别。而儒家伦理的可贵之处在于,要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将“爱人”推广开来。“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乃至“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这一仁爱的推广方式,到宋明理学时,发展为一种博大的爱。张载《西铭》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即是著名的“民胞物与”,人人皆是同胞手足,万物皆为同类。至王阳明,仁心遍及天地万物,其《大学问》云:
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仁爱之心表现为怵惕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等。可以看出,自孔子到王阳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仁爱思想的超越性一以贯之。因此,宗法伦理固然有尊卑、有主从,有血缘关系的天然边界,但是儒家伦理有着无限的博爱之心,立足于血缘伦理,而又不断突破血缘关系的限制。黄建中先生指出:“所谓五伦,属家者三,君臣视父子,朋友视昆弟,推之则四海同胞,天下一家。”[4]宗法伦理的扩展,使普天之下的同胞依差序格局而为一家。不止于此,儒家伦理还将仁爱推广到一切生命乃至万物。宗法伦理的仁爱之道虽然按顺序扩展愈远愈难,却是儒家伦理所追求的伦理精神。
五、结语
陈寅恪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Eidos者。”[1]陈氏此言中国文化,其实是指由古代中国社会结构所决定、所要求的伦理形态。君主专制、聚族而居、农业经济共同决定了核心的伦理规范是君权与父权至上(夫权从属于父权)。而宗法伦理的成熟与稳定,是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一方面,中国社会以农立国,以家族为社会基本单位最符合农业生产方式,故家族成为中国社会的天然的实体,父权稳定而家族安定、社会有序。另一方面,王族(皇族)以宗法伦理原则处理政治秩序问题,亦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西周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与殷代中期“九世之乱”的历史教训密切相关——没有严格宗法制导致了商王仲丁以后由王位纷争引发的百年动荡,这是商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故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指出:“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2]古人并非不知立贤,然而无可争议的嫡长子继承制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所以,中国古代的宗法伦理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不论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还是孝友、孝悌的核心伦理规范,以及五伦、六纪、三纲,不但皆具政治与伦理的双重性质,而且宗法伦理的发展、演变,都受到实际的政治需要的决定与影响。不唯如此,这些伦理原则甚至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法制发展进程。有学者指出,100多年来中国亲属法的最大变迁是废除女性的出入改宗,但“亲亲”“尊尊”的原理并没有改变[3]。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家族是重要的经济组织,承担着教育的责任,亦有着重要的宗教功能,祭祖活动几乎是全国一致的礼俗与传统。最为重要的是,除了城市,广大的农村皆是依靠社会自治,而以家族为主要单位的自治形式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宗法伦理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伦理场域”,在此熟人社会中,伦理的力量极具束缚力。简言之,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基石,其所承担的功能皆以宗法伦理秩序为前提。当然,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宗法伦理所维护的君主专制政体已失去了生命力,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根据以《清实录》为原始资料的研究,从1796年至1911年,包括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在这晚清最后的115年中,由皇帝颁布的奖赏多达200万件。其中,奖励忠君行为占60%,奖赏孝行占1%,褒奖贞节者占39%,而有三分之二的奖赏是在1851年至1875年这25年中颁出的。按照刘创楚等学者的解释,在19世纪清王朝危机四伏的境况下,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受到了大力奖励[4]。三纲之中,忠君行为受到最多嘉奖是正常的,而表彰贞节行为是为了强化以夫为妻纲为代表的宗法伦理。之所以奖励贞节行为远高于孝行,是因为守寡易见而孝行难知。这也说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与君主专制社会几乎是浑然一体、互为支撑的。今天,宗法家族社会已经解体,宗法伦理与我们已经渐行渐远,而新时代要求新型的家庭伦理规范。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以仁爱为伦理原则,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等伦理规范依然值得提倡。而传统儒家伦理从血缘伦理出发,使仁爱扩展到无限广大领域的价值追求,无疑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289页。
[2]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7页。下列商王世系,皆参照张光直先生此书。
[3][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2页,第562页。
[5]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6]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7页。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1917年王国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1933年郭沫若作《卜辞通纂》,1955年陈梦家作《殷虚卜辞综述》,虽然对于年代久远的殷代“先公”还有许多争议,但对于“先王”的世系基本达成了共识。
[1]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61页。
[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5页。
[3]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173—193页。
[1]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江蓝生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2]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27页。
[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3页。
[5]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
[1]董作宾:《殷历谱》上编卷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版,第3页。
[2][8]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3—374页,第370—373页。
[3][4][6][7]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前言”第1页,第136—138页,第306—307页。
[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9]常玉芝:《说文武帝——兼略述商末祭祀制度的变化》,《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5—233页。
[10]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江蓝生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页。
[11]李双芬:《从选祭到周祭》,《殷都学刊》2015年第2期。
[1]关于宗法分封制度的特征,已有不少相关研究,如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等,都研究了西周宗法分封制的特点。
[2]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56页。
[3]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26—128页。
[1]赵晓力指出,从周武王娶姜太公的女儿开始,历代周王都是隔一代与姜姓联姻一次,姬姜联盟隔代加强,既可以发挥婚姻“合二姓之好”的政治功能,又不至于让外戚势力太盛(参见赵晓力:《“五服”与“三代”:从中国婚姻法禁婚范围的变迁看“性别”与“姓别”》,《社会》2023年第5期。)。
[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主要包括周文王子辈(“文之昭”)、周武王子辈(“武之穆”)和周公的子辈(“周公之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3]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92页。
[4]高婧聪:《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165页。
[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293页。
[6]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165页。
[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6页。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2]现在的研究表明,嫡长子继承制在殷末已经出现。有学者亦认为,嫡长子继承制不是宗法制的标准,嫡长子继承制巩固了宗法制家族中族长的世袭和继承的地位,而不是判断有无宗法制的根据(参见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以上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西周继承、完善并严格执行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其制度的核心,并为了这一制度的稳定,而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丧服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等。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二册02614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22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七册10175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485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2840号,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第419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9页。
[5]钱宗范:《西周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209页。与西周相比,汉代以后的历代皇帝也祭先祖,但和地方官员的祭祖制度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反映了当时宗法制度只作为一个被继承的社会制度存在,和自皇帝至地方官员的政治统治系统不再结合。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
[2]顾颉刚:《国史讲话:上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1]三纲之说源于荀子。《荀子·天论》曰:“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后来《韩非子·忠孝》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的“天下之常道”,从而形成了三纲之雏形。
[2]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4—66页。
[3]杨伯峻:《试论孔子》,《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页。
[4]黄建中:《中西道德之异同》,郁龙余主编:《中西文化异同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2页。
[1]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页。
[2]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3]赵晓力:《“五服”与“三代”:从中国婚姻法禁婚范围的变迁看“性别”与“姓别”》,《社会》2023年第5期。
[4]刘创楚、杨庆堃:《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责任编辑: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