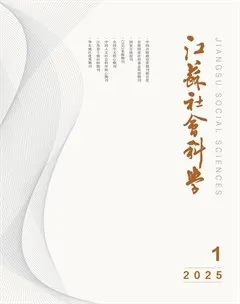“国家”渐变及其二元性
内容提要 晚清政府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有着“裕国”的目的,所呈现的“中国”既是一个传统农业文明强国,又有趋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进步;既帝制集权,又权能分化,且政府机构出现趋新变化;既宣扬“皇室”尊严,又开始面向世俗大众;既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故步自封;既学习西方,追求富强、进步,又坚守“中国”本位和特色,不完全模仿西国,这是典型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二元型”国家状态。晚清政府官员的“政府”观仍停留于“帝制皇朝”,与晚清社会已然彰显的超越“大清国”的“国家”观格格不入,因此晚清政府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的行为势必会招致充满“国家”觉醒意识的社会的批评。
关键词 晚清政府 圣路易斯博览会 “国家”观念
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写作时参阅了四川外国语学院王强老师提供的相关英文资料,特此致谢!
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是晚清时期中国参加的最为盛大的国际活动,也是晚清中央政府首次以“国家”名义亲自参加的国际博览会。对于晚清政府的这次参展及其所承载的“国家”观念,学界已然有所研究,但既有成果基本是以现代性的“西方”为标尺,认为晚清政府参展所呈现的“中国”不具有民族国家性质,其与西方所规制的展示秩序并不协调[1]。这类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忽视了“晚清政府”的存在,潜意识地认同“中国”应和“西方国家”一样。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从“晚清政府”的角度分析其在参展过程中所承载的中国“国家”到底如何,以期加深对晚清时期中国“国家”的认知。
一、晚清政府筹备参展
清朝外务部起初对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并不重视,只是按惯例“咨行南、北洋大臣饬属晓谕商民,届期备物前往,并札总税务司查照向章办理,暨咨行伍大臣派员就近赴会”[1]。1902年7月,圣路易斯博览会全权代表巴礼德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邀请中国政府与商民赴会,并希望帝、后亲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当即表示“我两国邦交辑睦,届时自当简派大员往襄盛会,从此商务振兴,升平共享,有厚望焉”[2]。自此,晚清中央政府正式同意赴会参展。
为何帝、后会同意参展呢?这与20世纪初中国的时局有关。庚子国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和约》,改变了与各国交往的模式。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一改不接见外国公使的惯例,在乾清宫正式接见诸国公使予以答谢议和,希望“邦交辑洽,海宇升平”,“中西各国必重敦睦谊,……同享升平之福”[3]。晚清政府开始以正常且平等的“国”之思维与他国联交睦谊。加之,历经动乱外逃回京的帝、后急需“太平”,对侵占北京之各国同意“议和”颇生感激,望与各国“同享升平之福”,因此才有了接见巴礼德及表示赴会以“升平共享”之举。
1903年1月,清政府谕任贝子溥伦为监督,全权办理赴会事宜。溥伦实乃趁赴会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所代表的是晚清中国“国家”,其赴美要在华盛顿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光绪帝给溥伦的敕书,谕令要本“裕国首重厚生、通商、惠工、睦邻”之旨,赴美“加意考察”,以助于“中华商业逐渐振兴”[4]。“国书”表明溥伦“分属宗支,留心商务”,希望美国予以优待,使之得以“加意考求”,而使“两国商务日臻兴盛”[5]。溥伦觐见美总统所致颂词曰:“大清国深知与各国通商实为要政,本监督奉命到美,系为竭力振兴中美商务,惟望贵国政府推诚相助,庶能日见兴旺。”[6]由此可见,晚清政府赴会主要是为了敦睦邦交、振兴商务以“裕国”。清政府同意参展至少说明晚清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迈出了大步,积极寻求建立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和好友谊,同时晚清政府也注重谋求中国之“国家”利益,有着富强“国家”的考量,这些都是立于中国“国家”本位的。
如何组织赴会,对晚清政府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大问题。首先是人事问题。赴会起初被视为“洋务”,由刚从总理衙门改制而来的外务部负责。1903年9月,商部成立,赴会又被视为“商政”归其管辖。外务部经询问美驻华公使康格后,决定按一正两副监督安排人选负责赴会事宜,正监督由皇帝旨派,副监督则由外务部拣派。监督溥伦统筹一切赴会事宜,代表大清国出使美国。美国人东海关税务司柯尔乐为副监督,主要负责出品接收、整理、运输与布展等工作;留美幼童出身的候补道黄开甲为另一副监督,主要负责赴会的前期工作,包括择地建设中国馆、协调中国出品之展场、料理华商赴会事宜及会场接待等事宜。
其次是出品问题。赴会的出品既由外务部饬总税务司署通令各海关税务司征集,又由外务部督饬、监督溥伦咨行各省督抚,或官办出品,或晓谕商人自行出品。江苏、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份都是官办出品,至于其他省份则多是劝谕商人自行出品。当然,也有个别省份组织不力,导致官民都未出品,例如山东就“无商民呈请运货前往”[1]。最终,晚清政府共征得出品约2000吨,时值638250美元,其中官方出品约占16%,民间出品约占84%[2],民间远多于官方。各省绅商对于赴会较为积极,他们不仅出品、办货自行赴会,而且自费或受官派赴会考察。在广东,粤商创立广业公司,集资20万元办理出品,派8名商人送货赴会考察[3],黄廷钦、郑贯贤等12个商民,自费组团观会考察[4];四川省派候补道章世恩带领通判祁祖彝及学生20人,赴会“考察各国工商之所长,宜如何规仿,审度我国工商之所短,宜如何改良”[5]。各省绅商之所以如此积极赴会,主要就是受到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催动,除有盈利目的,更多是想劝商兴工,以“求国之富强”[6]。
最后是经费问题。赴会预算需银75万两之多,外务部“实难再拨赛会经费”,但考虑到赛会“内可维持商务,外可联络邦交”,就请旨“饬下南北洋通商大臣及有商务省分各督抚,迅即妥为筹款”[7]。监督溥伦亦奏请谕旨,由户部先行垫付。然而,户部财政困难,难以全垫,遂决定先从江海关提拨45万两厘金垫给,以供赴会先期之用,同时向各省摊派筹款:直苏粤川各10万两,鄂浙各8万两,赣皖湘鲁各4万两,闽3万两,三个月内解款[8]。除直苏赣皖四省按时足额解款,其他省份多不配合,要么故意延宕,要么以财政紧张为由打折筹款,要么完全拒绝。最终各省共计解款46万两,不足部分之29万两由沪关垫付,后用厘金支补。这样的筹款解款模式,说明晚清政府财力虚弱,动员能力有限,央地财政支绌,海关所控厘金至关重要。
圣路易斯博览会是晚清中央政府首次主导参加的世博会,赴会最先由帝、后拍板决定,后由外商二部为主牵头,联合户部、总税务司、各省地方大员办理,并由皇帝谕派监督、外务部拣派副监督负责具体筹办事宜,赴会经费亦由政府筹措。如此组织赴会,体现了“中央集权”这一传统的国家行政运行方式,又反映了“国家”已然虚弱,财力及动员能力明显不足,不仅人事要仰仗外人,而且官办出品不及民间出品,中央政府筹款难以如愿,地方政府亦未能如期如数解款,须动用海关所掌控的厘金。这还可说明“国家”开始悄然而变,以往受总署札委,海关基本掌控了赴会事权,而今晚清政府已经意识到赴会能“裕国”、和睦邦交,开始由新设的外商二部主导赴会,借以削弱海关此项事权,直至1905年12月颁布《出洋赛会通行简章》,明确规定赴会事宜完全由商部自行办理。晚清政府开始积极接触世界,政府行政尤其是“商政”开始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这就从客观上引发了国家“形态”的转型。
二、博览会上的中国“国家”呈现
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晚清政府所承载的“国家”形态主要是通过中国展品展馆、慈禧画像及溥伦等人的言行呈现出来。
1.中国展品
海关总税务司署曾专门编写了中国展品目录[1],据此目录,笔者整理发现:在博览会官方所定的15类144组的征品类目中,中国的出品为11类85组,主要集中于制造类、人文教养类、美术类、农业类、渔业狩猎类,包括丝绣饰物、钱币、日晷、金银器皿、帽子、皮类饰品及编织物、珠宝等。这些展品都与农业文明高度相关,所呈现的是一个农业文明强国,而工业文明则相当落后。
然而,具体的展品反映了晚清中国开始发生趋向工业文明的进步。首先,在科学技术方面,部分与农业文明高度相关的产品已经开始采用工业化生产方式,诸如一些纺织类、矿冶类出品用模型展示了机械化的生产过程,这反映了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促使中国经济面向工业化所发生的新变化。其次,在城市建设方面,由海关负责征集的展品中就有关于口岸城市的地图、规划设计图表以及桥梁、住房、商店等模型,这些反映了中国传统市政建设在开埠后面向近代城市发生的新变化。最后,在学校教育方面,江南水师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堂等新式学校的展品,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开始向近代教育发生的新变化。上述这些新变化,实际上就是晚清中国整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在具体而微处的直接体现。
按照博览会官方规制,所有国家的出品都应按类别展陈于各个展馆,即按照西方近代知识系统进行分类陈列。不过,中国出品例外。中国出品虽已由海关按博览会官方所定的征品目录进行了分类编号,但在副监督黄开甲的坚持下,中国出品最终大多集中陈列于人文艺术馆的一片区域。之所以如此,按照博览会官方的解释,是因中国首次以“国家”身份参展,故而破例特许[2]。其实,中国一直主张“照例应由美赛会处给地若干,为中华货宝排列之所,然后由监督分派为各省货件地场”[3],把中国出品按中国省份区划,集中展陈一地。如此陈列,即使如有人所析,是晚清时人不懂得策展所致,导致中国不能融入西方所规制的展示秩序[4],但这是按照自己的知识理路和行政区划思维呈现了一个整体的“中国”,彰显了“中国”特色。
2.中国馆
中国馆仿溥伦北京皇室宅邸而建,由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英籍建筑师设计,美国建筑商承建,装饰布景完全由中国工匠用国内带去的材料完成,旨在符合中国文化意蕴,真正呈现“中国”。中国馆建造之初,博览会官方曾建议中国馆“仿内地名胜处所,建一房屋,或苑囿,或园林”[5],但清政府并未采纳。
中国馆的主体建筑是典型的华人会馆房式,“一厅两厢,中堂悬《天宫锦绣图》,附悬一联‘宗支瑞毓长春树,世泽祥延积庆图’,两排设座椅,分嵌镶、乌木、光漆、紫檀四种,中设一机,与官厅同,刻柱雕龙,缘壁铺挂绣画。左厢设两房,仿闺阁式,铺陈镂刻木床,花绣锦褥;右厢一仿书房式,一仿办公式,陈列古玩”,“大门则以砖石叠造,缀一红匾,颜曰‘大清国’。距门丈许,造牌楼一,旗杆二(左中国旗,右美国旗),牌楼雕刻华丽,加以红漆,右侧以小池,以细石砌成”[1]。所陈设家具及雕饰摆设,亦“悉用华式”[2]。
对于中国馆的陈设布局,有学者认为没能“标示民族国家框架下定义的‘中国’”[3]。这一说法隐伏着值得商榷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溥伦皇室宅邸能不能代表“中国”?皇室是帝制中国的核心表征,帝制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是中国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也是中国的“国家”代表。溥伦皇室宅邸,虽非“名胜处所”,但更具“文化”与“国家”的象征意义。向来神秘森严的皇室宅邸,能在国际博览会上展示于众,至少说明其所承载的中国之“国家”向大众化、世俗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况且这还可公开宣示其代表着“大清国”,即“中国”之“国家”。在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不独晚清政府以“皇室”作为“国家”的象征,英国、德国亦是如此:英国馆“仿坎心顿宫式构造”,“悬英皇像”,德国馆“仿二百年前普鲁斯之皇宫构造”[4]。
二是中国馆必须呈现“民族国家框架下定义的中国”吗?这个问题须进一步追问,中国馆必须在西方“国族论述”下呈现如西方民族国家一样的“中国”才能称得上“国家”吗?仿溥伦宅邸的中国馆如同中国出品集中展陈一样,坚持“中国”本位,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展示文化去呈现“中国”以迎合西方喜好,而是把最能代表传统中国、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的帝制皇室呈现给世界大众,以之来塑造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告知世人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其所呈现的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国”。这一方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较好地呈现了“中国”,另一方面公开强化了清皇室才是“中国”的“国家”代表,“大清国”即“中国”。
3.慈禧画像入美
慈禧太后虽没回应博览会官方“临幸”的邀请,但听从康格夫人的建议,同意将其画像送到博览会展示,以改善西方社会对其形象的认知。经康格夫人推荐,美籍画师卡尔·柯尔乐(副监督柯尔乐之妹)入宫为慈禧画像。按太后要求,画像10英尺长、6英尺宽,由身着皇宫服饰的慈禧肖像、九只凤凰、三折屏风及象征皇权的“宝座”组成。画像的画框和座架雕有“寿”字、“二龙戏珠”图案及“万寿无疆”的边饰。慈禧太后要求其肖像的面部全部呈亮色,使年近70岁的太后看起来很年轻、祥和[5]。
制作好的画像只能竖立而不能横放,裹以黄色绸缎后装封,交给外务部“祗领”。外务部饬总税务司把“圣容”“敬谨寄至美国”,“恭奉”至会场“俾共瞻仰”[6]。经总税务司赫德亲自安排,画像顺利启程赴美,在京、津、沪等地都有一众官员恭迎恭送。画像抵美后,两副监督备专车恭接恭送至会场,由博览会官方置于美术馆正厅展示,监督溥伦亲自布置画像,并举行了揭幕礼。博览会结束后,驻美大臣梁诚亲送画像至华盛顿以“国礼”赠美,由美总统罗斯福亲自接收。
“大清国皇太后”画像,就其内容和设计装饰而言,有着浓厚的帝王色彩,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的是帝制“国家”,但慈禧画像赴会展示及赠予美国,并享受“国家元首”待遇,这就维护了以“皇室”为象征的中国“国家”尊严。慈禧作为一个女性,且是晚清政府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能够打破禁忌,允许其画像在国际上公开展示,这本身就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大进步。慈禧太后画像入美,不仅增进了中美国家友谊,而且开启了中国利用领导人画像来塑造领导权威和国家形象的进程,还改善了慈禧太后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之“国家”的国际形象。
4.溥伦使美
溥伦以皇族身份担任监督使美,其代表的是国家,这既表明晚清皇室如慈禧画像一样,开始迈出国门,亮相国际舞台,同时又肩负“国家”重任,因其赴美不只是办好赴会事宜,更多是“加意考察”。
溥伦使美之时途经日本,专门到东京觐见天皇。抵达美国后,先是去华盛顿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离开美国后,他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到欧洲考察近2个月。溥伦在美虽近2个月,但在博览会场总共只待了20余天,他参加博览会开幕礼,办理中国馆开馆事宜,为慈禧画像揭幕,其余时间都是在美国考察。这些举动说明晚清希望利用赴会之机,着力于与国际交谊接轨,以图新图强。
溥伦在美,一方面对“西方”表现了浓厚兴趣,他考察了学校、博物馆、股票交易所、银行、商会等跟“新政”息息相关的机构组织,也深入体验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如乘汽车、吃冰激凌、坐游艇、逛百老汇、听歌剧、看棒球赛以及到普通人家做客,展现亲近西方、积极进取、喜好新奇、亲民友好的中国皇家官员形象;另一方面,极力彰显“中国”文化,在下榻酒店房间中布置中式家具,在博览会开幕及中国馆开馆等正式场合与黄开甲等人身着清朝官服,头戴顶戴花翎,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形象。溥伦一行,受关注的程度远高于同期日本包括男爵在内的赴会代表团及赴美访问的伏见亲王[1]。
溥伦等人的所作所为,表明晚清政府迈出了走向国际的开放步伐,在坚守中国传统和特色的同时,开始变革求新,学习西方,图富图强,努力改善中国国际形象。驻美大臣梁诚认为其“以天潢贵胄奉使”,所到之处“华洋人等欢呼迎接,其趋承恐后之状,爱慕依恋之诚,实为各国宗藩游历此邦所未曾有”,使得“美国上流人士,益知我国之日进文明,而华人之不易侮”[2]。
三、晚清政府的“国家”观念
就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事,光绪帝、慈禧太后、外务部、商部、军机处、监督溥伦、驻美大臣梁诚、南北洋大臣、地方督抚、副监督黄开甲等机构和官员互通文书及函件,言及了大量与“国”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反映了晚清政府的“国家”观念。
美国官方在致清政府的函件中都自称“美国”“美国政府”,而对晚清政府亦称之为“中国”“中国政府”,仅有1次称其为“大清国”[3],背后的“国家”观念甚为清晰。显然,这也会影响晚清政府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认知。晚清政府对美国的称呼基本为“美国”“美国政府”,对晚清中国除在非常正式的“国书”中称呼为“大清国”[1],基本就是泛化混称为“中国”“中华”。比如,光绪帝就强调,“所有中国商民赴会贸易者,均宜随时保护约束”,“期于中华商业逐渐振兴,用副委任之意”[2]。至于其他官员更是如此。溥伦即说,“赴赛系中华创举”[3],“中国地大物博,而制造尚未尽振兴,诚能研究精详,洵可广开风气”[4]。江汉关道岑春蓂言:“中国货宝应如何排列,一时尚未定议,……照例应由美赛会处给地若干,为中华货宝排列之所。”[5]此时的“中国”“中华”虽然混用,但都指称“中国”,其使用频率远超“大清国”,含义亦盖过“大清国”,当是指“大清国”所承载的自远古以来累积而成的“中国”。“大清国”作为中国之“国家”的具体承载体,已被“中国”所涵化,“中国”成了中国“国家”的统称,即便是晚清政府,亦言必称“中国”,这所折射的即是“国家”观念的萌生。
晚清政府亦曾直接表达了抽象的“国家”观念。驻美大臣梁诚在致美函件中说:“此次工匠人等来美,系国家所雇佣工。”[6]溥伦回国后向清廷建言,“各邦立国之大较,莫不以学务为根本”,“谋国者,贵绸缪于未雨”,“况国家整顿海军实为保护商民起见”[7]。溥伦言语中的“国”当然是指“中国”抽象化后的“国家”。晚清政府将慈禧画像赠送给美国,希冀“画像”获得“国家”一般的礼遇,因此在跟美国交涉时一再强调是赠送给美国“国家”[8]。这也表明晚清政府在国际交往中有了明确的“国家”观念。
随着“国家”观念的萌生,晚清政府还产生了与“国家”相关的情感和权利认知,表达了“国体”“主权”之类的词汇。梁诚在关于华人赴会事与美交涉时有言:“此事上关国体,下关商务,万难隐忍迁就,使得加膝坠渊”[9],“自行开埠,可保中国之主权”[10]。四川总督岑春煊致函外务部:“惟此举有关国体,何敢漠视,无论如何为难,仍当极力腾挪以应亟需而顾邦交。”[11]溥伦上书清廷:“惟思交际为国体所关,在在均为紧要”[12],“海界属于中国,则海权应操于中国”[13]。这些说辞都表明晚清政府已然十分在乎国家的尊严与权利。
虽然晚清政府的“国家”观大有进步,但“政府”观仍停留在“朝廷”,称清政府为“朝廷”者,比比皆是。例如,外务部言“仰体朝廷鼓励工商之至意”[1]。溥伦言及“朝廷”相当频繁,“冀副朝廷任使之隆”[2],“奴才自应悉心经理,以副朝廷通商惠工之至意”[3],“伏思朝廷设立领事,保护商民无微不至”[4]。就笔者目力,仅见一处称之为“政府”,即梁诚在致美照会中,提到“中国政府特为竭力以助赛会盛举”[5]。晚清政府的“政府”观,仍停留于帝制文化中的“皇朝”,视“政府”即“朝廷”。“政府”与“国家”息息相关,“国家”通过“政府”得以具象化。随着“国家”观念的成长,晚清政府的“政府”观如若仍原地踏步,甚至与“国家”背道而驰,其注定会被新的政府所取代。
四、国际国内社会之反响
对于中国赴会之举,西方社会多有褒意。对中国展品所承载的工艺和文化内涵,西方社会十分赞赏,认为数以千计的中国展品“展示世界的进步,构成独一无二的中国展览”[6]。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销售品也很青睐,认为茶叶等“独推中国为第一”,并与中国茶商签订“永远交易之合同”[7]。对中国馆,西方社会更是称赞有加,认为中国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美轮美奂,犹如仙境,是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最漂亮的建筑[8]。对慈禧画像,西方社会认为充满女性特有的“柔美”,与“乖张暴戾”的“老太后”形象有着天壤之别[9],甚至因慈禧太后同意中国加入《日内瓦公约》、赞助建立中国红十字会而将其誉为“中国的俾斯麦”,是对西方友好的优秀的改革者、政治家[10]。对溥伦,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开放的、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人,是一个亲民、民主、注重种族平等的皇家官员,是一个关注全民教育、经济、时政、军事且具有国际眼光的政治家;对常驻博览会场的黄开甲,博览会官方更是肯定有加,认为他“气象洪大,人甚谦和,办理一切紧要事宜,均为得当”,“足使中美之邦交更加亲密”[11]。
除中美敦睦友谊,中国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之所以能够获得西方社会的赞赏和肯定,主要是因为晚清政府呈现了独有的“中国特色”。虽然晚清政府赴会的主要目的是敦睦邦谊、振兴商务以“裕国”,有着学习西方的一面,但其并没有一味地哗“西”取宠,而是坚守“中国”本位,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中国”的民族性。这一点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就是其相当感兴趣的“异国风味”。
不过,与国际社会相反,国内社会对赴会之举却多有批评,极少溢美之词。首先,对展馆展场,国内社会认为选址、规划布置不当,建筑丑陋。“中国会场,地段狭隘,一无布置,此地介乎英、德、墨西哥会场之间,令人羞愧难堪之至”;中国馆之建筑,“矮小粗恶,莫名其丑”,“丢尽中国人颜矣”,“辱国不浅”[1]。对展品,国内社会认为不仅布展“错乱无章”[2],而且丑化了中国,彰显“国耻”,有辱“国体”,进而批评清政府不该委任海关洋员办理出品,导致“献丑”[3]。对赴会官员,国内社会认为他们无为、贪腐,批评溥伦不寓居会场,只知“炫其豪贵”,黄开甲“高卧不出”,对“赛品之得失,华商之短长,无从过问”[4];甚至认为溥伦所领用的15万两赛会经费,完全为其私人所用[5],黄开甲亦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其赴会就是为了“发大财”,且发财后不回中国,“以值二万美金之房屋,报销四十五万金”,并“将带来陈赛物品私运至纽约售卖,捏造应酬送人”,“净得美金三十万元”[6]。总之,晚清政府赴会“不特虚糜巨款,又使我四万万人之奇辱,永永印入全球人士之脑中”[7]。
其实,上述批评多属言过其实之论,有失公允,甚至是造谣诽谤。中国馆仿溥伦宅邸,虽然不是很宏伟,但也难称为“矮小粗恶”。展品“辱国”者只是少数,多数为西人所羡慕赞叹。溥伦以“天潢贵胄”之身担任监督,办理赴会事宜,主要是代表清政府处理中美两国“国家”层面的事务,其所肩负的重任更多是递交“国书”,敦睦中美邦交,在美各地考察,以谋“振兴商务”之策,因而不寓居会场,当在情理之中。溥伦赴美花费都有细目记载,事后呈报中央,其所领赛会经费并没有私用[8]。黄开甲所负责的事项,也都有收支细目,并呈报了中央,不仅没有中饱私囊,超支的1155两反而由其“捐廉弥补”[9]。博览会结束后,黄开甲并未私自贱卖中国馆物品,而是拍卖归公,难以拍卖的就整体赠送给了博览会官方;他也未滞留美国,而是回国继续为国家效力。此外,还有舆论造谣说,博览会总理拒绝接收慈禧画像,美国总统认为尊贵妇女若不与人结婚即不赠人照片,若收了太后画像,“近于亵渎”,最后更是将画像送还中国,因此批评慈禧画像入美导致“辱国”[10]。
这些批评言论基本是由留学生、新式知识分子、新式绅商及革命者发表于《大公报》《外交报》《东方杂志》《申报》《警钟日报》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或革命派所创办的新式报刊上。这些人物和报刊一般对晚清政府持批评态度,有些甚至与其直接对立,表达如上批评言论亦不足为怪。这些批评言论的出现还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关,尤其是超越“清政府”,超越并抽象化“大清国”的“中国”之“国家”观念已然萌生且明显化。不仅维新派、革命派等新式社群有着这样的“国家”观念,即使是晚清政府亦开始显露趋向近代的“国家”观。“国家”观念的强化必然会促使时人十分关注“中国”作为“国家”的权益和尊严。因此,当承载“中国”的晚清政府以“国家”名义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时,新式社群必然会时刻关注“国家”是否受损。革命者、留学生等对于“国家”更是一腔热血,况且他们对于晚清政府均有“腐败无能”的成见,为了推翻清政府,制造排满倒清的社会舆论氛围,会处处批判晚清政府,甚至不惜歪曲抹黑,而对其积极赴会的正面行为和实际效果基本视而不见。正是因为这种“国家”观念,批评的言论大都站在“国家”的高度,强调晚清政府赴会“辱国”,损害“国家”权益,更导致“东方病国恐无自立之日”[1]。
五、结语
晚清政府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有着较为明确的“国家”考量,既希望敦睦邦交,改善“大清国”的国际形象,又希望“裕国”,趁赴会之际考察欧美,寻求国家富强之道。晚清政府沿用传统行政思维以“中央集权”模式办理赴会事宜,通过饬令、摊派等方式要求各地出品、解款,然其实际效果不如预期,这说明晚清国家的“中央集权”效能已然弱化。不过,在办赛过程中,把赴会操办权由海关总署转移到外商二部,尤其是商部成立后,更是由其专管赛会事务,这也说明晚清政府为了适应新生事物,开始出现了权能分化和专业化。通过展品、展馆、慈禧画像和溥伦等人的言行,晚清政府的赴会既展示了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及其在生产方式、城市建设、学校教育等方面的趋新进步,又呈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彰显了“中国”的独特性,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与此同时,公开展示皇室宫殿、太后画像以及贝子赴美考察,都说明晚清皇室迈出了大众化、世俗化的步伐,显现了晚清政府有迈向君主立宪制的迹象,这些都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清廷”向“国家”转化。
整体而言,晚清政府赴会所呈现的“中国”,有着“裕国”的总体追求,既是一个传统农业文明强国,又发生了趋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进步;既帝制集权,又权能弱化,且政府机构出现趋新变化;既宣扬“皇室”尊严,又开始面向世俗大众;既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故步自封;既学习西方,追求富强、进步,又坚守“中国”本位和特色,不完全模仿西国,这是典型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二元型”国家状态。当然,晚清政府和晚清“国家”之间也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晚清社会,包括办理赴会的机构和官员,已然彰显超越“大清国”的“中国”观及更为抽象的“国家”观,重点关注中国的“国家”权益,但是这些机构和官员的“政府”观没有随之发生多大变化,仍然局限于“帝制皇朝”。迷恋“皇朝”的晚清政府显然难以适应“国家”的进步,无论其赴会如何作为,都会招致充满“国家”觉醒意识的社会的批评,晚清政府一味如此,不能全心全意谋“国家”之富强和进步,最终必然会被推翻。
[1]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印行,第421—475页;I. E. Cortinovis, \"China at the St. Louis World’s Fair\",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1977, 72(1), pp.59-66。
[1]《外务部致美使康格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二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3001页。
[2]《觐见答敕(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69页。
[3]《各国使臣会同觐见答敕(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谕(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3055页。
[4]《附件三:恭拟赴美赛会正监督敕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587页。
[5]《附件二:恭拟溥伦赴美赛会国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586页。
[6]《附件:颂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717页。
[1]《为东省并无商民呈请赴会现派员带同商董观会请将预留地段匀给别省事(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526页。
[2]参见居蜜主编:《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III,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3]《为户部主事梁用弧等招集粤商创立广业公司并集资办货赴美赛会事(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收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521—524页。
[4]《为商民黄廷钦等请赴美国赛会已由粤海关验填护照事(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793页。
[5]《外务部收署四川总督锡良文(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3825页。
[6]《论派员至美赛会之宜慎》,《中外日报》1903年8月9日。
[7]《为请旨简派赛会正监督并已令黄开甲柯尔乐充任副监督先行赴美事(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80页。
[8]《为现有寄各省电报请速转发事(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243—248页。
[1]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1册第409—567页,第222册第1—228页。
[2]居蜜主编:《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II,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3]《为晤商明年美国赛会中国货品占地事(光绪二十八年考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229—230页。
[4]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印行,第446—447页。
[5]《为驻美大臣奏报美国赛会应择地建屋事(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14页。
[1][4]陈琪:《美洲博览会记》,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第81—82页,第82页。
[2]《赛会汇纪》,广文编译所增编:《外交报汇编》第21册,台北广文书局1964年影初版,第91页。
[3]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印行,第472页。
[5]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王和平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163、199页。
[6]《为皇太后圣容恭绘告成现遵懿旨转饬寄至圣路易斯会场请钦遵事(光绪三十年二月三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690页。
[1]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印行,第473页。
[2]《为详陈赴会及供奉皇太后圣容于美国国家画院正厅事(光绪三十年五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790—791页。
[3]《为庆贺购地百年拟行赛会现恭请大清国皇帝御临事(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55页。
[1]《附件二:恭拟溥伦赴美赛会国书》、《附件:颂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586、717页。
[2]《附件三:恭拟赴美赛会正监督敕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587页。
[3][12]《为拟调内务府员外郎诚璋等五员随往赴会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289页,第289—290页。
[4]《为行抵圣路易斯并择三月二十一日开会事(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730页。
[5]《为晤商明年美国赛会中国货品占地事(光绪二十八年考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229—230页。
[6]《附件:抄录与美外部往来照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96页。
[7][13]《为敬陈赴美游历及办理圣路易斯赛会之管见事(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860、862、873页,第861页。
[8]《为皇太后圣容恭迎至会场瞻仰俟赛会事毕即赍送贵国希转政府查照事(光绪三十年二月三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686—689页。
[9]《为赛会副监督黄开甲抵旧金山并华商赛会章程交美工商局核议事(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424页。
[10]《为美工商部答允变通华人赴美赛会章程事(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446页。
[11]《为筹解美国赛会经费二万两事(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24页。
[1]《为请旨简派赛会正监督并已令黄开甲柯尔乐充任副监督先行赴美事(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80页。
[2]《附件一:为拟调内务府员外郎诚璋等五员随往赴会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289页。
[3]《为行抵圣路易斯并择三月二十一日开会事(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730页。
[4]《为敬陈赴美游历及办理圣路易斯赛会之管见事(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873页。
[5]《附件:抄录与美外部往来照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①,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96页。
[6]居蜜主编:《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III,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引言”第2页。
[7]《会场华茶畅销》,《大公报》1904年11月3日。
[8]居蜜主编:《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II,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T. Hardee, \"China’s Remarkable Exhibit at the World’s Fair\", New York Times, Aug 28, 1904。
[9]\"An Imperial Portrait\", New York Times, Jun 27, 1904;王正华:《走向“公开化”:慈禧肖像的风格形式、政治运作与形象塑造》,《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2期,2013年。
[10]P. Bigelow, \"A New View of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New York Times, Jun 26, 1904.
[11]《附件二:圣路易斯赛会会长为甚为欣悦黄开甲充任赛会副监督事信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610页。
[1]《节录某氏函述美国会场情形》,《大公报》1904年4月29日。
[2][4]陈琪:《美洲博览会记》,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第87页,第186—187页。
[3]《书美洲学报实业界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时评:圣路易会场之国耻》,《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5]《论伦贝子赛会之结果》,张元济主编:《外交报汇编》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08页。
[6]《节录某氏函述美国会场情形》,《大公报》1904年4月29日。
[7]《书美洲学报实业界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
[8]《附件二:赴圣路易斯赛会收支经费清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829—847页。
[9]《附件二:赴美圣路易斯赛会收支经费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②,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889—910页。
[10]《圣路易会场要事》,《警钟日报》1904年6月27日。
[1]陈琪:《美洲博览会记》,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第59页。
〔责任编辑:史拴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