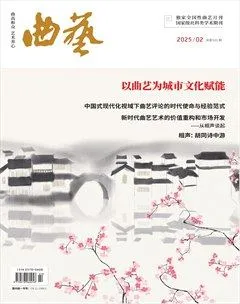陕北说书 “改造说书”的历史探源、变革维度及当代启示
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曲艺生根发芽并于地方文化的滋养中日臻成熟,在艺术上往往呈现出极强的地方性,不仅内容取材于当地的生活,而且说唱所采用的语言也往往是地方方言。与此同时,曲艺往往会对当地的文化产生反作用。“改造说书”运动中的陕北说书就是这种双向影响的一个绝佳例证。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从“旧”到“新”的艺术蜕变中,陕北说书既获得了新生,也成为了曲艺参与地方文化、革命文化的宝贵样本。这对于今天的地方曲艺发展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一、“改造说书”的历史探源
延安时期的“改造说书”有着自身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是反映延安地区社会新面貌的根本需要,也是顺应全面抗战形势的必然结果。在这一根本需要下,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的精神引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赋予旧的艺术样式“新生命”的历史创造之中。
(一)反映社会新貌,服务抗战事业
作为使用陕北方言,连说带唱的曲艺种类,陕北说书确切可考的历史应当确定至清代。及至民国时期,随着艺人的成熟,陕北说书逐渐发展成为了陕北文化当中极为重要一部分,与陕北地区的民俗文化紧密相连,“一种以家书、村社书和庙会书为主的说平安书(亦称‘愿书’)习俗逐渐形成”①。此时演出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一是讲史事、说戏文;二是根据古代小说改编;三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和民间笑话趣闻等编演”②。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西北部吴起镇,“落户”陕北,以大刀阔斧的革新使陕北地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毫无疑问,陕北说书过去“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③的题材已然不能表现这时的社会变革。改造陕北说书,使之可以反映社会新貌,成为抗战文艺事业的一部分,成为彼时陕北说书艺人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同志曾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要想赢得战争,就必须充分动员可以动员的一切人民群众。然而,“边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是文盲”⑤。因此,事实层面对社会民众起到教化作用的,是包括陕北说书在内的各种文艺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1942年《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基本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确定了文学艺术成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普及进步思想和文化的重大使命。
(二)《讲话》的引领、改进及“新秧歌运动”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革命的文艺工作”⑥。1942年5月2日到23日,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⑦“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⑧学者们高度评价《讲话》,认为《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艺思想的历史性超越”⑨。《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大众化”的问题,强调“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⑩。在《讲话》的精神引领下,陕北地区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开始自觉自发地在农村、农民中汲取创作的营养,真真正正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反映进步思想的优秀文艺作品。
《讲话》的影响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以1943年的《兄妹开荒》为标志,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开始了。“1943年起,知识分子积极介入秧歌的创作、演出后,延安的老百姓把这之前自己的旧秧歌唤作‘骚情秧歌’、‘溜沟子秧歌’,而命名新秧歌为‘翻身秧歌’、‘胜利秧歌’和‘斗争秧歌’”11。在新秧歌运动中,文艺工作者们真正做到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剔除过去秧歌中荤黄下流、封建迷信的元素,赋予新创作品以时代的气息,并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理念。各个机关、单位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秧歌队,甚至还举办了秧歌的汇演。一时之间,秧歌艺术在进步思想的帮助下焕发了新的光芒和色彩,引领了当时陕北地区的风尚。在新秧歌运动影响下,彼时的陕北说书艺人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反映现实,为革命服务的新秧歌、新戏剧发展起来了。那时,我(韩起祥)住在乡下,离延安二十多里路。我到延安一看,人家扭秧歌、唱歌、演戏都是新的了,而我还是今天说‘摇钱记’,明天说‘张七姐下凡’。我开始感到我说书的内容和党的政策是相反的。”12
二、“改造说书”的变革维度
“改造说书”作为当代陕北说书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变化并非某一维度(或层面)的;相反,其变化包括了创作模式和曲艺本身两个维度。换言之,“改造说书”对陕北说书的变化是由艺人到艺术的,是由表及里的。
(一)对创作模式的“改造”
在《讲话》的引领及新秧歌运动的影响之下,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近民间艺人,并主动团结、积极教育,最终达到“改造”的目的,使民间艺人逐渐成长为文艺事业的中流砥柱。在当代诗人贺敬之的引荐下,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走进了知识分子的事业之中。“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做好陕北改造说书的工作,在林山等同志的建议下,边区文协于1945年4月间,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以下简称“说书组”)’”13。“说书组”中就包括了林山、陈明、安波、韩起祥、高敏夫、王宗元等人。“说书组”首先采取了“联系、团结、教育、改造民间说书艺人,启发、引导、帮助他们编新书、学新书和修改旧说书,首先是个别采访,选择对象,培养典型,然后通过他们来联络其他说书人”14的改造思路。具体地说,“说书组”对韩起祥等的“改造”主要分为3部分:第一,帮助艺人整理《刀枪记》《还魂记》《花柳记》等传统书目,教育、启发艺人,删去传统书目中落后、糟粕的元素;第二,加强思想教育,启发艺人在书目当中增加边区的生活变化,并鼓励知识分子参与创作,与艺人共同创作积极向上、宣传进步观念的新作品;第三,便是将韩起祥作为“进步了”的典型,鼓励他向广大说书艺人现身说法,“以点盖面”地影响和塑造其他的说书艺人。在这一期间,韩起祥创作、表演了包括《红鞋女妖精》《张家庄祈雨》《刘巧团圆》在内的一大批反映延安地区生活新貌的新作品。而在这一过程中,韩起祥本人有了“文化娱乐我承当”15的社会责任感。他从陕北说书艺人到陕北说书艺术家的转变也在这一刻完成。其次,“说书组”已然意识到了单单改造一个韩起祥是不够的,“随后,陕北说书改进会在延安、绥德、米脂、清涧、延川、延长等地陆续办了八期培训班。当时,陕北解放区有盲艺人约四百八十余人,参加培训班而自觉编演新书的就有二百七十三人”16。越来越多的陕北说书艺人如韩起祥一样走上了创作表演新书目的路。
(二)对曲艺本体的“改造”
“改造”之于陕北说书而言,除创作模式上知识分子与传统艺人的合作,也在内容、形式上实现了说新、唱新、演新,赋予了陕北说书全新的面貌。首先,核心的“改造”就是艺术表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韩起祥在延安时期演出的新书目,主题涉及进步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破除封建迷信的《红鞋女妖精》、推崇自由恋爱的《刘巧团圆》、讲述民主选举的《张玉兰参加选举会》、普及科学文化的《张家庄祈雨》等,反映延安地区生活新貌的作品不胜枚举。这种变化使得陕北说书不仅有了更为强烈的时代气息,及时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且还使进步的思想以形象的方式得以呈现,真真正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其次,就是表演形式的变化。第一,唱词形式发生了变化,传统陕北说书中的七字句或十字句的限制被突破,四字、五字、六字乃至十几字的句式使得作品更为灵活多变和通俗易懂,也使得演出中添字衬句更为方便。第二,唱腔音乐也发生了变化,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陕北说书艺人们在传统说书唱腔基础上,大量吸收当地的民歌小调、秦腔、碗碗腔及陕北道情等艺术形式的音乐唱腔,形成了新的唱腔。第三,在唱腔音乐发生变化的基础上,伴奏过门也发生了变化,“也采用了一些民间小调和唢呐曲牌”17。
改造后的陕北说书,是在对传统陕北说书进行继承上的创新,是对陕北说书艺术传统进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基础上的“再创造”,既有新的内容和形式,又充满了时代气息,表现了时代面貌。总而言之,内容与形式统一,继承和革新融合,使得“近现代陕北说书的鼎盛时期应该说是延安的新文艺运动时期”18。
三、“改造说书”的当代启示
21世纪的今天,城市文化发展迅猛,文化艺术领域的“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回顾“改造说书”的历史,不难发现,文艺工作者要想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有作为“守门人”的使命自觉,更要自觉传承“文化基因”。
(一)“守门人”的使命自觉
作为新时代的曲艺工作者,要在扎实自身的业务能力基础之上,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先进的世界观,做好社会传播的“守门人”。美国传播学学者库尔特·卢因提出了著名的“守门人”理论。所谓的“守门人”,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的筛选、过滤、加工等具有决定权的个体或机构。回顾“改造说书”的历程,可以说,包括韩起祥在内的“说书组”完全承担起了“守门人”的责任。他们正是在对传统书目整理的基础上,用进步的世界观、深厚的文化积累以及扎实的专业素养,努力辨别陕北说书传统书目当中的糟粕与精华,从而达到了艺术创作上的“通古今而计之”的境界。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而言,“守门人”责任的关键首先应该是进步的世界观。如果没有对旧社会苦难的深刻见解和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衷心爱戴,彼时还只是盲艺人的韩起祥又怎么会加入到“改造说书”这一曲艺史的创举之中呢?陕北说书艺术家韩起祥的蝶变并非孤证。正是在切身经历了神州大地上从“旧”到“新”,清醒意识到社会生活的变革与观众的审美变迁,相声大师侯宝林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觉和老舍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一片,组织北京相声艺人,开始对北京相声去粗取精。其次,“守门人”责任还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提升自身道德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上的讲话中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19。韩起祥在“改造说书”中的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人贺敬之在这一时期跟韩起祥讲了陕北农村地方神婆故弄玄虚,用狗血假装“红鞋女妖精”来欺骗百姓钱财的故事。听罢故事后,在深入调查陕北农村封建迷信情况的前提下,韩起祥就创演了《红鞋女妖精》这一作品,使得作品真正达到了“充实之谓美”的效果。
(二)“文化基因”的创作方法
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首先提出了这一观念,“文化基因”是相对于生物基因而言的,被用来描述文化传播和演变的基本单位,是一种存在于人类文化领域的、可以像生物基因一样进行传播和复制的信息单元。道金斯指出,文化基因具有可复制性、遗传性和变异性。对于曲艺工作者而言,任何创新和创造都不能脱离“曲艺”本体的范围与范畴,否则“创新”就有可能变成创伤,“创造”也只会留下创口,雄心壮志的艺术创举最后也许只会沦为相声大师侯宝林所说的“戏不够,神仙凑”20的尴尬境地。在“改造说书”中,从曲艺脚本的创作,到姊妹艺术音乐体制的吸收,种种突破都离不开韩起祥对于陕北说书全面、系统的继承。从中不难看出,回归曲艺本体并传承其“文化基因”,综合全面地继承前辈的艺术技巧,结合自身特点与时代风貌进行遴选,才是今天曲艺创新创作的“必经之路”。我国古代哲学家王船山所说的“通古今而计之”,戏曲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强调的“移步不换形”,其中都蕴含着这个道理。
哲学家张世英说,“过去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要在后来和现在中展开”21。宏观地说,“说书改造”这段当代曲艺史上的岁月,在某个角度上来说,是为今天的曲艺创作,乃至曲艺的创新与发展再次梳理理论路径。微观地说,曲艺工作者们更要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不断加强自身道德建设,努力传承前辈的曲艺成果,同时,还要回顾曲艺的发展历程,“以史为鉴”地观照自身的创作与研究。
注释:
①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陕西卷》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曲艺志·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9年,第92页。
②《中国曲艺志·陕西卷》,第92页。
③胡孟祥:《韩起祥评传》,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⑤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⑥胡孟祥:《韩起祥评传》,第6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3页。
⑨陆贵山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5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1页。
11郭玉琼:《发现秧歌:规训与狂欢—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2006年第1期,第250页。
12延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下)》,延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2008年,第168页。
13胡孟祥:《韩起祥评传》,第70页。
14胡孟祥:《韩起祥评传》,第71页。
15韩起祥、高敏夫:《刘巧团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1页。
16《中国曲艺志·陕西卷》,第93页。
17《中国曲艺志·陕西卷》,第93页。
18曹伯植:《陕北说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
19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薛宝琨:《侯宝林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21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3页。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