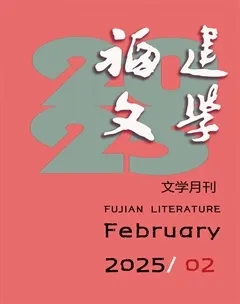儿童医院的阳台
1
也许是由于惯性,我们总是以时间计算着日子,由时间,将此刻坐在这里区别于几日前在另一地做着另一事。当时间消弭以后,我在这所儿童医院里所孜孜不倦的,竟然是洗衣,晾衣,再一遍遍地穿过T字形的走廊,穿过那些焦灼而不得不放慢脚步的父母与他们的孩子——一个个身上某个地方贴着纱布的孩子,来到一扇虚掩的门前。
这个门通往一个闷热的阳台。阳台的栏杆上摆着几盆绿植,有一盆兰花甚至还盛开着。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孤独而奇异的美感。阳台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衣服,一股霉湿的热气扑面而来。这些衣物都是走廊和房间里的那些父母与孩子们的,不仅挂满了上面栏杆,还在地面的矮杠上铺满。
我仰着脖子,寻找着还能挂上去的空隙。在前天我们住进了这一层的病房后,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琳琅的衣服中寻找可钻的缝隙。最后,在一顶黄色小童帽的旁边,我把小天的一件上衣挂了上去,刚刚好贴着帽檐。
2
到后来,我渐渐忘了来到此地的时间,只有一天下午除外。那时傍晚来临,我穿过那些父母和孩子,还有婴孩的哭声,和一个个奔忙的身影,来到房间的窗边,拉开蓝色的帘子,望见窗外格外明净的天空,夕阳将半个天空的云照成了鱼鳞状。我把小天拉到窗边抱起来,让他去看这一幕。他的眼神却落在眼前的居民楼上,并指着那一排的屋顶,问他的爸爸住在哪一个酒店里。
现在我又回到了时间的圈套里面,在回想的同时,也在远离一些现场的东西。
六个床位的病房被蓝色的布帘切割成一块块。那些布帘掩盖住了一个个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伤口,哭声,以及顽笑。
小天每天都渴望着出去,但手上的两条腕带成为他向外的禁锢。他开始在有限的空间里折腾,把一种叫假水的玩具胶一盒一盒打开,揉搓,从桌上,到行军床,再到地板,铺成他内心无意识的镜像与想象,嘀咕自语。玩腻后,小天再次折腾起病床边上的摇杆,把床头摇成一个斜坡。
一直到第三天时,小天才终于找到了一个玩伴,是被他的电子陀螺发出的呼啸声吸引过来的隔壁19床的一个小男孩。男孩的眼睛在术后还肿胀着,像两粒大核桃。不安让这个男孩在夜晚发出种种声响。那声响不是哭,是像是哭又像是在叫的小兽的纠缠。还有一些哭声从其他布帘里冷不防地发出,那些哭声更加放开,更加声嘶力竭,是尖着喉咙的婴儿,像最初的人类面临恐惧与不安时会发出的那种毫无保留的哭声。
我躺在皮漆脱落的蓝色行军床上,每天伴随着不同的哭声入眠。刚开始还去分辨,甚至于有些揪心,到后来,那些哭声竟渐渐成为环境的一部分,让我的神经渐趋于麻木,而快速坠入深沉如黑洞般的梦境。
3
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我身上消弭的呢?也许是从戴上腕带不能外出开始,从素面朝天和没有多少讲究的穿着开始,这一天和另一天有着太深的重复,我甚至开始两天穿着同一套衣服。一个人的社会属性消失后,才开始面对自我,也可以说不用再面对自我。面对的除了按部就班,在现代医疗体系面前乖乖就范,就是大段的意义空间的消弭。当我开始麻木时,我同时感到了出逃时间后的轻松。但是,有另外一些线穿引着喜怒哀乐,这时,我开始往晾衣服的阳台走去。小天的衣服勉强干了,但旁边那顶童帽至今无人来收。
和我们同一天进来的是18床,那是一位哺乳期的妈妈,每天穿宽大的T恤和热裤。她很快就和其他的妈妈们建立了话题,聊起了彩礼、剖宫产、母乳喂养,还有直男老公。
小天不满于我整天抱着电脑,他也许隐约觉得不公平,因为电脑通往另一个世界,另一层时间。我就想着办法给他搞好吃的。美团外卖是一个盼望,我从那里买回脸盆、衣服、被单、水果刀和刀叉,驱蚊的罗湖山,生活在这里被重建。后来开始在上面找好吃的,但护工说,不能整天帮我们拿外卖,只好转向了食堂点餐。食物带来短暂的满足,看着小天吃焖排骨吃得很香,后来又变着法子给他点烤翅、各类汤。
重复是最大的表象,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变化。每天都有新的病友进来,也会有父母带着孩子拆掉针口办理出院。更细微而迅疾的变化在身体内部,红衣护士及白衣医生每天都在和这些孩子们身体内部的疾病赛跑。
19床眼睛肿胀的男孩在两天后就出院了。新来的男孩看上去更小,由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位细挑高大穿黑T恤和牛仔裤的女性,偌大的旅行箱带着远方城市的风尘仆仆,来得很急。她一来,自来熟的护工阿姨便和她攀谈上了。表面云淡风轻,其实无比紧迫,在孩子那圆圆脑袋上,器官内部的病已生成并逐日扩大,必须加紧手术切除。“刚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呕吐,抽搐,做了各种检查,就往这里赶。”
傍晚,我向她借从旅行箱中抽出的吹风筒,吹干了滴水的头发。
4
闲逛到护士站时,服务台上摆着一份新来的报纸,还散发着油墨味,这种气味让人觉得陌生而带怀旧,像一位上了年纪的熟人。便向护士要了来,本想打发时间,翻开饱满的版面,上面记载着另一层的时间,他们光鲜亮丽,充满欢庆与胜利,握手与笑脸,与当下这些蓝色布帘内的人事无关,也与阳台上的霉湿无关,更与我的行军床和夜里哭声中的梦无关。时间在这里出现了断裂。但报纸本身是实用的,成了就餐时垫在下面的护垫。
在蓝色布帘、冷气、消毒水和婴儿哭声的空间里,唯一洋溢着欢乐气氛的,是一位女护工。她穿白色印花的制服套装,在各个病房内穿梭,手中携带着一张门卡,这张卡掌握着所有病人家属们的出入。这让女护工有了一种权力的幻觉,因为她是出入住院部规则的管理者,这个规则就是:每张病床的孩子只能放一位家长进入陪同,家长和孩子进入后便戴上那种手环带,再也不可外出。但是在早晚各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谁要走出这个楼层,通往外面的世界,或者谁要从外面进入这里,都得低声下气地央求护工在门口嘀一下。
“小辣椒!你又哭啦。”护工跨着几乎是欢快的步伐走了进来,一边用她的大嗓门逗着东床的孩子,径直往内,走到另一家雇请了她的床边,抱起里面的女婴,让女婴妈妈得以暂时脱手做点其他事。
爸爸们常常在夜里来换班,但是如果是母乳喂养的妈妈,就只能24小时地陪护在这里。比如19床那位后续住进来的年轻妈妈,孩子每次哭了,她就拎到门口,用我们听不懂的家乡话训斥几句,直到他的哭声停止,她再把孩子拎回来。到了手术前,孩子的爸爸出现了。医院动员家长献血,以保证孩子在手术一旦出现紧急状况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这位爸爸做了一番体检后,发现体重未达标,只好留在病房,他的老婆二话不说地到楼下献血去了。
5
两天后,我和这对夫妻同排坐在了楼下的大椅上,焦急地等待着手机里随时可能出现的通知信息。病房内有三个孩子在这一天安排了手术,而他们是第一台。那小男孩一大早就挂上点滴,被用车推进了手术室内。
我给那位年轻妈妈递过去一瓶饮料,她说不用了,谢谢。她和丈夫的前面摆着两个装满生活用品的塑料桶,是早上从病房搬出来的。护士告知他们,孩子手术后要住进重症监护,请家长把19号收拾出来,先在外面找个地方落脚,后续再看情况安排。我们坐在长椅上的时候,周围是医院大厅熙熙攘攘的人群,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到了夜晚,会有家长躺在这些蓝色的长椅上休息,小天爸爸早上来探访的时候,发现这里躺着人,还吓一跳。
我和那对年轻的夫妇就这样不约而同地坐在这排长椅上盯着手机。这时,她从椅子欠了欠腰身,像是和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道:“8点就进去了。”手机上已经是12点了。我也在等。
后来我收到小天爸爸的信息,说孩子从病房出来,已经被推车推着进入另一栋楼,在手术室门口等候了。我一口气跑过去,坐电梯到8楼,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问了一旁的医护,才知道跑错楼了。
等我跑到真正的手术楼时,看见小天爸爸用手举着输液瓶,而小天穿着一套不合体的病服坐在一旁,看着旁边电视上的动画片咯咯直笑。“好看吗?”“嗯,哈哈哈哈。”
冷气森然。麻醉师从手术室里出来,推出一辆推车。询问了我们一些信息后,便拔掉正在输液的端口,把他手中的麻醉液慢慢推进了针管里。这时,孩子已经躺在了拖车上,我们看着他在几秒之间,慢慢入睡。太冷了。麻醉师把小天推进的时候,让我们止步。“那,我们是在这里等吗?”“都可以。”那扇门再次关上了。小天爸爸拉着我,走出了手术中转等候室,到大厅。大厅坐满了表情焦急的家长,有些人坐一会儿又站起来走几圈。我站在大厅的窗前,往外望去,一下便望见了那个阳台,那个挂满衣物的阳台上,仿佛有我们昨天挂出去的小天的一条裤子。
6
后几日,小天爸爸和我轮流在病房里照顾术后的小天。白天的时候我在那里,到了晚上,他就从附近租住的酒店里出来和我换班。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走出那栋大楼,走在了街市当中。从现代文明进入这里的街市,恍如走入另一层时间和它的产物:旧骑楼,老榕树。当然还有各种美食店。一天傍晚回酒店的路上,看见路边的面点铺,便让老板打包了两个椰丝包和一个菠萝包。拿过包子,扫码付款,却突然问人家:“放到明早会不会不新鲜不好吃啊?”阿姨用粤语普通话笑道:“其实你都知道的呀!还要问我们。”我也忍不住笑:“是是是,可我想要你们假装安慰顾客说,‘越久越好吃啊’!”店老板便配合大笑:“系呀系呀,越久越醇香嘛。”
再次转头赶路时,橘黄的路灯将影子拖得很长。
那天手术过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19床那位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孩子。现在这个床位换了另一对母子,是从别的科室住院部转过来的。“在下面已经住了半个月,是联合会诊,在这个科室也要做个小手术。”“之前在人民医院,已经住了将近一个月,各种检查做遍,最后告诉我他们做不了。”“尽管有买新农合,但也已经花了20万。”做妈妈的,好像在描述别人的事。那男孩是乐观的,到处串门,认识了一个个阿姨。当他看我扛着个笔记本时,就好奇地凑了过来。“这是你自己写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甚至对于我打开的文档就要认真读起来,上面记录着另一些时间发生的故事。我不习惯被这样当着面凝视文本,轻轻挪开了。
后来这个六年级男孩兴奋地告诉他妈妈:“那位阿姨会写东西。”我以这种方式被认知,感到好玩。男孩用妈妈的手机加了我的微信,把他的地址发过来(一个偏远的地级市),意思是如果有一天我的书出版了,可要给他寄一本呢。出院那天,男孩走了还不忘回头提醒我一句:“阿姨,别忘了。”
7
时间再次出现断层,如同伤口的弥合,是一点点缓慢发生的。病房里的其他妈妈半开玩笑称19号床风水好,出院快。18号的妈妈依然活跃,已经和另一位妈妈约好了,等出院后一起到上下九、白马城逛街去,“那里的童装很便宜。”我走进通往阳台的那扇小门,发现独自盛开的兰花已逐渐萎谢,衣物倒是干了一大半,那顶黄色的帽子已经消失不见,新的水滴在地上打转。
责任编辑 韦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