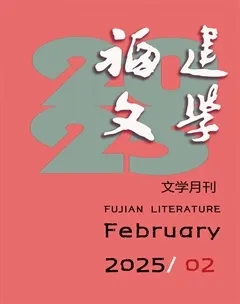诗外的工夫
新诗又称自由诗,这一定性决定诗人是自由的倡导者与履行者。正是这一宏阔的取向,让诗人有了自主选择艺术路径的权利,但有一点则是诗人必须葆有的某种共性,或者说是殊途同归的驿站,那就是工夫在诗外。这源于古人的一种提法,实则这也是古人追求自由的一种洒脱的方式,在现时仍起到精神向导的作用。任何一个有追求的诗人,都应具有工夫在诗外的本事,诗外工夫的造诣决定了这一本事的大小。
在这本诗集中,一旦我们用心分解,不难找到这一功力的投注留下的蛛丝马迹。诗人崇尚短诗,如何在有限的诗行中,让诗外的效应得以聚焦与释放,或许,这更考验他诗艺的提纯力、认识的提纯力,以及美感的提纯力。郑泽鸿就是以这高度概括与简约的形态,完成了从诗外返归诗内的作业。
人活在时间之中,时间中的生命都有个定量,决定了生命的有限性。“或许我就是那个在半夜/寻找自我的人/点着台灯又摁灭了/生怕搅醒小儿的梦。”(《灵感消亡史》)实则,这一小儿的梦,早已蕴含于诗人的创作过程之中,成为永远搅不醒的梦。用梦想拉开时间的长度,或许这是诗人延续时光的一种方式。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说,“自我不是别的东西,只使自身成为客体的产生作用罢了。”
郑泽鸿从“儿子伸出手接雨”那一欢欣中,看到了童真世界的美妙,“唯有他独享纯粹的时刻/就像这世界只有他/和上帝玩好玩的游戏。”(《接雨》)实际上,这一好玩的游戏,本身就是一首童稚赋予的纯真的诗,自然成了作为父亲的他的一种共享。正如黑格尔所言,“因为它(感觉和意识)那时与心灵相联,只有心灵才能感觉到或思维到自己在看在走,这个结论也就完全确定了。”
郑泽鸿有首名曰《凤凰独舞》的诗,其中写道:“一个人的广场舞/也可以使浮躁的人间/让出一片天地。”用一片天地的慷慨,来分享一个人的独舞,这也应是惊天动地的一种行为,实则这是郑泽鸿用浩大恢宏的场景为孤独讴歌。因为精神在推进的过程中,唯有心无旁骛方能进入那一状态。正如黑格尔所言,“人不能为别人而思维,独立思维就是证明。”正是这一独立思维成就诗中的独舞。
郑泽鸿对物的存在与定性,关注的则是它的意蕴性。意蕴性给凝固的物件发放了指代生命的通行证。“排队等候的雨伞/躲进车厢收起了生平。”(《雨中帖》)伞这与人关系密切的物件,因为人,构成了荫蔽天地的另一传奇。黑格尔说:“自然被设定为与客观的东西、思想相一致,必须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证明自我如何向客观的东西进展。”在这里,伞以具象的演示,体现着人如何向客观的东西进展的姿态,以期达到物如其人的终端。
“这些场景像薄霜覆上思绪/迟迟无法消退/他继续写,大黄鱼游在他纸上。”这是《雨夜》中的几句,诗人将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予以诗化的理解。这看似是一种互为的联合之力,实则应是不分彼此的共同驱使。从宇宙的视野看,他们本来就是共生共荣的一体。正如黑格尔所说,“人在他关于自然和有限事物的表象、思维里超出了有限性,进展到一个超自然、超感性的领域。”
在郑泽鸿的作品中,人与自然的联结与渗透,已成为一种常态,并在这一关系之间,产生有机融合的矢量。“他们每走一
步/沙滩就柔软一分/海浪就掀起更晶莹的幕布/覆盖淡蓝色的忧伤。”(《渔歌》)在这里,人实则通过自然这一更旷大的生命来填充自身,表达自身,最终完善自身。正如黑格尔所说,“就在于一切事物中都有胚芽,一切事物都是自行产生的有机物……一切东西都是结合的、联系着、都在和谐中。”
“试图借汹涌不息的潮水/把天空的蓝墨水瓶/彻底打翻/为大海留一道永恒的文身。”(《海的文身》)郑泽鸿把海天看作一个互动的整体,从西方的观念上看,这是一种聚拢而成的统一性。“声声鸟儿的啁
啾/将秋意喊得更深了。”(《遥远的回响》)在这里,他将鸟儿啁啾的空间带入秋意渐深的时间,形成相关联的共同指认。正如黑格尔所言,“谁没有这种表象统一性的想象力,谁就缺乏研究哲学的工具。”因而,从某种角度上讲,诗人就是手持这一哲学工具的一分子。
在这部作品中,自然的意识中串联着生命的意识。自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人,改变着人,自然是人生的导师。“我们没有说话/仿佛已被一朵祥云抬高/我们没有说话/仿佛大海已将全身浸蓝。”(《留云寺的潮声》)正如黑格尔所言,“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成客观的东西。”在这里,这一客观的东西呈现的正是这一循循善诱者的形象。
诗人往往将写诗当作一项精神的作业,在这作业中,或许仅凭诗人单独的力量仍远远不够,借助自然之手成为一种选择,不论这一选择是主动还是被迫,都是一种必然的指归。“波浪在船尾写诗/把柴油味的潦草几行/撕给远天的乌云。”(《在金湖一号船尾读雨》)在这里,波浪代表着自然的诗篇,在这诗篇中,有船上人在马达上操作留下的柴油味,这就是生命向自然,或者自然向生命的过渡。正如黑格尔所言,“自然被迫走向精神,精神就被迫走向自然,并且两者必定要向对方过渡,自我以及自然都可以看作第一位。”
自然是个庞大有序的系统,蕴含着无数的可能。“天空浸泡在碧潭/任水草擦亮白云。”(《月的词沼》)在常人眼里,这一逻辑应颠倒过来,应是白云凝聚成水滴,擦亮水草,但自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有的只是互通有无的循环关系。地生气,气生云,云生水,当自然打开另一视角,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正是这三者的循环往复,产生了这一关系的胚芽。正如黑格尔所言:“空气应当也同样有胚芽,这个胚芽得到了水、火等的哺育,就进入了现实状态。”或许,“水草擦亮白云”就是这一现实状态的演绎。
在郑泽鸿眼里,自然也有它的七情六欲,这一情感决定了天地拥有主宰自身的客观力量。“雪交出利刃/收割荒野/思念从此寸草不生。”(《雪》)在这里,雪无疑以其纯洁的情感,给自身带来敢爱敢恨的决绝的形象。雪是诗的化身,也是人格的典范。诗人必须在黑白分明的矛盾冲突中成就自身。正如黑格尔所说:“自我并不因为有了矛盾而解体……自我能够忍受矛盾。精神(最高的东西)就是矛盾。”
或许,一首伟大诗篇的价值在于对于真理的追寻,诗人永远在追寻的途中,“一首伟大的诗篇还未完成/它在等待窗外的雨。”(《春风帖》)郑泽鸿相信对自然的期待足以“唤醒初春的鸟鸣”。黑格尔说,“真理是具体的,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每一阶段的体系里都有自己的形式,最后的阶段就是各个形式的全部。”这个全部毫无芥蒂地交给诗与雨共同完成。
从对以上作品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郑泽鸿正是扩大到诗的外部的认识,才让诗拥有更旷大的容量、更充足的资源、更强大的后劲,以此满足精神世界的需要。
从诗内到诗外,郑泽鸿还有许多路要走,这条路关乎创造的里程,让他内在的体验产生无形通达之畅快,他的亢奋与激情之迸发也源于此。当他从纸上走向山水,“寄来了辽阔也寄走行旅”,捧起“即将决堤的桃花”;扑向大海,拥抱主动跨界的“大黄鱼”,助力“鱼群把大海钓起来”;升入云层,“为那偶然投射的一缕微光”,拧开“天空的蓝墨水瓶”。这一切旨在让天地留痕,留下诗人精神的“这一道永恒的文身”。因为诗走过的地方不设国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生命的快乐就源于这无限的开拔。诗是精神的共同体,注定了诗外的浩瀚与苍茫,注定了诗的创造永远在路上。我们相信,郑泽鸿的诗的创作之路将越走越自信、越走越旷达,因为通向精神王国的万里长征正频频向他召唤。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