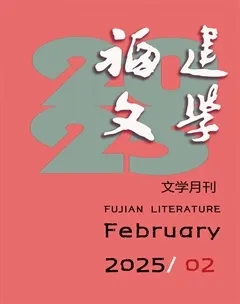塑造一个美学的海洋新天地
历史上,福州主张沿江发展,如今向海图强,发展海洋经济,弘扬海洋文化,那么海洋题材在福州故事的书写中要求更高了,因而,周而兴散文集《海峡风吟》就越来越显出社会价值了,正所谓“题材选对了作品就成功了一半”。问题是,作家的社会价值是建立在文学价值基础上的,文学性不过关,社会性就是空谈。文学创作规律表明,用对了题材还得用对叙述角度和表达方式,而叙述角度和表达方式不是光靠迎合社会需求就可以实现的,更多的要靠作家自身的德行与文学修养。
海洋,这个伟大的文学形象,立体、复杂、多元。在周而兴的笔下,大海、海岛、海风等不仅是与海洋关联的客观物象,更是他心海里洋溢着的丰沛情感的意象。观照《海峡风吟》,周而兴的倾情创作,展示出一个美学的、艺术的海洋新天地,这个新天地让人看到了作者的心灵与海洋的精神融合在一起,意蕴深远,耐人寻味。
从这部集子的笔调可以猜出一个现实生活里的周而兴:摆脱海岛少年困苦之后依然艰辛求索,显得谨慎、务实、热情、灵性。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周而兴,在海岛生长的青涩少年就怀有放飞天空的情愫,激励他一路向前;因为青涩所以珍惜,因为珍惜所以只愿关注世间万象中的真善美,回避假恶丑,这份美在心中的执着,引领他充满灵性的文学修为流连于赞颂和讴歌;因为赞颂和讴歌,他释放了自己对人世的美好祝愿,获得了生命慰藉。
周而兴处理生活题材的这种叙述角度和剪裁特色,形成他散文创作的审美起点。
掩卷回味,可以发现周而兴是个回望型的作家,眼中尽是情境,钟爱的物象被他描述得细腻透彻;他的散文是一种生活升华的记录型文脉,似乎只论世事变化而不作未来世界前瞻,只有“既然”没有“倘若”;时光伤感,光阴变幻,海岛的景象尤其入味;时代讴歌,景象变化,只谈美好,即便涉及苦难和窘迫也会用甜美化解它们。这是周而兴散文创作的立世个性,也在他的叙述表达过程之中得到彰显。
周而兴的表达质朴流畅,叙事状物喜溯源感怀,抒情表意常引经据典。他的讲述,思绪飘逸,落句洒脱;叙述起伏,言语跌宕;语气朴实,语感温润;读之如茶汤入口,畅爽之余舌底回甘。
《海峡风吟》散文集的标签是“海风”,周而兴对风的描述深刻而精彩,使他摆脱了当今散文“同质化”的境地。
集子里有很多篇作品都写了海风。比如,《走过古桥》描述“福州派江吻海”,海风吹过闽江“轻拂”古桥,《东壁岛》写福清东壁岛“海风清爽”“海风曼妙”。这些描绘体现了周而兴对海风的敏感,但都比较平淡。可是,一写到平潭海风,周而兴就生动起来了,平潭岛的海风把周而兴的文学才情刮得字里行间四处浪涛。为什么?也许是周而兴深刻的平潭生活体验造就他的题材深刻,“我生长在平潭,从小与海风耳鬓厮磨,对于故乡海风的感受尤为深刻”;也许是周而兴描述手法的巧妙,刻画出平潭海风与众不同的精妙,那种“反映肆无忌惮变化多端的天性”。
周而兴认为,“大自然的风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从天涯到海角,到处都有她的身影,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流动着。潮起潮落,她伴随波涛奔腾不息;云卷云舒,她随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只是一般的风,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的风,并无个性可言。但是,他一写到平潭岛的海风,文学性就浓郁起来了。
周而兴先说“海峡风大”,登上平潭岛,“海风便扑面迎来寒暄,让人一不小心打了个趔趄才得以站稳。”这种动感描绘一下就让海风入目穿耳。他还引用了一句民谣加强感知:“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接着他告诉我们海风是怎样眷顾平潭的:“当越冬回归的海鸥带来春的讯息,从西太平洋吹来的季风便接踵而来,直扑这座海岛。然后,这阵和煦的海风在海岛的春夏季节里短暂兜转片刻,旋即转为秋冬季强悍的东北或西北风。其间,还发飙几场凶猛的台风。”
固然,这样的描述渲染确实让我们明白了平潭海风的面貌,但是,如果只是停留于此,周而兴的讲述就会流于世俗,不过是有些文学色彩的说明文而已。令人欣慰的是,周而兴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讲述,他运用了迂回穿插、正面开掘等多种手法,进入了“入古抚今”的表达境界。
周而兴引古人名篇名句开掘平潭海风的人文内涵。他引《诗经·邶风·北风》,引庄子《逍遥游》,引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引袁枚诗句,等等,这些都是迂回的手法,加剧风的丰富性、感染性。他引清代平潭名儒施天章的咏叹,则是直面平潭特征的海风情调:“万壑俯临谁作障,一声长啸欲乘风。”这就平添了风中言志的精神色彩了,由入古再出古,引出了周而兴的海风抚今意趣。
如果说,周而兴的海风入目穿耳与入古,是物象的描述,那么,他的海风抚今则是对当下世象的叙说。
首先,周而兴把平潭海风作为苦难的象征,他用了许多情景描绘来表达风中悲怆。“风小砧板声,风大啼哭声。彼时的海风,便是渔民命运的主宰者。飘忽不定、神秘诡异的风,令人惊怵。”他还多篇叙忆岛上风沙以及风浪中轮渡的惊险和渡轮的停顿。
然后,周而兴以苦难的风为衬托,表达出人的坚强和伟大。他说:“海风也铸就了海岛人处事风风火火、爽直敢拼的性格。”通过这样的铺垫,周而兴的笔下就出现了许多反衬的叙说,变恶为善的风力发电,战胜风浪回归港湾的渔轮,高高的堤坝,坚实的石厝,悲怆化作了顽强。他这是运用世象来开掘海风物象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其中最具个性色彩的是多篇描述的“木麻黄树”和“公铁大桥”。在周而兴笔下,“木麻黄不畏惧风沙贫瘠,不追逐田地,不贪念阳光,也不需要浇灌施肥,只要有一点土壤与水分,就会顽强扎根成长、生生不息。”“台风过后,房前屋后一片狼藉,许多花木残躯断臂,落叶和树枝随处可见。然而,稍显稀疏的木麻黄依然伫立在那儿。我们给木麻黄修复整理那些弯折未断的树枝,几天后,木麻黄便会恢复枝繁叶茂,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周而兴笔下,这座建造时曾被世人称为“造桥禁区”的世界最长、最美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仿如母亲伸出有力的手臂拉住孤单的孩子”,使孤岛不再失落。他描述驱车公铁大桥的情景:“海风吹打海浪,桥边波涛翻涌,桥道上却是细风和煦,车子平稳驰骋。怎的海面上吹来直呼呼、硬生生的大风到桥上却成了强弩之末?心生纳闷,特地减慢车速,摇下车窗察看。原来,大桥两侧安装了黑科技的挡风板,这种带有降低风速与改变风向的神器,有效减缓了风力的直面冲击。”通过“木麻黄”“公铁大桥”这类世象的描述,周而兴发出了“原先我行我素的海风终于乖乖地顺应了人们的意志”的感叹,“风吹海峡,吹走了海岛人漂泊于狂风骇浪、艰辛谋生的苦涩光阴,吹来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给海岛平添了靓丽和灵动。”
最后,上述物象与世象的互动以及层层推进的讲述,使周而兴由衷地发出时代赞颂,他的讴歌顺理成章,笔下的海风文韵悠长。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以有情的写作,为时代与人心托底。题材选择的价值取向与开掘角度以及表达手法的贴切运用,使周而兴创作的立世个性获得顺应时代主旋律的文学价值。是的,如果散文写出了自己的气质,形成自己的标签,不去复制且无法被复制,就可谓自成一家了。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