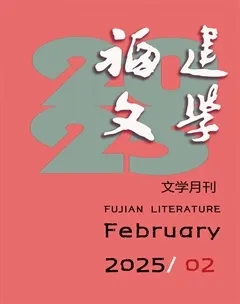推荐人语
王十月(小说家、《作品》杂志主编):
这是一篇令人惊喜的小说。
我们注意到,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没有名字的,尤其是那位“铲车司机”。作者显然是有意为之。在制造某种异质感和间离效果的同时,当这个称谓被一遍遍重复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某类特定社会属性一起参与到叙事中来,这个只会在主流话语余光里被一晃而过的群体,成为这篇小说的某种底色。事实上,跟一个个具体的名字相比,人更大程度上是按照他的社会身份被世界对待的。
能看出来,这篇小说里是有一定野心的,相比爱情和婚姻,作者更想讨论的是一些更普遍的东西:有关人的困境,如何应对困境,以及某种难以言说、无法忽略的混沌之物,它带有一些宿命主义和神秘主义,将我们裹挟,试图将我们吞噬。这应该也是好的文学作品都拥有的品质:作品文本内部隐藏的力量要超越文本本身。
作者的语言内敛但富于张力,常常在不经意中给我们制造一些惊奇。同时作者也是个营造气氛的好手,阅读过程中,那种冰冷刺骨同时又带着一些湿漉漉的气息弥漫在整篇小说的文字里,带领我们最终拨开迷雾,穿过梦境,来到开阔地带。
虽然希望并不总是好的,有时候它会让我们盲目,让我们的感受变钝,但生活总是要有希望的。只有希望才能让我们去勇敢面对命运加在我们身上的困境,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
余岱宗(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樱桃园》具有一种梦魇般的叙事效果,通过铲车司机的感知叙述,小说一直在强化文字世界构成的诱惑,形塑文字世界的危险性。铲车司机与爱读书的妻子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分属于两个世界。他无法进入妻子那极难理解的文字世界,而且意外发现妻子与作为市政道路工程师的诗人之间的关系。要不是市政道路工程师的妻子无意中的介入,几乎就要发生一个十分狗血的命案。《樱桃园》寓言般地叙述了文字世界的诱惑力与脆弱性。铲车司机的形象,更以其多疑、粗率、豪气与手下留情,显现了粗粝的现实对敏感多情的文字虚构世界的网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