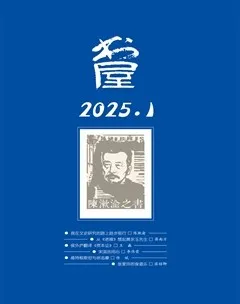我的表哥陈漱渝
写下此文标题时,我得承认多少有点炫耀之嫌。不止一次,有人对我说,原来陈漱渝是你表哥啊。这话听了叫人舒服。而且一般情况下,我还会小有得意地补充,陈漱渝不但是我的表哥,而且是血缘很近的表哥。即我的祖父是他的外公,我喊他母亲作姑妈,他喊我父亲作舅舅。
有件轶事可以一提。多年以前,有一回陈漱渝从北京至长沙出差,抽空去倒脱靴巷看望我的父亲。其时,父亲正独处一隅,兀自举杯浇愁。陈漱渝却明知故问,用长沙话说:“舅舅,你喝酒哒!”父亲闻言,正色道:“我哪里活久哒?”陈漱渝反应过来,只好一笑。此乃因长沙话“喝”“活”同音,而说一个人“活久哒”,有诅咒之意。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舅舅与外甥无意之间的幽默,给家里带来了一丝难得的愉快,所以我一直记得。
陈漱渝从事鲁迅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史研究数十年,已蔚然而成大家,但个中艰辛难以尽述。我的姑爹是黄埔军校九期毕业生,后在国民党炮兵部队任职。双方长辈出于亲上加亲之想法,撮合姑爹姑妈这对表兄妹结婚,但两人并无感情基础。姑爹偏又风流成性,在陈漱渝出生仅满两月之时,竟拋妻弃子,另觅新欢。姑妈得知,不与姑爹做任何纠缠,毅然与他断绝了所有关系,从此含辛茹苦,独自将陈漱渝抚养成人。但我们从未听姑妈说过姑爹半句坏话。她说,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直到1989年,已近知命之年的陈漱渝不计前嫌,赴台湾踏上了寻父之旅。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陈漱渝动情地写道:
莎拉台风席卷台湾宝岛。豆大的雨点密密匝匝,在水泥地面溅起一朵朵小水花。半身不遂的父亲不顾年迈体弱,双手强撑着半月形的铝合金扶手,一大早就站在狭窄的门楣下。妹妹打着伞一次次上前劝说:“哥哥乘坐的航班中午才能抵达桃园机场,您先回屋里去歇息吧。”父亲毫无反响,木然不动,任风撩起他那稀疏的白发,任雨溅湿他的衣衫。他就这样站着,站着,奇迹般地站了三个多小时,隔绝四十多年的父子终于团聚了。当我从计程车中钻出身子,向熟悉而又陌生的父亲深鞠一躬时,老人的声音和躯体都颤抖着,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漱渝,我不配做你的父亲!”
我读至此处,又联想到姑妈大半辈子的困厄际遇,不禁潸然。其实姑妈的命运曾有过短暂的转机。1952年,她经考试被中南矿冶学院录用为卫生科药剂员。姑妈带着对生活的热情与喜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料后来遭小人构陷,以“盗窃一瓶链霉素”的罪名被开除公职,直到古稀之年方得以平反,复查结论为“仅仅是怀疑,根本不能作为处分依据”。药房遗失一瓶链霉素而责任不明,却让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几乎一辈子不得翻身,在现今看来如听“天方夜谭”,但于姑妈却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
姑妈的书其实读得也不错,还会背不少古诗词。记得表哥曾回忆过,姑妈最爱吟诵的是唐代诗人元稹的《遣悲怀》,每每读到“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时,眼泪便夺眶而出,感伤自己所遇非人。
唯一值得姑妈欣慰的是,表哥陈漱渝读书虽然严重偏科,但语文成绩特别好。四岁发蒙,十六岁便考进天津的南开大学,就读于中文系。陈漱渝长我整整十岁,与我同住倒脱靴巷恐怕也有七八年吧,但印象已然淡薄。他曾经对我说过,小时候我长得还算胖,脸圆圆的,他特喜欢捏,这我更不记得。倒是后来对陈漱渝的小儿子放放,我还留有较深的印象。“文革”期间,陈漱渝在北京女八中教书,因下放的原因,不得已将未及两岁的放放送回长沙,请姑妈暂时抚养,这可给她带来了难得的欢喜。
姑妈喜欢教孙儿背唐诗。背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和“两个黄鹂鸣翠柳”之后,放放竟表现出一种非凡的才能,只要姑妈背上句,他必定能接下句。姑妈喜出望外,认定其孙出口不凡,将来必成大器。我却将信将疑,于是亲自验证,信口道:“红军不怕远征难。”放放随口便接:“旦挡当当挡当当。”我又道:“飒爽英姿五尺枪。”他再接:“挡当当旦挡当当。”这才晓得放放背诗的秘诀乃以不变应万变,不禁喷饭,弄得姑妈好几天不跟我说话。
但放放长大后终究还是成了大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来是北京电视台连续十年的春晚总导演,并且对祖母及父母非常孝顺,这当然也让陈漱渝两口子颇为欣慰。
我从来不认为年轻时的陈漱渝长得帅,他既瘦且高,像根竹竿,何况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呢。但他偏偏惹女孩子喜欢。我认识他的初恋女友,叫程茹(化名),长得非常漂亮,说话的声音尤其好听,且居然会吹口哨。我听她吹过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尤其是半音部分,真是令人陶醉。其时,陈漱渝刚从南开毕业,分配至北京女八中教书,有次回长沙探亲,通过我姐姐认识了程茹。刚开始两人在姑妈屋里一本正经谈文学,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什么的。那时候我十二三岁,也喜欢凑过去听,且听得津津有味。如果说我是在那段时日里,不经意完成了我的文学启蒙,也未可知。但他们两人由谈文学变成了谈恋爱,我却懵然不知。
后来我知道了他们最终分手的大致原因。一是双方出身都不好,加之姑妈怀疑程茹身体不好,便坚决反对。陈漱渝是个大孝子,对母亲从来百依百顺。此外,陈漱渝的事业刚刚起步,不可能调回长沙,程茹更无可能去北京工作。陈漱渝曾经回忆过他与程茹在长沙火车东站分手时的情景。在候车室里,大庭广众之下,两人“执手相看泪眼”,却被一位巡警发现,大喝一声:“你们在干什么?”他们吓得赶紧松开双手,哪里敢申辩半句。
陈漱渝从小做事笨手笨脚,用长沙话讲叫“圞手板”,除非不得已,姑妈不会让他做家务,尤其是洗碗。此乃天生的毛病,一辈子改不掉的。直到如今,陈漱渝连换个电灯泡都要喊人。我读过他的自传性作品《沙滩上的足迹》,其中有处写到他给恩师李何林沏茶,却因紧张被开水烫伤了手背,差点将茶盏摔破。他又想替李师母提放在网兜里的一钵茉莉花,不料又将花苞挂掉了好几朵,弄得李何林先生连连跺脚:“你别提了,你别提了!”
陈漱渝此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对鲁迅的研究,我虽属外行(当然不能说完全不懂),但也于此有几分兴趣。我与他虽然从事不同领域里的文字工作,但彼此应该说得上惺惺相惜。固然,表哥成就之高,我难以望其项背。我个人特别应该感谢他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参与创办《书屋》杂志时,他给予我极大帮助。创刊伊始,我建议将《书屋》定位为“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并提出《书屋》应与一般文学创作或文化理论类刊物有别,其主要作者对象应以“作家型的学者,学者型的作家”为上佳。最初去北京组稿时,对国内优秀的学者、文化人知之甚少,但我还是颇有信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知道可以通过陈漱渝广泛的人际关系,顺藤摸瓜,得以结识一大批水平甚高的作者,其中当然不乏鲁迅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此行果然收获颇丰。乃至再去上海组稿,我依葫芦画瓢,找到其时复旦大学的青年才俊张业松,借势又网罗了一批质量不亚于首都的上海作者。后来又到南京、广州等地,我自诩采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法,找到一个,便可找到一群,《书屋》杂志的作者队伍就此基本建立了。
陈漱渝是我表哥,我必得从他身上揩更多的油。说来惭愧,那时去北京出差,必住陈漱渝家。原因有二:其一,可以更方便地跟他到处跑。既组了稿,一路上又好玩。每天早上,表嫂给我与表哥每人烤两片面包,加上白煮鸡蛋一个、牛奶一杯。这是我在长沙从未吃过的“西式早餐”。吃罢便出门。我跟他拜访过多位德高望重且成就斐然的老前辈,恕不一一举例。其二,还可以省钱。住在表哥家,住宿费及伙食费一块,省下了一大笔开销。
当然,晚上躺在表哥书房里临时搭就的行军床上,几乎彻夜翻看未曾删节的全本《金瓶梅》,恶补先前洁本里的□□□□,以及“此处删去×××字”之巨大遗憾,至今仍为我最难忘怀的美好回忆。
我与陈漱渝合作出版过不少关于鲁迅的书。陈漱渝对鲁迅史料的研究深入且透彻,且擅长融入自己的独特见解。尤为重要的是,他基本上是在尽量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做文章。陈漱渝又说过,所有的史料都是死的,只有当它们被研究者赋予思考且利用后,才会活过来。诚哉斯言。二十多年前,我与他合作出版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即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这一认识。此书系我与友人王巍策划,请陈漱渝主编。但选题最初在某家出版社未获通过,理由是“几十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没有什么意思,也免得惹是生非”,我颇感失望。最后书在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印了两万册,居然还被数度盗版,以其受欢迎度而言,尚可聊以自慰。陈漱渝在此书序言中写道:
鲁迅虽然出身于绅士阶层,却从中国劳苦大众的母体上吮取着精神养分。他涤除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铸就的奴才式的家畜性,而具备了反叛一切邪恶势力的野兽性,最终成为了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民族英雄。
此段话中“家畜性”与“野兽性”的鲜明对比,迄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且具有直击人心的巨大冲击力。
说起来,我还喜欢陈漱渝编的《一对小兔子:胡适夫妇两地书》。此书由湖南出版集团下属的兄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我负责组稿,并为编辑之一。说实话,与鲁迅、许广平夫妇的《两地书》相比,我更喜欢读胡适夫妇的“两地书”,尽管前者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后者,不可以道里计。
胡适晚年时曾以“过来人”的心情,总结过他跟江冬秀结合四十余年而不离不弃的经验。他说:“我认为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没有建造和建设的才能。人家是把爱情谈到非常彻底而后结婚,但过于彻底,就一览无余,没有文章可做了。很可能由于枯燥无味,而有陷于破裂的危险。我则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我和太太都时时刻刻在爱的尝试里,所以能保持家庭的和乐。”此说固然有些许自我解嘲的成分,但说得很实在,亦可明显看出胡适一生一以贯之的禀性,即胡适从来就是个温和的建设者。这一点鲁迅与他相比,可说恰恰相反。并且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若拿许广平与江冬秀相比,我觉得江冬秀活得更加自在,更加真实。这应该也是我不太喜欢晚年许广平与周海婴的原因吧。
陈漱渝亦说过,他是在“文革”后期,“为了挺直精神脊梁”,才开始系统研究鲁迅的。四十多年过去,表哥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愿望,做了很多他所想做的事情。因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漱渝至六十七岁方才正式退休。但他“人退心不退”,笔耕不辍,文章一篇接一篇,出书一本接一本,“尚未有穷期”。陈漱渝如今已年逾八十,近年在《随笔》上发表了一篇谈生死的文章,尤其令我感佩。在此文中,他深情地写道:
我祖籍是湖南长沙,但却在战乱年代出生于重庆。八十年中真正生活在湖南至多不过十六七年。我应该怀念天津,因为我在南开大学求学五年。我更应该怀念北京,它为我提供了许多事业机遇和施展才智的舞台。除老家之外,我在北京还建立了一个新家。我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年,确实是“从故乡到异乡,从少年到白头”。但不知为什么,故乡总是我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我明明在故乡经历了很多苦难,但却一直以身为湖南人而自豪。我永远不会忘记晚清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写的那句话:“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对于国家、民族,湖南人是有担当的。我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爱国主义者。虽然故乡安置不了我的肉身,但他乡依然容不下我的灵魂。所以,我百年之后,无论如何还是要魂归故里。
除开湖南人的爱国救亡意识,故乡让我割舍不了的还有长沙米粉,无论是肉丝粉、牛肉粉,还是酸菜粉、寒菌粉,一想起就让我馋涎欲滴。我家穷困时,母亲只买了一碗米粉给我解馋,而她坐在旁边看着、笑着……那痴痴的怜爱之情至今仍灼热着我的心。
我期待表哥陈漱渝有机会多回长沙。若再回来,头一件事情还是请他去八一桥下的原味粉店吃米粉。记得上次回来,他吃完一碗双油双码的肉丝粉后仍意犹未尽,居然又叫了一碗,且再度吃个精光。表哥曾说他是个好吃的大胃王,此言确实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