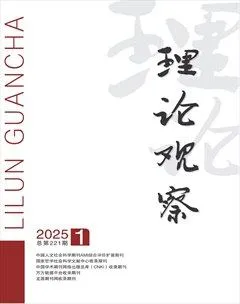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下“文化工业”的概念辨析
摘要:将《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视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或将其定性为对某种特定文化现象的批判是对“文化工业”理论的误解。实际上,阿多诺早就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对“文化工业”词源上的模糊及争议性作出阐述。霍克海默也曾在《论真理的问题》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观念论之所以不同的根本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本文认为,要回归“文化工业”的真正内涵,必须结合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文化工业”作为历史范畴,是一种非文化且“另有所图”的事物,不仅是以文化形式出现的“特殊商品”,更产生着“文化拜物教”一般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文化工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启蒙辩证法;阿多诺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25)01—0055—06
通常认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贯穿于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历程始终的重要议题之一。由此,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在其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也自然被视为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许多学者将“文化工业”等同于对大众文化现象和价值的讨论,而与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比如同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甚至是早期文化研究思潮中的伯明翰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例如威廉斯、汤普森、霍尔等。实际上,这种比较无益于我们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理论,这使得“文化工业”失去了其哲学理论基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究其根源,这源自我们对“文化工业”概念的误解。一方面,“文化工业”的真正内涵不在于对大众文化的现象批判;另一方面,“文化工业”的探讨域与大众文化批判和一般文化研究是截然不同的。若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文化批判的一般性理论进行解读,就会产生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从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流俗为对一般文化现象的批判和文化方面的敌意与傲慢,甚至造成其理论合法性的问题(例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中所产生的“基础-上层建筑”矛盾问题)。
要理解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必须摒弃“文化工业”等同于“大众文化批判”的传统认知,并重新审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内众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例如,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李乾坤;复旦大学的王凤才等)所支持。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多人一贯具有“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哲学”、放弃所谓“成熟马克思所关切的问题”的误解。在这种解读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失去结合马克思这一理论渊源的合法性,从而造成“两个马克思”的认识断裂。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对于汉语学术界来讲,法兰克福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依然是一片尚待深入的研究领域。于是,目前对“文化工业”的大多研究仍忽视着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重要基础,将“文化工业”理论简单处理为对大众文化的“现象批判”。为纠察这一误解的根源,首先应当回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本人的所公开发表的文本,结合《文化工业再思考》和《论真理问题》这两篇文章,再思考“文化工业”的真正内蕴。
一、“文化工业”概念的深层内涵辨析
(一)词源模糊性及学界的误用
首先,阿多诺的文章《文化工业再思考》(1967)曾明确辨析“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区别,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化工业”理论。阿多诺曾经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作出以下说明:“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这个术语可能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该书。在我们的草稿中,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culture)。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popularart)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1]翻阅这篇文章的原文可以得到,阿多诺在此处严格地区分了“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的区别。在该文章的原文中,这几个概念所对应的德文单词也有所不同,分别是Kulturindustrie、Massenkutur和Volkskunst.
由此可知,对于他和霍克海默而言,“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并不等于“大众文化”(massculture),也不等同于流行艺术(popularart)的当代形式。他们正因担心出现这种误解,才在《文化工业:作为群众欺骗的启蒙》中使用了“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这个概念,而非草稿中原定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便表明了“文化工业”这个概念在词源上的模糊性和争议性。这篇文章的问世比《启蒙辩证法》迟了二十余年,因此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在这篇文章出版后的很长时间内,大众对“文化工业”理论的解读仍仅基于《启蒙辩证法》的参考,而较为广泛地对“文化工业”产生着词源上的误解。人们通常语境下的“大众文化”是从人民群众中诞生的,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天然的文化需求和文化从业者的创造性共同作用下能动地被创作出来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文化工业”则不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披着文化形式的工业产品,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品,亦即“文化工业”。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明确阐释了他对这种误解的担忧,并且因此解释了之所以在《启蒙辩证法》的草稿中使用“大众文化”,而在最终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使用“文化工业”的原因。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这里,明显可以得到,“文化工业”的实践的全部目的在于赢取利润,这一点与马克思的商品交换理论不谋而合。阿多诺指认,“文化工业”所投射的客体——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实则也并非是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形式”只是承载着“文化工业”盈利目的的一种无灵魂的躯壳,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非真正的文化产品。
(二)“文化工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基础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多次提到其关于文化领域的认识具备着坚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这也提示着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渊源处,对“文化工业”的阐释路径再作寻觅。
霍克海默1935年在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第4卷第1期的《论真理问题》中通过对比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体系,指出其理论的缺陷与进步,最终对辩证法及马克思哲学体系作出评价。霍克海默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克服西方近代哲学之对立的最宏伟的尝试,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却是不为唯物主义者所认同的,因为当黑格尔把一种整体性赋予某个历史阶段,即他自己的哲学,并把它视为绝对真理时,便又陷入了新的教条主义。这也体现出传统形而上学“天真的”特点。形而上学总是基于各种观念产生其“幻想的基础”,然而现实社会中的“内在机制”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压力却从未被揭示出来。由此,霍克海默通过《论真理问题》将理论的目光从观念世界转移至现实社会。从而以大段篇幅论证并认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现实社会的重要性,即“社会中的某些现实趋势被理论化后的“相互关系”体现为——大资本的积累与整个社会阶层的比例失调、失业率的上升、社会劳动在各种商品中的分配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等等。霍克海默指出,以上的这些过程早就被马克思所论证且重视了,并且这些政治经济学现象在理论探索中是十分必要的。但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似乎只有少数几个先进国家正在对此进行研究,而且还处于萌芽状态,(在当时)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所崇尚的前景似乎还很美好。然而,霍克海默指出,历史现实在发展中不仅首先预言且认定了这些批判性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还证明了它们的必要性。霍克海默同时指出,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一般的初始存在,马克思从其中发展出了价值概念,从而产生了与这一切密切联系的货币、资本等范畴。而上述的一切经济“相互关系”则都由价值这一概念所设定,并以现实逻辑可以层层递进、推导出来。霍克海默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一方面,它具有现实的实践性。因为现实的人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指导下所做的努力,可以防止社会重新陷入“野蛮状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是经过历史进程所证实的理论,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永恒式的理论,而代表着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实践时刻。正如霍克海默所说一般,这是与受到威胁的人民的全部急迫感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理论。另一方面,它具有理论的基础性。因为对所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理论认识都可以通过商品的一般概念这一原初的认识而被中介得到。[2]
在这里,应当注意到:霍克海默认为,我们关于“文化领域”的认识,是通过“价值”这一原初的认识,而被中介得到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普遍性概念推导出“价值”。霍克海默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之后的大多经济范畴都由“价值”这一概念所设定,正如列宁所说一般,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包含着一切尚未展开的主要矛盾[3]。商品作为“第一个最一般的概念”,在马克思而后在《资本论》的论述中逐渐丰富其内蕴,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正如霍克海默所指认——“其抽象性随着理论的发展而被克服”。商品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霍克海默认为,对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所有认识都是由商品交换这一“原初的认识”而被中介后所得到的。由此可以察觉,霍克海默对作为一个整体领域的“文化”的认识,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文化工业”作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论述文化领域过程中所提出的重要理论,我们通过霍克海默参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所勾勒出的批判理论范式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若要真正理解“文化工业”的深层内涵,便应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相结合。绝不能将“文化工业”的批判对象简单归为由大众文化流行而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旨在通过“文化工业”对社会作出整体性的批判反思,而非对某种表层的文化现象作浅显否定。实际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借用“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批判伪装成文化,实则并非文化,且另有“所图”的事物。
二、“文化工业”实质:非文化且“另有所图”的事物
在传统大众文化批判视域中,通常将“文化工业”视为一种流行文化于大众而言的负面形式,或是指认文化作品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一环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却很少有将“文化工业”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而进行的探讨。“文化工业”实质是非文化且“另有所图”的事物。首先,“文化工业”实际上是以文化形式出现的、以逐利为主要目的的商品。它在诞生之初便与其他的文化产品有所不同,因为文化产品通常包含着审美的意蕴,是为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的产物。而“文化产业”自诞生之初便带有逐利这一目的,其全部的实践意义也在于此。其次,在“文化工业”诞生后,便会演变为一种“文化拜物教”,也就是在逐利这一经济功能的基础上,又带有了“意识形态”熏陶这一政治功能。
(一)作为“非文化事物”的“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实则是将“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的非文化事物。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分别的承接。
阿多诺曾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强调文化变为商品后的逐利性。在文化工业的各个分支中,“特意为大众的消费而制作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的那些产品,或多或少是有计划地炮制的。”也就是说,文化工业之所指不再像是从前古典艺术家们所投入激情与创造的文化产物,而是为了在大众群体中获取利润而有计划地“炮制”出来的。亦即,当“文化”和“艺术”成为资本的附庸,成为逐利的产品,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和“艺术”便变为了非文化、非艺术的东西,即“文化工业”。因此,“文化工业”并不能称作是大众文化,而只能是一种“工业商品”。
针对劳动的不同性质,即生产性和非生产的区别,《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4]生产劳动所生产的是用于资本增殖的商品,而非生产劳动创造的则是使用价值。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一个受社会关系所限的历史范畴,二者的界限是相对的。马克思指出:对于消费者而言,饭店中的侍者和厨师的劳动行为属于非生产劳动,而对于饭店老板来说则是生产劳动,“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但如若老板将这些人视为家仆,那么他们便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家仆的服务并未创造资本,雇主此刻也仅是将自己的收入花费在这些服务上。[5]生产劳动者为他们的雇主(即他们劳动能力的买者)生产商品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参与资本增殖的过程。但非生产劳动者为他们劳动能力的买者生产的却只是使用价值。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这种使用价值是“想象的或现实的使用价值,而绝不是商品”。[6]而当这种使用价值进入文化领域之时,便体现为阿多诺所强调的出于激情所能动创造出的文化产物,比如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但“文化工业”却是在经济上参与资本增殖过程并纯粹属于商业范畴的“工业商品”。由此,马克思明确地总结: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当文化领域的产品不再服务于想象的使用价值,而是服从于交换价值时,便普遍地变为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所言的“文化工业”。
同时,《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英国作家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创作《失乐园》和莱比锡的“一位无产阶级作家”为例生动说明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
文本明确提出,约翰·弥尔顿创作《失乐园》后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即“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7]弥尔顿作为十七世纪声名鼎赫的文化从业者,未曾经历工业革命,也未曾置身于阶级社会,他的作品属于英国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失乐园》是纯粹出于审美和文化需要而诞生的。《失乐园》不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消费和文化需要而被“炮制”出来的,便不属于“文化工业”,而是他天性的“能动表现”。在这里,《资本论》中所提到的“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天性的能动表现”和阿多诺所强调的古典音乐创作家的“激情、创作”实则是一回事,都是一种在文化领域的“非生产劳动”。阿多诺认为,只有这种“非生产劳动”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文化、艺术,而“文化工业”则不然。
与之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7]处于十九至二十世纪撰写剩余价值理论批判的作家属于无产阶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阶级范畴出现的一刻起,就意味着它生存并服从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随着阶级差距的分化,即便一位作为无产者的作家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旨在批判资本,也只能归属于“劳动产品”。因为这种文化产品经过发行商与书商的出版和销售,便会使作家成为提供工厂式劳动的“文化商品”生产者。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别,《资本论》中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例证,上述关于作家的论述是在文化生产领域最直白的一个例证。由《资本论》上述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区别的例证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可以理解,“文化工业”实则是处于文化领域的劳动变为了一种“生产劳动”,而非“非生产劳动”。文化领域的创作普遍地变为以逐利为目的的生产,“文化工业”便诞生了。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
当“文化工业”被造就后,则不再满足于逐利性,而是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公共关系,这是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颠倒了的意识(即意识形态),到《资本论》中拜物教思想的接续。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处的年代,“文化工业”实则产生着“文化拜物教”一般的负面影响。“文化工业”不仅拥有商品的逐利性,同时也具备着服务、巩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处的历史时期,在致富欲的推动与极权主义的操纵下,人们越发地创造出“文化工业”、沉迷于“文化工业”,就越成为“文化工业”的手段,最终使主体意识屈尊于意识形态的强权之下。
《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形态》)在批判传统的观念论时曾指出意识形态的颠倒。现实的人的生存与实践困境导致了颠倒的意识形态的产生。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局限性的产物,更是资本主义整体下无产阶级生存境遇的真实反映。马克思在《形态》的手稿中说明,人有关于自然界、他人、自身的观念都是由现实生活得来的,“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颠倒”根源于现实的“颠倒”。但在《形态》这一阶段,马克思还未能完全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深入到资本增殖过程的内核。马克思也如此作出说明,如果要彻底澄明曾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说明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意识形态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务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而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出发。”[9]直至《资本论》,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生产关系,达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准确而全面的批判认知,才在真正意义上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职业和分工”出发,从而完成了这一“说明”。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物教”概念。“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在《形态》中“颠倒了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接续。拜物教原指在原始社会,人们限制于自身的实践水平,缺乏科学知识,无法理解自然现象,从而将自然物神化,把它们当作神来崇拜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拜物教”观念,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一方面,拜物教体现为主客体的颠倒,主体本来作为产品的创造者应当主宰并使用自己的创造物,但在以逐利作为目的的行为驱使下,将能主宰其命运的客体神化,而产生崇拜般的迷信。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体现为对消费的无限沉迷、对物欲的无限追求及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另一方面,在拜物教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在拜物教的主客体关系中,客体不再局限于“物”本身,而演变为物化了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就在于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0]
“文化工业”实则产生着“文化拜物教”一般的负面影响。首先,在“文化工业”面前,正如阿多诺所论述的一般,大众绝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亦即,大众是被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顾客并非上帝,不是文化产品的主体,而是客体。这就导致了主客体的颠倒,人作为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本应是审美的主体,如今在“文化工业”的逐利性面前却变为了被算计的客体。这种主客颠倒的状况使得顾客仅仅是“文化工业”的消费者,而非“文化产品”创造者和享有者。顾客在“文化工业”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作为被资本剥削的一分子,心甘情愿为“文化工业”商品买单,从而参与到资本社会的商品交换过程当中。其次,人民群众在“文化工业”中麻痹自我,以获得由于阶级矛盾而导致的悲惨现实中的短暂宽慰。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在表面上拥有不同的形式与风格,“文化工业”则戳破了这些风格背后的秘密——即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遵从。[11]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纵横,在这种状况下,人们越是探讨所谓的“文化”,就越是被已经代入公共关系领域的“文化工业”所索引和分类。因为现实的冲突导致人的不平等状况,文化工业作为资本的产物实则加强了阶级的固化,使原本平等的个体被不断地分类、标签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电影为例说明了这一点,电影生产商为观众炮制出各种文化垃圾,这种文化工业使人们感到欣慰,“使所有人都认为自己依然可能会有坚韧的和真实的命运”。与此同时,这种命运一定是一种“拒不妥协的命运”[12]而在资本现实中,无产阶级的命运很多时候却不为自身所掌控,而表现为资本的支配力量。也就是说,在文化产品中所描述的在敌人和苦难面前,人们所表现出的“勇敢、自由的情感”,其根本在于现实的个人与资本社会根本对立的这一社会实体。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处的二战时期,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权威力量吞噬了人们的反抗能力,这正是通过文化工业“从孤立无援的人们身上获得整合的奇迹”而被表现的。社会根本矛盾被文化工业所表现出的被迫害者的所谓的勇敢、自由等情感悄然无息地掩盖、包裹住了,这使极权主义的残酷行径变得“温文尔雅”。[13]于是,“文化工业”也变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于社会结构中,如同马克思从《形态》到《资本论》所论述的“颠倒了的意识形态”和“被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一般,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文化工业诞生之初以逐利的姿态,成为“彻头彻尾的商品”。随着商品逐利性质的不断发展,便不再仅仅满足于致富欲,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公共关系、意识形态。正如阿多诺所说,文化工业曾经是从直接追求利润发展起来的。而如今,“利润带来的这些利益已经在它的意识形态里对象化了,甚至已经使它们自身独立于售卖文化商品的冲动之外。”也就是说,“文化工业”此刻便转化成为维持资本运转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产生着“文化拜物教”一般的负面影响,而不涉及特定的商社或可销售的货物。
三、反思与启示:“文化工业”与“当代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历程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引领了一时的学术热潮。这一理论,根植于二战烽火连天历史背景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土壤,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观点,更是一个深刻反映时代特征的历史性范畴。
文化工业理论深刻揭示了受资本增殖驱动的文化所遭受的根本性负面影响,同时,它也潜藏着对极权主义政权和当时美国大众流行文化的深刻批判。文化工业在资本的操控下,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性和多样性,成为了一种标准化、同质化的商品生产模式。这种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不仅削弱了文化的批判性和创新性,还进一步强化了极权主义政权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同时,美国流行文化作为文化工业的典型代表,其表面的多元与自由背后,实则隐藏着资本逻辑的深刻影响,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对“文化工业”进行再辨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新形态,更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对文化霸权和资本逻辑的清醒认识,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推动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立性的发展。
简单地将“文化工业”与某些负面文化现象(如低俗文化、落后文化等)画等号这一误解遮蔽了“文化工业”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事实上,“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它并非大众文化的同义词,而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生产模式的一种深刻剖析与批判。作为学术范畴的“文化工业”,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机制的一种深刻揭示,更是对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探索。但同时,无可否认的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也暗含着其对文化审美精英主义式的傲慢和否定性批判的态度。因此,在理解“文化工业”时,我们应超越表面的标签与误解,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与历史脉络,以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
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推动“两个结合”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从理论层面剖析,深入挖掘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深刻哲学内涵,并提升文化哲学在学术体系中的重视程度,具有极为显著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保持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文化,而且我国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具备开放性才能在此基础之上交流、融合,经过涵化进行文化创新。我国文化也是创新的文化,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社会进步才能具有持续的力量。[14]在现实实践中,面对广大民众广泛接受并喜爱的丰富文化现象,我们应秉持继承与发展的积极态度,而非简单地采取否定性的批判视角。结合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再思考能够给予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启示,具体而言,这要求我们明确区分“文化工业”与“当代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与界限,并针对两者采取不同的理论立场与实践策略,以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与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TheodorW.Adorno.CultureIndustryRecons-idered[M].DukeUniversityPress,1975:12.
[2]MaxHorkheimer.ZumProblemderWahrheit[M].ZeitschriftfürSozialforschung,JahrgangIV.Heft3,1935.
[3]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6.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0.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1.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6.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2009:524.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4.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9.
[11]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8.
[12]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7.
[13]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9.
[14]丁立群,陆鹏飞.全球化视域下我国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和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4):81.
〔责任编辑:侯庆海,周浩〕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