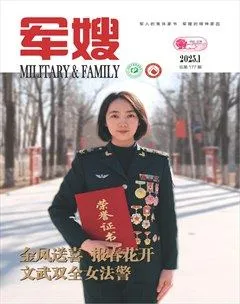我家兵故事
一
父亲在世时,很少讲他当兵时的事。那段经历于我们姐弟几个来说,就像他的人生留白。
在我们眼中父亲很普通。父亲长年在外工作,偶尔回家,不是在院里编筐打制农具,就是到地里侍弄庄稼,对别人总是和和气气,对我们却常常板着面孔,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不敢亲近他。
一副对联改变了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
我们家在村子贯穿南北的一条街边上。小时候,每到元旦,长长的街道上只有我家已贴着红彤彤的新对联,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格外惹人眼目。
我曾经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别人家只有春节才贴对联,而我们家这时候就贴上了呢?”
母亲笑着说:“你爸当过兵打过仗,每到阳历新年,政府都会给当过兵的人家送对联。”
“啊?爸爸当过兵打过仗!”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原来我们的父亲也是英勇战士中的一员啊。那不是普通的对联,是父亲一段过去的历史,是我们家庭的一份荣光。这让年少的我为此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无形中也对父亲产生了一份崇敬的情感。
大姐中学毕业后,突然有一天告诉父亲,她想去当兵。大姐以为,父亲作为老兵一定会为她的这个想法高兴不已。
父亲却面露难色。他知道,当时很少从农村招女兵,他怕大姐愿望落空失望。父亲问大姐,为什么要当兵?大姐说,穿上军装很神气,保家卫国很光荣。
父亲说,你先在家好好劳动,然后找一份工作吧。大姐听不进父亲的话,依然对部队充满向往,一心想要当兵。当时,大姐对父亲很不满,还偷偷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愿。我还看到兵团给大姐的回信,大意是让她安心劳动,无论在哪里都能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大姐哭了。当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是她唯一的心愿。情急之下,大姐为当不了兵而怪罪父亲,还因此和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当大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长相漂亮的她吸引了不少追求者。面对常来登门提亲的媒人,大姐问:“是当兵的吗?”
“不是。”
大姐把脖子一拧:“不见。”
就这一句话,便把媒人撅在原地,气氛很尴尬。
大姐告诉父亲,自己非当兵的不嫁。
知女莫若父。从此,父亲总是留心周边谁家的儿子在部队,以便将人家纳为大女婿人选。
那年,父亲打听到邻村有一户人家的儿子正在上军校,顿时有些激动。他没有办法帮助大女儿实现当兵的梦想,便一心想寻一个“兵女婿”。
在一个秋日的上午,父亲换上一身整洁的衣服,急匆匆步行去了邻村。
那户人家对父亲很热情。但父亲知道,军校毕业就是军官,而且听说给那家儿子介绍对象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甚至还有姑娘自己找上门来。所以,父亲心里很没底。

父亲为人正直善良,受人尊敬,三乡五里留有好名声。那家人早就听说过父亲,知道他的来意后,还没有见过大姐,就一口答应了。他们觉得,像父亲这样的人,教育出来的女儿肯定错不了。
从此,那家便拒绝了上门的众多媒人,也直接挡住了上门求见的姑娘。后来,那名军校学员放假回来,与大姐见了面,二人一见倾心。
家里多了个“兵女婿”,父亲常常引以为荣。当时,我还不知道,对一个老兵来说,那是一种融入骨子里的骄傲。
二
我上班以后,父亲已退休在家。那时的他,已然没有了早年的严厉,一脸的和蔼慈祥。一个秋雨淅沥的午后,许是闲来无事,许是有意为之,父亲竟给我们讲起了当兵时的事。
父亲坐在炕上,伸直双腿给我们看。我们这才发现,他的右腿竟比左腿稍短一些。
尽管我早就知道父亲是残疾军人,而且民政部门每年都给父亲寄来一双皮鞋,是专门为他订做的:一只鞋跟高,一只鞋跟低。父亲走路稍显异样,可我们谁都没有特别留意过。
那是父亲第一次主动和我们说起从军往事,也是第一次让我们看他的腿。
父亲淡然地说,他是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负的伤。
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他说,自己在一场激烈的战役中负伤昏了过去,后来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一名年长的战友又叹息又心疼地说:“唉,要落到敌人手中,你就没命了!”
父亲说,那天,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举目望去,身边都是牺牲的战友……说着说着,父亲的眼圈就红了。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他的眼中,充满了我们从没见过的沉痛和悲伤。
父亲说,你们赶上了好年代,一定要珍惜,干工作不要怕苦怕累,要有眼力见儿,虚心学习,要尊重年长的同事。父亲的这些话,我们听过好多遍,我们姐弟几个不论谁离家走上工作岗位,他总要这样叮嘱一番。
父亲退役后,一直在商业部门上班,后来担任了部门领导。每年秋天,是收购货物的旺季。一天,有人来到家里,和父亲说了许多客套话,最后硬是塞给父亲一个小纸包就想离开。父亲原本温和的面容一下子严肃起来,见那人已经迈出屋门,他几乎是跳起来去追,硬是把纸包塞回那人裤兜里。送走那人后,父亲坐在炕边久久没有说话。
原来,来人与父亲早就相熟,想让父亲把单位收购的花椒压低价格给他,差价和父亲平分,并给父亲送来200元钱。不能贪污、不能受贿,是父亲坚持的原则,也是对我们姐弟的要求。大姐结婚后,父亲对在部队负责财务工作的大姐夫,也是这样反复叮嘱的。
三
弟弟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我们姐妹工作、成家后,高考落榜的弟弟四处打工,生活漂泊无定。
那时,父亲已经年迈,肺气肿严重到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来。父亲整日为弟弟的将来发愁,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说他年纪轻轻就在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打工不叫个事,很难有什么出息。
父亲深知,部队是个大熔炉,让孩子当兵去部队是最好的选择。父亲便给大姐、大姐夫去信说起弟弟的情况,商量着想让弟弟参军入伍。当时,我们虽然都赞成父亲的想法,但内心也很纠结,他和母亲年岁大、身体不好,正是身边需人照顾的时候。
那年,从弟弟参加征兵体检开始,父母便茶饭不想夜不能眠,心里有太多太多的不舍。后来,听说接兵干部要来家访,父亲对母亲又是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她说出“舍不得”而拖了后腿。
弟弟离家那天早晨,天上飘起小雪。父亲没去送弟弟,只是在家里反复叮嘱他:“到了部队要服从安排,踏实做事,争取当个好兵。"”
父亲的身体,已如风中残烛。在不时的咳嗽和艰难喘息中,他常常对我们说:“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哪天一口气喘不上来,你弟弟都赶不回来啊……”
果然,弟弟入伍不足一年,父亲的病就严重起来。1998年初,父亲临终前,眼睛始终盯着门口,我们知道,他在等弟弟。
弟弟归来时,父亲已去世3天。为了让弟弟见到父亲的遗容,我们也不得不将父亲的葬礼推迟。
父亲去世后,弟弟在部队更加刻苦,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后来被调到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弟弟在部队服役12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荣立1次三等功。
从部队退役后,弟弟被北京一家杂志社聘为编辑、记者,2024年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弟弟常对我说,一朝入伍,终生是一个敢打硬拼的兵,他一直感激父亲当年让他走进部队,使他有了用武之地,练就了一技之长。
是啊,无论我们姐弟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在部队服役,父亲的引导和叮咛始终伴随着我们前行。
2023年,我有幸为家乡整理村史,数次跑县党史办、档案局、地名办等单位查证资料。让我震惊不已的是,我们那个小小的山村,在战争年代竟有近百人离家奔赴前线。他们有的血染疆场、埋骨他乡,有的身负重伤、落下残疾,有的退伍还乡、默默劳作……
对父亲的详细履历尤其是从军经历,我们一无所知。一筹莫展之际,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父亲生前的工作单位,居然找到了他的档案——
牛亭祥,男,河北省易县牛岗乡台底村人,1928年10月出生,1944年8月入党,1948年2月参军,某团战士,曾参加平津战役,1949年1月在执行任务中负伤,1949年11月退伍回乡,1956年参加工作,1988年退休。
父亲的这份档案,就像一幅人物简笔画,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也清晰地记录了他的人生步履。细细想来,我们姐弟几个踏实进取、与人为善、和睦相亲的品质,何尝不是为父亲的人生简笔画补充了细节,让他的形象完整清晰……
(作者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