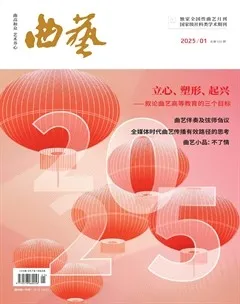管窥“非遗”保护下曹元珠河南坠子艺术传承与发展实践
20世纪初,河南坠子源起、盛兴于河南地区,后传至山东、河北、天津、北京、上海、南京、香港、甘肃等地,唱响大江南北,流派纷繁,名家众多。作为非遗代表性优秀传承人,曹元珠历经两个世纪、80余年的舞台生涯,形成独特的艺术演唱与表演风格。其唱腔设计曲调新颖,手法高妙。同时,培育出多名富有新时代精神的中青年艺术家,在“非遗”保护的指导下,推动着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创作迈进。
一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5〕18号)以来,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加强实施了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并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① 16字方针作为非遗工作的行动指南。对此,天津市政府和市文旅局积极落实中央精神,制定出台相关措施与方案,开启了对河南坠子等曲艺曲种的传承保护,并不断改善曲艺音乐生态环境,使河南坠子等曲艺音乐曲种得到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百余年前,河南坠子形成于河南乡间,由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曲种交融而生。民国初期,经大运河水旱之路传至津门,其大书、中篇、短段(以唱为主)诸形式见于津门书场、茶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艺人乔清秀、董桂芝、程玉兰相继来津登台献艺,成为一代久负盛名的河南坠子三大流派。同时,家族式的河南坠子演唱班社更是琳琅津门,龚家、武家、苑家、马家等河南坠子家族群体,以群口、单口、双口形式布满老城东、南、西、北园子书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更有王元堂、王宝霞、曹元珠、武艳芳、苑宝珍、杜凤兰等一大批河南坠子中青年艺人,活跃在九河下梢天津卫的曲艺大小剧场。他们的演唱风格各具悠长,技艺夺人,形成北方河南坠子的生力军。
曹元珠(1931.8—2019.2),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曲艺教育家、曲艺音乐革新家、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现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第五届中国金唱片奖获得者、河南坠子曹派创始人,历经两个世纪、80余载,携艺走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将河南坠子从浓郁乡俗到华丽都市形象转化的一代演员,更是首位唱响东方明珠-香港的坠子艺术家。20世纪50年代初,她由旅居上海、南京等地归落津门,成为市曲艺团演员,55岁盛年时,入职中国第一所曲艺学校,成为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河南坠子专业首任教授、专职传承人,为河南坠子的传承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曹元珠先生一生勤奋向上,执着进取。在演唱、表演以及唱腔艺术设计创作上,不断继承和弘扬前辈传统技艺优长。同时,勇于追寻时代审美趋向,创造出易于南北观众接受的河南坠子声腔,她的《杨七郎打擂》《宝玉探病》《秋江》《战马超》《黛玉悲秋》等多部艺术代表作品,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天津音像公司等媒介出版唱片、CD、DVD影像艺术品,为河南本土以外的坠子传承发展、发扬光大做出极大努力和成就。曲艺评论家、理论家、南开大学教授薛宝琨曾这样评介:“曹元珠老师的艺术经历和成就令人十分感动。她的经历基本反映了坠子这一民间形式由农村而城市、由长篇而短段、出粗粝而滑细日臻完美的成熟过程。她不仅是这一过程的生动缩影,并且是其间最能动最富创造力的元素……曹元珠的每一步前进都烙印着这一形式的发展足迹,坠子的每一变化都是曹元珠进取的目标。”②由此表明曹元珠在河南坠子发展历程中的显耀地位。
曹元珠先生在唱腔设计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坚持以唱词立意为中心,曲调与唱词的内容密切相依,许多经过重新修辞、重设腔调的传统唱段颇具时代观感,而表达当代的新词,则打破固有的唱腔结构范式,形成长短不一、形式多变、上下句关联通畅的腔体。在演唱上,她的“悲”曲令人为之痛泪,“俏”则灵动美巧,“情”则舒展深邃,“脆”则不拖泥带水。灵动神似的表演,逼真的情境塑造,呈现着风趣幽默、虚拟空幻、顽皮奸诈、威武彪悍、乖张泼辣等众多形象,赢得了几代观众的喜爱与赞捧。
二
作为天津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曹元珠先生在继承传统河南坠子美学表达方式的同时,执着追求与时代相符合的人文精神,不断将艺术作品“拆洗”“复创”“提升”“出新”,增强河南坠子艺术的时代感染力。20世纪80年代,当其由演出团体调到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后,更是遵循“出人出书走正路”的宗旨,老骥伏枥,勤奋教徒传艺。一方面课堂口传身带,严苛指导,并亲自登台示范展演技艺作为引领。另一方面则创新出新,与词作家、曲艺理论家王济先生、杨妤婕女士合作,为学生唱腔设计新段,力推《黎明灯火》《擂鼓战金山》等多部与时代相宜的作品。其曲段腔调新颖,为了增加舞台气氛,更贴切地再现古战场鏖战厮杀之况,首次尝试加入花盆鼓的击打,与音乐相得益彰,一举荣获首届中国鼓曲唱曲金奖。同时,她率先鼓励学生、弟子们勇于跨界、跨曲种、跨流派学习融汇,破除保守和故步自封,告诫弟子必须坚守、继承传统河南坠子优秀基因,在本体属性不变的前提下大胆革新尝试,积极运用现代艺术形式,推动河南坠子向更高更远的发展迈进。
三
21世纪是一个现代科技飞速发展、艺术文化多元的时代。大众审美的趋之嬗变,也带给传统艺术在传承、传播、发展上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全面的传承保护计划,使传统说唱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救护。倡导的“在传承中提升转化,在发展中创新”,更令曲艺音乐发展前景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中指出:“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③如何将讲话精神作为本行业发展前行的理论指导、实践航标,弘扬光大河南坠子,构造具有时代精神、传统与现代理念相融的艺术作品需要深入思考。笔者认为,河南省域以外的坠子面对困难重重境况,势必在坚守传统的同时,更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勇气,多维的思辨能力,以及采用现代性发展手段与方法为策略,在唱法、发声、用气等方面独树专道。
自1986年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随师学艺,30多年来,笔者从“小白”到“模学”再到独立“唱新曲”,不断地将河南坠子延袭承传、锻造提升,并奋力在实践中演化出新。从过去时走向现代时,继往开来地奔向未来时,力争在传统河南坠子本体腔韵下有所突破,构造与时代精神相和、人民大众喜爱的艺术作品。与师辈不同的是,笔者学艺初萌时期,恰逢流行音乐、通俗歌曲兴盛之始。因而,在师父不保守观念的鼓励下,学习演唱了大量的通俗流行歌曲,同时兼修了河南坠子以外的曲种(京韵大鼓、铁片大鼓、时调、单弦岔曲以及诵说类的相声)、跨界的艺术表演门类(小品、影视、节目主持)。这些实践自觉与不自觉地在笔者对河南坠子本体的演唱方式、唱腔声韵、舞台表演等方面产生影响,也成为自己创造河南坠子现代艺术表达的动力,并不断地在演唱的新作品中大胆摸索、累积、放大、衍生和出新。实践证明,尽管在传统艺术本体上我们难以超越前辈,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传统曲艺音乐艺术在现代理念的推动下,正朝着适于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而动,其曲韵声腔、歌唱方式方法都会更加贴近时代感,艺术创作思路、艺术视野变得越来越宽广,加之高科技手段的应用,超越前人、令河南坠子呈现现代性艺术发展有了更多、更好、更有效的途径与可能。
首先,在继承传统声腔伴奏方式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电声乐器衬奏、现代MID编配制作等手段,大大提高了河南坠子音乐的音响效果,新创曲段《秋红赋》便是这一实践成果的代表之作。《秋红赋》唱词描述了百花斗艳的美丽景致,“秋花、秋果漫山岭,天蓝水绿枫叶红……玲珑的小豆红啊,敦厚的倭瓜红。酸甜甜的山里红,麻辣的辣椒红,灯笼般的橘子红……”。一幅幅可人、美妙的秋景,展现着“红”的画卷,浓烈的时代气息,纯美昂然的诗情画意,传统器乐形式和腔曲很难达至极准的意境。因而,采用了电声+民乐的伴奏,促就了传统河南坠子音响的丰满,情感表达更加深厚,音响也更具时代感。而声腔的设计,以抒情曲调为主体,大篇幅的长调、上下波荡的旋律使情感得以深广的渲染与宣泄,其音域达到传统河南坠子极限,构筑了一幅诗美的“音画”,是河南坠子唱腔设计上的一次突破。
其次是表演上“气韵生动”与“形神兼备”的追求。在30多年的河南坠子演艺表演中,笔者不断追求“气韵生动”与“形神兼备”的境界,特别是在新创作品表达上,构造着自己独到的表演套路。“形神兼备是表演艺术之妙蒂……。张楷的表演从起步伊始就简洁概括,她富有才气的目光和举止都因为对主题和形象、性格的准确把握,以及她对自身女性形象和风度的矜持而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过分也不不及,或者说,宁可不够而绝不过头。这当然是艺术自信也是艺术旨趣的体现。”④上述为曲艺理论家薛宝琨教授对笔者唱做表演过誉的评价,其言更是笔者奋斗的目标。在唱段《擂鼓战金山》的表演上,笔者以“气韵”为引领,夸张、大写意为表演手段,塑造了巾帼英雄梁红玉气吞山河之势、鼓响雷霆震万军之态的女将风度;而《宝玉探病》中的宝玉、黛玉诠释,则是形与神的共融,虚实有度的张力,“情”大于“意”的处理手段;谐谑曲目的《偷石榴》,人物众众,其年龄跨度、性别差异、亲情关系、事件的突变反转等方面,在同一情境、而性格各异的表演上,则突出了“趣”的表达。笔者对每一部作品都在践行着“气韵生动”和“形神兼备”这一宗旨,以现代性的舞台表演思维,写意与写实相融的艺术塑造理念,使书段中久远的人物抑或虚构事件的表达,更能与今日观众审美情趣相近,而不至与时代脱节,人物枯黄无味。这种艺术的表达,完全基于笔者在其他表演艺术理论与实践中所获取的灵光而得,也正是过往的“艺不压身”才有了今日的“气韵生动”和“形神兼备”资誉,才能将传统的曲艺河南坠子表演艺术与现代舞台需要相契合。
最后是声腔演唱的突破创变与新唱腔形式的实践。一部优秀的曲艺鼓曲音乐作品,是基于唱段文学内容的新颖、贴切的词句、情真的曲调唱腔而来,但更需要通过演员对词文意境、唱腔音律的深刻理解,运用独到的声腔演唱方法、个性化的声音塑造以及优秀的表演方式才能形成,二者缺一不可,新创曲目《秋红赋》便是有力的实证。《秋红赋》唱词意境深广、赋美,文学性、诗意性、格律性和音乐唱腔的旋律性、歌唱性、艺术性都非常完善,如何将其搬上舞台、能否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喜爱,则看演员的技艺本领了。由于唱段音乐大篇幅的抒情旋律,音乐起伏较大且频次繁多,使说唱演员在声腔演唱处理上难度高强。笔者在运用传统河南坠子唱调发声吐字方法的基础上,结合音乐歌唱的气息、发声方式,以及本人音色的特质,形成非歌曲、非传统曲艺说唱的唱腔音乐处理,既有民族说唱的朴实无华美,又展露传统坠子无法达到的声腔演唱情境。在这里,已无法精准确认它是河南坠子哪一“流派”的风格与特征。此外,在近期新作品《海河情怀》演唱中,笔者完成了传统河南坠子本体及历史创作上创新性的5/4节拍、跨小节长时值的连续切分节奏、嗨“C”的音高等曲艺音乐演唱,赢得了界内外同行、专家的认可。
综上所述,河南坠子的兴衰与近现代津门商贸发展、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关联。无论是河南坠子史上诸多著名流派的形成,还是华丽转身、成为大都市艺术舞台上一枝奇葩,都与天津这座国际大都市、海纳百川的码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今下,在必须笃定坚守、坚实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坠子音乐、汲取其他传统音乐文化的同时,更需要用当代艺术的审美理念、表达方式、演唱表演来创造和构筑具有现代性的优秀曲艺音乐作品,使河南坠子音乐艺术赓续延绵,万曲繁盛,异彩纷呈。
注释:
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5〕18号),2005年3月26日。
②曹宏凯:《曲海艺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③习近平:《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2023年6月。
④薛宝琨:《气韵生动 形神兼备—坠子名家张楷艺术特色小识》,《曲荟》,2011年第2期。
(作者:中国曲协河南坠子艺委会委员、天津市曲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