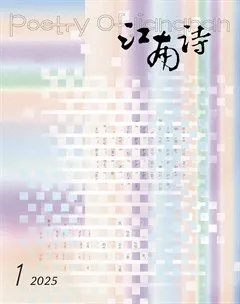鹅卵石
潘维品读:
在许多学院派的写作里,都不太愿意给普通人颁发阅读通行证,从纯粹理性认知来说并没有错,但实际上,诗歌不仅仅只需要神性,还需要人间烟火。换个说法就是,所有的写作者都必须面对:满足自我与接受非我之间的问题。曹僧这首《鹅卵石》很典型,我作为读者,很显然,他的语言把控能力很强,思路的运行也非常清晰,才气满溢,但我的感受是无法用自己的呼吸去细细品味,只能顺从文字的意志不断推进。这是否减去了读者的参与度?当然,曹僧作为复旦诗群的核心成员,他对诗歌有他的追求,反对平庸,寻找一种“综合心智”的创造,这种价值态度无疑符合知识群体的美学;可我给曹僧的建议是,适当的在诗歌中容纳一些平庸,也许会有更丰富的收获。
雨季曾泥泞不堪的道路至秋日已干涸
枝头,饱满的苦槠在壳斗中摇摇欲坠
当它们没有征兆地随机落地时,那声音
会像贝壳呕出痛苦一样干脆吗?
但土岸边先人种下的苦槠林整片静悄悄
黑夜的触须正偷偷摸摸地占领
从土壤呼吸的气孔,从草丛,从叶脉背面
包裹了残破的墓碑,缠绕了树干和树梢
然后又越过积有枯枝的浅沟,来到大路上
鬼手伸进你的衣领,在你一回头时
又忽然幻灭,像没有来得及溶解的颗粒
在一两声狗吠中:世界之杯晃了
只有一种自然之物还能如此坚固
从某个外县运来的鹅卵石,它们铺在路面
和苦槠被碾磨、凝结、变成稚嫩的豆腐一样新鲜
——彼时我们还没见过它们如何被溪流冲刷而下
我们蹲在地上耐心拣选,用一块敲击另一块
大多时候,石头排斥石头只有嘈杂的争斗
但当幸运的时刻来临,伴随着燃烧的刺激气味
零星的火光从撞击点向外溅射、穿刺
在黑暗中留下短暂的锚点,一次又一次
把头顶闪烁不定的星球搬进我们的脑中
我们听见,那是一种不一样的声音
使我们全然忽略一声声呼喊在身后将我们命名
——即使花朵关闭,黄鼬偷走记忆
那么久那么多的快乐与悲伤在万物间隐没
——即使发现只剩一个人,抬头、望向远处
被密林夹紧的道路,如同一口蓄势的深井
还不能让人知晓有什么将迎面迸涌
(选自本刊2024年第六期“首推诗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