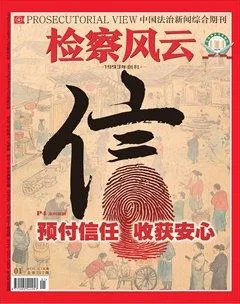张凌寒:探索人工智能治理“中国路径”

近一两年,就算是那些对时代“水温”不甚敏感的人,也或多或少被人工智能的热度所影响。更何况,“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这次深入访谈之后,记者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若不凌寒,怎有暗香?浪潮已来,我们呼吁更多热点中的“冷思考”。
一个充满挑战与希望的时代
记者:您是如何与人工智能结缘的,此后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哪些深入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果?
张凌寒:我的学术探索并非“一步到位”的简单过程,而是对数据、平台治理及传统民商法领域的深入钻研与持续积累。作为一名法学研究者,我最初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传统民商法和数据法领域,但始终保持着对新兴领域敏锐的“嗅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与逐步兴起,我认识到,这些新兴技术带来的不仅有技术层面的挑战,还有关乎社会治理和法律体系的全新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多项与人工智能和数据治理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立法咨询工作,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工智能法(学者建议稿)》(以下简称“学者建议稿”)起草专家组的牵头专家。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我很荣幸担任联合国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专家,在全球层面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讨论与决策,向世界传递我国人工智能治理理念,让国际社会听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然而,人工智能治理道阻且长,仍然有许多亟待探索的前沿问题。我将继续在这一领域跋涉、耕耘,希望未来能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人工智能治理提供更多具有实践价值的学术支持。
记者:以人工智能为重要驱动力量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幕拉开。当下,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融合?
张凌寒: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上的革新,更是对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重塑,它在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优化决策过程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这一轮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人工智能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对传统行业的深度赋能,使得几乎每个行业都在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可能。当然,科技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挑战。人工智能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还有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算法歧视、隐私保护、就业结构的调整等。如何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国际合作,强化人工智能的透明性、可控性和负责任使用,是当下的关键课题。我始终坚信,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如何以“善治”促“善智”
记者:以“善治”促“善智”,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您如何解读“善治”这个词,“善治”如何更好地促进“善智”?
张凌寒:“善治”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理念,本质上是为了引导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向善”发展,即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造福社会、推动人类进步,并且不偏离道德和伦理的轨道。
“善治”的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意味着在技术创新中,必须将人类福祉、社会伦理和公平正义置于中心位置,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善智”的实现离不开发展,而良好的“善治”能够有效促进发展,从这点看,人工智能的创新和监管并非对立关系。建立和完善分级分类的动态监管机制较为重要。人工智能的“向善”发展还需要政府、企业、学界及公众的共同努力。包容多元的全球合作机制,或将保障人工智能技术朝着更加安全、可靠且负责任的方向发展,最终抵达“善智”的彼岸。
记者: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风起云涌”。各国关于人工智能的立法和政策,通常能够反映出各自国际生态位下相应的治理诉求。中国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大国,将需要怎样的法律?
张凌寒:“领先的追赶者”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之定位,在这一定位的基础上,中国相关专门性法律的制定应从兼顾“发展与安全”出发,实事求是,积极回应中国本土的治理需求。在法律设计上,宜在推动技术发展方面提供实质性支持;在风险防控上,宜构建统筹协调的监管机制,合理使用分级分类的立法技术,针对不同风险级别的应用进行差异化管理,便于各行业主管部门在统筹协调的机制下,根据各自领域的特点配备相应的规范。
此外,法律宜着眼个体权益保护,并为未来技术发展预留“窗口”。例如,前述“学者建议稿”在个人隐私、知情权、平等权等领域设立专门条款,并特别关注对数字弱势群体的保护,以遏制人工智能影响下的数字鸿沟扩大的势头。宜建立人工智能动态监测、预警、响应机制,为产业创新探索监管试点(沙盒监管)制度等,以持续适应技术发展进步,进而实现敏捷治理。
记者:在网络法历史上,有过著名的“马法之议”。在今天,人工智能问题的法律化究竟是一种类型化的法学问题,还是具体现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张凌寒: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马之立法似空中楼阁,而人工智能之立法是历史与发展、矛盾与需求、变革与大局下的必然选择。人工智能对现有法律体系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其涉及领域之纷繁复杂致使其难以在某个或某几个部门法下得到体系性的解释。当下发展的趋势是算法、数据等要素治理逐渐被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治理所涵盖,致使原本在网络信息时代占据“基本法”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逐步演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要素法”,较难全面解决人工智能相关问题。有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尚聚焦于小领域、小问题,有待更高位阶法律予以协调。
我们立处如此重要的时代转折点,如何在此节点站稳脚跟,乃至把握主动权,是立法者、产业界及学术界共同关切之所在。“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历史变迁的轨迹、人民权利的保障、现存立法的分散性、产业发展的需要,共同呼吁着一部具有前瞻性、先进性的法律出台。
数字浪潮下的“世界课题”
记者:人工智能治理事关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国际社会群策群力。我们注意到,2023年10月,联合国宣布成立“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负责分析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并提出政策建议,两名中国学者入选机构成员,其中便有您。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一机构?
张凌寒: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全球统一步调、实现“共治”是确保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并提高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能力的重要途径。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由来自世界各国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主要致力于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科学、系统的政策建议,机构尤其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安全与隐私等方面的挑战,包容性与普适性是其价值基础,引导“智能向善”、强化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缩小技术鸿沟、推动科技公平共享是其发力方向,引导多方利益攸关方开展对话是其关键路径。
记者:您觉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应如何定位自己?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上可以贡献怎样的智慧?
张凌寒: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强对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开放共享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义,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交流与合作不可或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方可保障其在未来的全球标准与治理框架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领跑者,更需要以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路径”,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彰显大国担当、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